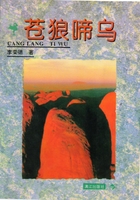——关于爱情的一篇童话
时间不会改变的是,岸边的居民永远都不会知道,北海是海还是湖。除了老墨,再没有人愿意关心这个问题。那时候,新任国王加冕不久,崭新的秩序和规律迅速蔓延四方各地,终于在侵袭北海最后一个村落时以碰壁告终。村落位于距城堡最远的北海沿岸,每天日落,村民拧小了灯芯,北海水波之下的黑暗和寂静中就开始蠕动着各类低沉的能量。
为了表达对北海神秘力量的崇敬,这个村子也叫北海。
“什么都不会改变,”每次去镇上开完会,在回村的路上,老墨都会强调,“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理论还有规定,让这些东西绕道而行,北海永远都只是北海。”
饥荒
六十年代,北海沿岸的上空笼罩起死亡的迷雾,数不清的生灵因饥饿而死去,幸存而孤独的生命只能缩在黑暗里不安地向外窥探。“几乎能看到死神骑着骷髅飞马在每一个屋顶上挥舞着镰刀时的身影。”人们不安地诉说,仿佛正在谈论一场恐怖的噩梦。正午,稍有力气的人都会走出门外,仅仅是因为一句谣言,他们带上大约两升容量的水袋或木桶,嘴里念念有词,耗尽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拖着饿扁的身体来到北海岸,终于筋疲力尽,最后把两升海水带回来洒在屋顶上。没有人再愿意把脑力花费在寻找食物上,饥荒已经被彻底接受,唯一变化的就是死亡人数的累积,人们相信,情况会在死神自认为足以满载而归时突然好转。所以在此之前,唯一可做的就是对死神隐瞒自己的热情好客——用北海之水驱赶它们。这么做仿佛有效,很多人都说,洒过海水的夜晚,似乎就听不到死神踩在瓦片上的那种可怕声响。
北海很幸运地避免了这次灾难。在饥荒开始之前,老墨顽固而冒险地拒绝了新任国王政令的下达,所以,在大多村落都喧闹的时候,北海异常安静。时过境迁,往日对老墨表示不解和弹劾的人终于在今天哑然失语,或许就连老墨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对变化和新鲜事物的排斥竟然奇迹般地使得北海和饥荒擦肩而过。不过话说回来,针对这件事,村民们更愿意相信的则是另一种解释——不是国王政令的失误,也没有谁做错了——而是德高望重的老墨配制出来的神奇的种子,才让肆虐的饥荒绕开了自己的村落。
那时候,北海成为海岸那一片枯黄中唯一的一块绿地,吸引着四方各地脆弱的生命。
为了自存,在尽了最大努力的接纳和援救之后,北海迫不得已对所有可怜的外村人关上了大门。头天夜晚,北海的村民再也听不到远处北海低沉的呼吸,取而代之的则是陌生人在饥饿折磨下的呻吟和哀号。往日低沉柔和的催眠曲,一夜之间变成了死亡进行时的恐怖伴奏。于是,北海每个村民都体验到了那种灵魂在岩石上摩擦的感觉。这场灾难终究让所有人不得自全。
能力
除了能配制出神奇的高产种子,老墨还是一个伟大的画师。在北海,几乎每个家庭都收藏了几张他的作品。老墨乐于为所有人免费画像,以至于为此废寝忘食。只要他自认为没有比画画更重要的事情急着做,老墨就永远不会放下手中的画笔。老墨从来不肯透露自己的秘密,他认为自己没有秘密可言,大家看到结果也就是原因——为什么自己画出来的肖像都可以向外界微笑,犹如活物——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他只知道,每次勾勒完毕,搁下画笔,画中的那张面孔就会抬起它神秘的嘴角,那一刻总能使在场的所有人满足和惊愕。
六十年代第九个年头,我来到北海,因为略懂绘画并且崇信北海深邃的内蕴,不等寒暄便得到了老墨热情的接待。那些天,北海表现出了少有的变化,在往日空荡荡的村口旁,村民们在三天内搭建了一座庞大的水泥碑。水泥碑完工之后,老墨扶着梯子提着五颜六色的涂料,把一个男人的头像放大了几百倍,小心翼翼地画在了上面。没错,就是那个住在城堡里的高傲的国王。这是国王对老墨多年前拒不服从国家新政的惩罚。我记得老墨在墙上涂画着国王额头上的红色宝石,忽然回头说道:“虽然我极不情愿,但是这是现在对未来的妥协。”虽然极不情愿,但是他并没有把国王画得面目狰狞,相反,他在工作时一如常态,画笔刚落,墙上的国王便浮现出一种满意而温和的微笑。
当然,城堡中的国王并不如画像中那般慈善,相反,他的脾气乖戾且一意孤行,言语之间可以让一个村落荡然无存。这自然让老墨从心里抵触,他忘不了那场绝望的饥荒,他忘不了宰割自己灵魂的一声声乞求和呻吟——但未来属于孩子们,他只能选择妥协。终究,老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由于难以忍受为国王画肖像的耻辱感,一个月后,他丢弃了自己视如生命的画笔,发誓今后永不作画。需要说明的是,答应为国王画像前的那晚,老墨做了一个满是涂料的梦,次日早晨,他找来线装古书、石头下的蟋蟀、三天前的炉灰、一盒铁钉和两团麻线,用它们完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阐释程序后,老墨召集了所有亲朋好友,宣布说:在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秋天海棠盛开的时候,自己的孙子就会来到这个世上。
北海的村民无人不晓,老墨拥有一种可怕的自信。此事之后,他坚信在某个女人的肚皮底下,自己的孙子必将遗传家族神秘的能力。那是让人神往而痴迷的恩赐,老墨的父亲不曾获得,儿子也不能获得,以致两代人都默默无闻。老墨坚信这种稀缺的能力必定也是以吝啬的方式赋予——隔代遗传。
秘密
八十年代,我已经沦为彻底的北海村民,继承了本地土生土长的奇怪风俗,养成了听到与死亡有关的消息就在口袋里放一点儿炉灰的习惯,学会了在每个礼拜五不假思索地走去北海取来海水洒到屋顶上的怪异行为,这是饥荒年代过后,从其他村落传来的习惯。在北海,只有老墨不愿遵从——十多年来,我从未见他去过北海岸。另外,因为我对老墨最彻底的尊敬,如果整个白天没有遇到老墨,我就会在傍晚跑去向他请安。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年,老墨的身体明显要垮掉了。
我从来不曾怀疑,老墨的梦果真得到了应验。但这多多少少也得益于老墨自己的催促,我记得七十年代最后一个年头,那是老墨一生中最唠叨的一年。为了耳根清净,原本打算修身养性的儿子很不情愿地结婚了,妻子是他儿时的玩伴,勤劳美丽,门当户对。一如童年时光,他总是忽略她的存在。无论如何,夫妻二人相处融洽,除了爱情什么都不缺少。
时间也对,篱笆院里的海棠花开了。坐在院子中间的木椅上,老墨焦急而自信地期待着孙子的第一声啼哭,它将盖过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喧哗。在这焦急的等待中,椅子上的老墨明显憔悴而衰老,那天,他再次召集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向大家透露了自己隐忍多年的秘密:
“我原本是可以飞的。”
老墨的意思是,他原本是可以飞的:像拥抱爱人那样张开双臂,脚尖踮起,便能凭风而去,就像水面上的一缕青烟。飞翔固然逍遥,老墨又说,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在神秘北海温柔的水面上行走。此时,他的表情是重温相隔多年的美好记忆的那种特有的陶醉:
“就像未出生的婴孩在子宫里独自嬉耍。”
伴随着忙乱的嘈杂,屋里传出一声尖细的啼哭,那孩子高调地降临人世。
意料之外的是,是一个女婴。老墨为孙子准备好的名字是鲲。那是他查了族里古老的家谱又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占卜后做出的决定。
“男孩的名字会带坏女孩的性格和命运。”接受了现实的老墨转口说,“这孩子叫鲤。”
鲤出生的第二年,老墨就重回自己深深迷恋着的北海的怀抱,自此,他的名字和自画像成为所有人缅怀和崇敬他的感伤物品。北海的村民并不向老墨的后代转移崇敬之情,他们珍惜这种感情,只让它在梦里泛滥。老墨说过,死并不代表人的瞬间消失,自己会在别人的脑海和追忆中再生。
记忆
鲤出生那天,接生的女人说,这个孩子可能是虚胖。她从没见过块头那么大身体却那么轻的婴孩。在场者只有老墨泰然处之,他说这孩子继承了家族最优秀的神秘能力,最后他又赢了,在他沉入黑暗海底的第二年,鲤已经可以偶尔地飘向天空,怡然自得地挂在树梢、依附在天花板上,就像一颗气球。
起初,北海的村民表示好奇,当他们一次次抬头看惯了天上的鲤,所有人便习以为常了。时间到了八十年代末,这个九岁的孩子不再独自享受飞翔的乐趣,她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研究如何同别人融洽相处上。那一年世界一如过往,只有信任和亲昵明显不再容易,仿佛这两种品质被装进了潘多拉的盒子,并且将被永久封存。人们走在街上,再也看不到路人脸上曾有的善意和笑容;人们在荒野赶路,就像行走在平行的两个空间,彼此视若无睹。而在此时,鲤却把享受克服引力的奇妙感觉分享给了身边的朋友,用之换来少有的信任和亲昵,就像用钱币在集市上置换生活用品,尽管那信任和亲昵有着明显的瑕疵——鲤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缺少最珍贵的那点儿单纯。
令人担忧的是,信任和亲昵一旦开始减少,趋势便一再恶化。日复一日,村民们淡忘了很多朋友和情感,能够剩下的都格外珍贵和必要。人们并不感觉奇怪和落寞,相反,他们唯一的顿悟就是过去不该那么滥用和浪费这些品质。除了这种变化,天空的变化也格外明显。以前孤独的鲤的影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陌生幼稚的面孔和她结伴出现,拉着她的手,在天空的一角,尖叫着飞来飞去。
历史总是不甘于被封藏在过去,五年过后,十四岁的鲤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祖父,她打听到许多他的事迹,伴随着对老墨了解的逐渐深入,鲤开始和村民一样对他充满敬畏,她发现自己未曾谋面的祖父竟是如此超于常人。老墨的灵魂就这么在孙女的脑海中得到了再生,她在村子上空飞来飞去,挨家挨户用传口信送鸡蛋这些鸡毛蒜皮的代价换来一段段祖父古老的往事,这些碎片从记忆的最深处被触摸、打捞并清洗如初,拼凑成一部宏大的生命乐章。关于老墨生命的结尾,也就是自己生命的开始,鲤只得到了一个闪烁其词的回答,因为凡是不知道的人都渴望知道,而知情的人又都渴望忘记。
鲤出生后的第二年夏天,鲤的祖父已经衰弱不堪,他变得沉默寡言,他想念北海温柔的波浪,就像想念数十年前自己难产而死的女人的脸庞和胸脯。她和自己第二个孩子的死让他不得释怀,他想起悲剧发生前的那一晚,自己对另一个姑娘辗转反侧的痛苦的渴望。于是次日,自己的女人同爱情一同死去,留下来的只有无边汹涌的怨恨和羞愧。自那以后,每次踩在北海的波浪上,他都能看到一双女人的手从水底伸出来,抓住自己的脚踝,冰冷地向下拖去。自那以后,他开始从天上掉下来,像流星一样。自那以后,他变得像中了枪的梅花鹿一样一头钻入灌木丛中,却又被那疯狂的枝杈捆绑缠绕,因而再难脱身。为了让自己重归平静,年轻的老墨大刀阔斧地冻结了北海空气中一切与之有关的记忆。他让自己沉醉于植物学,沉醉于夜以继日的画画,大脑超负荷的工作让那些灰暗的往事和情绪统统被挤压得模糊难辨,最后,以切割去自己一部分灵魂作为代价,老墨终于重获自由。但是时间让一切悄然变化,衰老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随之而来,鲤的出世让他从忘记中惊醒,他相信十一年前自己梦境的指示,男孩变成了女孩,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次意外也是一个指示,那就是要正视自己的过去而不是忘记。从此大片痛苦的记忆重回脑海,久违了的那部分灵魂像水母一样飘摇归来,又忽然像水蛭一样钻入他柔软的心肺,快速吸食他剩下不多的生命。一年下来,老墨变得衰弱不堪,生命的尽头眯眼就能看到,但生命的意义却未曾浮现。
那年夏天,老墨支起画架,拿起久违的画笔,颤抖着画出一张年轻女人的脸。收笔那刻,不同以往,那女人的脸上没有笑容,她在哭泣。当天,老墨决定并回到北海潮湿的岸边,听到他脚步声的逼近,树木让开道路,虫蛇蚯蚓纷纷探出土壤,环境像数十年前一样美好,老墨踽踽踏上水面,像夜船一样安静。此时的北海异常平静,仿佛水面屏住了呼吸。走到水面的稍远处,老墨向下望去,看到了久违的那双手,苍老让他不再恐惧,他回过头来,向岸边的世界挥手告别。
坠落
听完这段回忆,鲤和别人同样感伤,也开始明白为何自己那么恐惧北海宽阔的水面。而在当下的现实,鲤遇到一个看似特别的男孩,他眼里没有环绕她的那些孩子们眼中虚假的热情,在他的眼睛里只有让她好奇的深邃的空洞,就像北海无尽的海底。这个孩子腼腆而自闭,为了让他变得开朗,老师就让他做这些孩子们的小组长,但他依旧独来独往,没有起色,弄得整个小组也松松散散的。
很明显,他的冷漠挑战了她的自信。
那天他独自蹲在离人群有一段距离的草地上,鲤走过去,说要带他围着他们休息的巨大的苹果树的树冠盘旋三圈,条件是要他把小组长的职位让给她。
面对鲤的要求,小组长选择默许,反正他对一切都毫无兴趣。于是她说:
“一会儿飞的时候,我是背着你还是拉着你?”
似乎有些征兆,鲤突然就失去了飞翔的能力。她坚持认为因为自己伸手拉小组长起来的时候,他暗暗地用力捏了一下她的手,刻意而又不轻不重。这让她失去视野,意识里翻涌出一团清澈的泉水。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重。引力冲破地面,牢牢地抓住了鲤的身体,无意放开。她就再也飞不起来了。
她不得不开始适应一个身体的重力,学会像正常人一样慢悠悠地生活。因为不肯相信,她每天都会从草地上跳起,从椅子上跳下,从桌子上跳下,栽倒在地上,再失望地站起来。远不止这些,需要学习和适应的还有作为普通人无法逃避的平凡和孤寂,这点让她难以忍受。以往因渴望飞翔而拥簇她的人变得一如往常的冷漠,没有了鲤的天空也因此显得单调而苍白。与此同时,角落里的小组长却突然走出了往日的封闭,他好似换了灵魂一般突然长大,整日散发着让所有人久违的、空前纯粹的热情。
他成了她最后收服也是唯一剩留的朋友。小组长不相信是他不小心捏了一下让她失去了飞翔的能力,但他还是表示愿意为此负责。他邀请她踩着自己的手掌爬上自己的肩膀,骑在自己的脖子上,紧接着他开始奔跑,大叫着告诉她:“你看,我还可以让你继续飞。”而后,她总会爬上他的肩膀,骑在他的脖子上,让他载着她四处奔跑,怀念以前飞绕苹果树冠的日子。
鲤失去飞翔能力的第二年,针对肆虐地吞噬情感的恶魔,城堡里的国王发起了一场自我救赎运动。新政令的下达便是另一场灾难的开始,国王的热心和善意换来的只能是更糟的结果,人们对国王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什么也不做。按照国王的意思,路人必须相互示好,邻居必须定时走访,就连每个人的言行思想,都要及时记录下来,在每个夜晚九点,准时递送到镇上,而后一级一级递送到城堡。北海没有了老墨,政令的下达变得畅通无阻,于是,在每个夜晚的九点,小组长都要跑去遥远的镇上,向上级递送组员们当日的言行思想,风雨无阻。从第一天开始,那条通往镇上的小路就开始逐渐变得纤细而漫长,直到一个月后的那晚,小组长发现自己已经走不到尽头,而回过头来,位于北海的起点也已被荒野一口吞噬,他仿佛走进了另一个空间,直到自己消失。
北海的村民哀叹小组长的离去,对着老墨的画像哀叹世界的变化。画像里的老墨依旧抬起嘴角,笑容空白而无内容。
沉没
小组长消失之后,鲤的身体一天天变得沉重起来,直到彻底迈不开脚步。她纤弱的身体从未像现在这么沉重,那是什么的重量,她能觉察但是无能为力。日渐增加的重量让她喘不过气,每日只能进一小碗清水,她几乎开始绝食。
随着身体的日渐憔悴,自我调理机制睁开了它沉睡的双眼。鲤开始变得特别健忘,一些浓重的记忆被快速抹去。白天,她记不清小组长是否举起过自己,晚上,那些被抹去的记忆会做出最后的挣扎。她翻开一个破旧的笔记本,快速地记下这些片段,直到有一天,她再翻开这些文字也是无济于事,她完全忘记了小组长肩膀的温度,也忘记了他亲吻自己脸颊时的甜蜜。不到一个月,鲤已经彻底忘记了小组长的面孔,忘记了他是如何让她无法飞翔的。那年岁末,大病初愈的鲤踮了踮脚,发现自己的身体轻得可怜。
再没有浪漫怪异的故事发生,九十年代第八个年头,一个外村旅店老板的儿子,和十八岁的鲤结婚并生下了一个女儿。很久以来,我一直都在计划着离开北海,却不知道该往何处落脚,我的人生陷入了长久的犹豫和徘徊之中,不知不觉已到垂老之年。我开始审视自己的过去,我怀念我的老朋友。其实也不用焦急,在每一个周五的早晨,当我提着水桶走出村落,在色彩浓重的北海边,隔着一片海水,我已经能看到越来越近的彼岸,那里有老墨和他爱过的女人们,还有那些夭折的孩子们,在那里,我们将一如过往。
而出嫁后的鲤并没有像我们一样平凡终老,两年以后的世纪末,她来到北海,水面像微风吹过的草地。她想起让祖父身陷大海的那双女人的手,它让他一度坠入无尽的恐惧,也成为鲤无尽的噩梦。这时候,北海寂静得仅剩万物的呼吸,她走到遥远的大海中间,低下头去,看到一双男人的手,伸出水面,它抓住她的脚踝。它没有如传言那般将她冰冷地向海底拖去,而是暗暗地用力捏了她一下,刻意而又不轻不重。瞬间,重返眼下的记忆和情感带给了她往日的重量,她开始快速下沉,波浪下面,这海底像极了小组长深邃的瞳孔。身边,当那双手将她托出海面的时候,她发现,过去从来没有离开过。
最后,她还是沉入了深邃的海底。目击者兴奋而惊恐地说:“无论如何,她还是被拖了下去。”应该是她自己要下去的,因为她要去吻他的脸,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