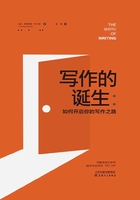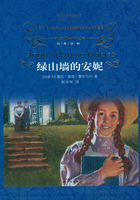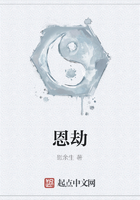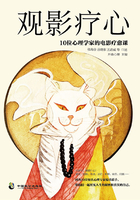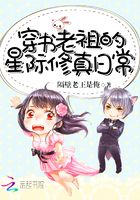这个世间有很多事情,总要拖延到回顾之际才会变得明晰,在事情的进程中却不能产生敏捷的反应,从而及时意识到它的严酷,倘若事情的后果当真有必要劳烦“严酷”的话。缓慢的尘埃落定之日,也并非悉数等同于盖棺论定之时,认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往往并不意味着事情的性质就能得到公认。公认,公众或者拥有发言权之资质的全体人士的统一口径,无疑是个奢侈的期待,尤其在“研究”的名义下。
如此,对中国人口于清朝时期那番史无前例的增长,究竟是否应当给予一个“人口危机”或者“人口过剩”的概括,也就不足为奇会成为一件让众学者挠头的事情,给有给的理由,不给有不给的论据,两相争议的声音是如此之响,且始终不见拍板定音。
好在事情业已过去,无论到底该如何定性,人口的增长总还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事实是,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极为壮观的一次人口膨胀:连续突破2亿、3亿和4亿大关,至咸丰元年(1851年)已攀升到4.3亿人之多。至于这个庞大数字的基数,则至今,或者说以后,以及永远,都将无法得到精准的确定。这缘于彼时不曾进行过可资信赖的全国人口普查。
清朝从顺治八年(1651年)首次进行丁册的编审,接下来五年一次,持续到乾隆六年(1741年)户口制度做出重大改革。这期间留下来的唯一数据,就是丰富的丁数。不过有很多事实表明,这些数据虽名义上为“人丁”统计,却既不代表全国确切的丁(16—60岁的成年男子)数,更不代表含“大小妇男”在内的人口数或者户数,而只是纳税单位;至“推丁入地”导致丁税不存之后,此类不足尽信的数据就愈加漫不经心。因此对于清前期中国人口数据的复原,无论治学如何严谨的学者,都只能采用估计的方法,估计出当时的平均每户人口数,再与这些模棱两可的丁数相乘。史上曾被诸多中国人口统计学家认可为“最有见识”的估计是:顺治八年中国的人口大致为6500万。
将人口从6500万增升至4.3亿,耗时两个世纪。在一个前工业社会里,如此强劲的人口增长势头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且是就世界范围而言。据说此速度已与进入工业革命时期(1760—1850年)的英国年均人口增长率不相上下,同时期的欧洲则不在话下。
这样的一场人口增殖,来得迅捷、果断又不事招摇,亦因此久不被觉察,过程中虽有零星的前瞻性警示言论出现,却也顶多取得了惊世骇俗或耸人听闻的言语效果而已,并无补于实事。如若不是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一点点得以突显并渐趋尖锐,以致最终严重失衡几乎影响到每个人的生计,或许人们还在一味感恩于人丁的兴旺,而不会抬起头来定睛打量一下周遭已然十分拥塞的人群,更不会回过头去试图弄清这状况的确实来路。
蓦然回首之际,时人也并找不出一个人口增长的切实起点,以及促成这一增长的具体缘由,还是陆续的后来者渐次拂去时间的尘埃,慢慢浮现了几根模糊的线条,或许可以大致勾勒出历史的颜容。
最有分寸的说法,是清朝时期中国人口的快速稳步增长起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或者说,康熙二十二年之后,社会才为人口的快速稳步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整体环境。在此之前,人口的增长应该也有发生,不过是缓慢的,且只是恢复性增长,恢复在明末李自成等人牵头的农民起义中所损失的人口,以及在清廷漫长的征服中原之战中所杀伤的数量未必不足道的人口。这种增长也不一定就保持了稳定,历时十载的平三藩和收台湾之战,必然会丧失一定量的人口,也必然会部分地挫伤人口的繁育。
当时间滑行至1683年,清廷掐灭前明遗魂的最后一缕香火,完好收复了台湾之后,中国本土始才再无伤筋动骨的大规模战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1796年)。在这一百多年间,除了几次展布于边疆的军事活动和波及范围相当有限的小打小闹之外,社会整体上是太平的,兴许也称得上是祥和的。康熙二十二年,由此成为孕育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繁华盛世的起点,也成了导致此番人口膨胀的一个重要拐点,中国人口自此开始在快速增长的轨道上稳步前行。
久无战争的世道,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碰巧投生于这一时代的人们无疑是幸运的。当不必须再为生存心怀焦虑,不必须再因祸乱劳苦奔波,人们似乎也就有理由在繁育后代的事业上多花点时间,多用点心思。后来的事实表明,人们也果真以空前的热情这么做了。这似是情有可原的,如果不说是顺理成章。中国古老的传统观念告诉人们,人丁兴旺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幸事,亦是一个朝代足够强盛的印证。证明一个家庭是否称得上幸运,一个朝代是否称得上繁荣,人丁的是否兴旺总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很多时候两者互打证言,互为促动,从而把这种幸运与繁荣推衍至峰巅。
对生活于封建社会的人们来说,这种幸运的得来是绝对的偶然,就如一个封建王朝的繁盛一样,都是特别的脆弱。封建王朝的专制性质,使这个王朝的景况以及投身于其中的民众生活,都大多取决于那个被称之为“皇帝”的人,取决于此人的人格、品质与能力等。这无疑是一种所下赌注非常不均衡的非对等性赌博。在这样的一场赌博中,如果还侥幸取得了王朝的繁盛与民众的幸运,以及由此而来的事实上的人丁兴旺,则有充足理由需感恩戴德于事物的偶然性,即刚刚好好碰上了一位大体称职的皇帝。
以仁爱留名史册的康熙帝,应该说是名副其实的,此君宽厚仁德,心肠很可称道,在位六十一年,颇以普天下的民众生活为自己眉间心头之事。当事情已成历史,人们再回头观望之时,会发现康熙不仅为中国在有清一朝的“人丁兴旺”提供了一个优良的大环境,还以一道著名的“仁政”为此添加了一股强大的助力。
此“仁政”即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清朝的国库收入原本主要来源于两项:田赋和丁役。田赋指土地所有者每年按亩数向政府交纳的一定税额,也可说是地税;丁役指16—60岁之男子每年向政府承担的一定徭役,多被视为人头税。此两项一向被历朝历代称之为正税,初起前者纳粮,后者服劳役,至清朝则只要一部分粮食以备漕粮(供给军队及北京政府消费之粮)所需,余者均已折合为银钱,丁役也就演化成了丁银。丁银的征收是按丁数来计算,无论此丁是否拥有相应的财产,因此一直是底层贫苦民众的沉重负担,躲丁逃役之事普遍发生。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康熙颁发了一份影响深远的谕旨:念“今海宇承平已久”,“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故令各省官员“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这就是清朝有名的新政:“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意思是说:此刻账簿上存有多少人丁,日后就照此收取多少丁银;以后世面上再添新丁,都恒久不再加征丁银。亦即:从此政府只收地税,以及以1711年的丁数为标准的定额丁银,就可以了。据康熙透露,彼时“国帑充裕……国用所需,并无不足之虞。”
此旨意在民间,尤其在广大贫民中所注定要产生的反响,即使现今的人们应该也能够想象得出。康熙的“永不加赋”实质上含有这样的暗示:此后出生的人丁,如若你的手里没有土地,你将有可能不再身负一文税赋。
之所以说只是“有可能”而非“必然”,缘于冻结在1711年的人丁数仅是丁口数额,并非具体的人丁,而人丁在年满60岁或半路意外弃世时,理论上都要从丁册里去除;去除掉的这部分差额,则还需要新的人丁来补足,如此方能圆满政府的定额丁银。至于找谁来补,政府亦有明文规定:“如一户之内开除一丁,新增一丁,即以所增抵补所除;倘开除二三丁,本户抵补不足,即以亲族之丁多者抵补;又不足,即以同甲之粮多者顶补”。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猫腻很多,尤其存在有权势者的上下其手,于是这抵补之丁究竟会摊到谁的头上,并不必然。并不必然,也还同时意味着这件倒霉事未必一准儿就会摊到我的头上,起码它已丧失了命中注定的权威性,而给了侥幸心理以充足的生存空间。
这就够了。
数年之后,当“不必然会负担丁银”,转而成为“必然不再负担丁银”之际,人们在繁育后代的时候,心中所存的最后一丝丁银上的隐忧,想来也就有可能彻底烟消云散。
这一转变的操作者是雍正帝。
康熙的接班人雍正,其性情与乃父迥然不同,他严峻冷酷,猜忌多疑,恰还有着更胜一筹的精力来支持他更加勤于政务,这使他于在位的短短十三年间,将集权专制发展到了一个新台阶。所幸的是,雍正亦是一位胸怀大格局的帝王,其专制并不曾导致王朝境况的下滑,反而在他的铁拳下更趋捋顺调阳,起码对人丁兴旺的盛世景观算得上是锦上添花。这动力的来由,就在于赫赫有名的“摊丁入地”政策的普遍推广。
“摊丁入地”是中国赋税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改革,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就已在康熙的默许下,率先于广东和四川两省试行,却并不曾推而广之。所谓“摊丁入地”,即把丁银核入地亩,一切赋税皆由地出,丁随地起,丁地合一。出发点在于使纳税人的赋税与其财产相匹配,从而杜绝事实上早已存在的“富室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之弊端,以此缓解无地贫民因无力缴纳丁银而隐漏逃亡的现象,以期达成赋税得以顺畅征收的目的。无疑这是一项相对科学又公平的征赋之法,却因严重有损于地主阶层与富户缙绅的利益(这些人向来以地多丁少为集体特征),而于过程中遭遇到了强烈反对与百般阻挠。难说康熙如何理解这样的阻力,总之在他有生之年没能将其全面推行。即使是雍正在最终下定决心推广之前,也还在捡这样的用词骂人:“摊丁之议,关系甚重,岂可草率从事……观尔近来所奏,每多涉于孟浪”。
不过这份惹来指责的奏折,想来还是引发了雍正更为审慎的斟酌,使他很快就在再一份的同类奏折上果断批示:此事“实可准行”。这道朱批令各省督抚震动异常,却是事情已成定局。雍正二年(1724年),“摊丁入地”在直隶正式施行,接下来陆续推广到福建、山东、河南和浙江等十三省。未竟的事业由其子乾隆代劳,18世纪末基本上完成了这项一波三折又困难重重的赋税改革(东北三省因情况特殊,至19世纪中叶才开始实行)。
“摊丁入地”多被视为“惠于贫民”的恩政,起码理论上如此,毕竟无地有丁或地少丁多是底层民众的一贯特点。然而凡事架不住运作,运作手艺的高超精妙,足以令一切事情于进程中改头换面,无论其原本的脸孔如何纯洁。
不管哪个朝代,土地持有者与土地劳作者向来不能画等号,堪画等号的自耕农向来只占很小比例。自清朝伊始,贫民以租佃方式劳作于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就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雇工身份成为土地真正劳作者的贫民,也已越来越多。当贫民必得依赖向土地持有者支付地租或支取工钱来维持生计的时候,心肠不怎么厚道的土地持有者,也就总有机会使出万般花样,来尝试将核入土地的丁银重新转嫁给贫民。
只是无论如何,天下间也还是从此再无丁银之说了。自古就紧箍咒般套牢在头顶上的正税之一,业已就此连根去除,且理论上将永不复现,不管以后的事态将会扭曲到何种程度。
这就足够了。
康熙、雍正与乾隆,这祖孙三代帝王相继制订与施行的诸道“良法美政”,营造出了为期一个多世纪的清明世界,至少当政者的本意属实是想营造出这份清明的。这样良好的社会大气候,显然轻易不会挫伤人们的生育热情,如果不说还一定给予了鼓动的话。也很有可能,部分地区的溺婴习俗(“产后流产”之普遍手段)亦会得以部分破除,甚或得以一定程度的杜绝也说不定,毕竟无需再担心那小人儿胎带来的税赋了,孩子注定是负担而非财富的局面已彻底得以打破,这使个人的法定生存成本得到了显著降低。康雍乾的“开明专制”,不仅促生了许多人,也挽救了不少人;人又育人,生齿日繁。
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增长模式,各有不同。对前工业社会来说,传统的人口增长模式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较低的自然增长率。这样的模式,理论上可以套用于有清一朝,不过其中晚期事实上已存在的人口膨胀,让人有理由怀疑一定有哪个环节出现了异常。
一个国家或一个时期的人口,究竟是增长还是降低,取决于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比拼:当出生率大于死亡率,人口必然增长;当出生率等于死亡率,人口的增长为零;当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则必然负增长(降低)。由上述可知,自康熙二十二年之后,社会是相对太平的,政治是相对清明的,由此导致相对的高出生率,是可能发生的,亦是可信服的;人口的快速稳步增长又确凿而毋庸置疑。看来,异常之处只能出现于这一模式的中间环节:高死亡率。意即,唯有这一比率业已卓有成效地事实上削减为“低”或“较低”,至少要远低于出生率,才能把这样一个人口膨胀事件,永久地注册于历史之中。
那么,人们究竟获得了怎样的外力支撑,才保障了这些用相当不慢的速度相继莅临的浩荡生命,以颇高的比率得以存活下来?
必然影响一个生命是否能够得以存活的因素有多种,其中以食物最为直接。尤其在医疗水平并无相对的特别改善,自然灾害也并没有相对的明显减少之时,食物对于一个生命的能否延续,对于某一时期人口死亡率的或高或低,就更加具有决定性。
对有清一朝的中国人口发展问题研究至今,人们倾向于认为,食物对这场持久的人口增长给予了相当助力;也就是说,食物供应的大体充足,亦是此番人口增长的催生因素,与环境的太平和政治的清明一样不可或缺,如果愿意,也可以把它看作严肃的经济因素。既属经济范畴,食物的态度是否积极,也就取决于社会的整体经济状况;食物所能提供的具体饱腹之物,也就要由相应时间段的实际经济状况来做主。
曾有学者从世界人口发展史中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每一次壮观的人口激增,都是在生产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时发生的”。这貌似一条真理。就世界人口增长史而言,人口增长幅度属实在随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提升,增长率16世纪为11.9%,17世纪为47.5%,18世纪为80.6%。18世纪的世界人口增长之所以如此迅捷,显然与欧洲的工业革命已在进行中密切相关。不过这条规律显然并不适合有清一朝的中国人口发展状况:那一阶段的人口增长不可谓不壮观,却并不曾发生应当的生产技术革命。如果此规律当真是一条普世的人口发展规律,那么此阶段的中国人口增长,似乎就只能算作一种不理智的率性而为。也或许,那仅是人类增进人口最佳的理想方案,而非唯一。
无论如何,中国于有清一朝的人口增长已是事实。对于这一事实与上述规律之间所存在的出入,仍然是人们倾向于认为:有清一朝的中国百姓,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借助于粗谷杂粮,就养活了于此番人口增长中激增的庞大人群。这一既成案例告诉人们:假如肯把饮食降格为果腹,肯把生活退而为生存,即使在生产技术并未发生重大变革的前提下,在经济状况并不如何乐观的景况中,亦有可能成就一番人口增长的伟业。尽管这一点儿都称不上理想。
负责任的说法是,有清一朝人口增长的前期阶段,经济状况还是相当可资称道的。正处于巅峰期的农业文明,使传统的封建生产方式取得了利润的最大化,这使彼时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准无论是与前朝相比,还是就同时期的世界范围而言,都一度处于领先地位,即使赶不上正在着手工业革命的英国,却未必不优于法国,也未必不会超出普鲁士。“总是尽生活资料允许的范围繁殖后代”,相传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育文化,想来若不曾有相应的经济支持,此番人口增长的序幕万难拉开。
在前现代时代,人口增殖与社会资源的关系很直接:人口越多,开发资源的动力越足,越迫切;社会资源越充分,人口的增殖也就越多,越迅速。不妙的是,社会资源并不会无条件地步步紧随人口的增长而增长,尤其是仍在旧有的生产方式下,社会资源渐次的相对短缺倒是一种必然。因此,在一个不曾对人口增长做好准备的社会阶段,即未曾同期进行生产技术变革的人口增长阶段,经济上的渐趋委靡、捉襟见肘,就是一个必然后果,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见窘迫。事实是,中国农民以渐次降低生活水准为代价,暂且躲过了那个传统模式中理应的“高死亡率”,从而维系了此番人口的持续增长。
源引自美洲的多种高产粮食作物,使这种难说是否划算的交换得以成行。
堪称救命稻草的美洲粮食作物,并非在有清一朝始才到来,当哥伦布那双值得问候的大脚踏上新大陆30多年后,中国的土地上就已经生出了花生的植苗。之后各类作物的种子,包括玉米、地瓜和土豆等,都陆续到来。诸如此类的美洲粮食作物,之所以在此番中国人口增殖过程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积极因素,在于它适时得到了推广。
这种推广的性质与其种子的引进迥然不同。种子的引进或许实属无意,最初仅是由葡萄牙等外国人的兜里揣来,带有偶然性;推广则是绝对的有意而为,人口增长愈多,愈被政府及治下诸省的各级官员热切呼吁,并再四督促,带有极强烈极直接的目的性——养活人,养活更多的人。这是使中国的食品供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好歹算是大体跟上了人口增长比例的多种因素之重要一种,从而保障了“高死亡率”的有效降低。
在这些作物中,地瓜,也即那种学名甘薯的物质,值得一提。
相对而言,地瓜的生物学特性可谓优秀,大致表现于三点:一是适应能力强,别种作物无法存活的盐碱沙荒土,完全可以成为它的温床,以致“东西南北,无地不宜”;二是特别高产,“一亩种数十石,胜谷二十倍”,且不惧蝗,蝗过而草木净尽之时,“唯薯根埋地中,蝗食不及,即令茎叶皆尽,尚能发生”;三是富含高浓度淀粉,可做菜,尤其可作为粮食替代品,且好储存,晒干后同样可食。
这样的品质,使地瓜在已苦于家里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民手里,得到了热情的广泛种植。地瓜的引种,使人们开发了以往不能利用的大量荒地,使耕地面积得到了增加,粮食总产量得到相应提高。至后来,仅充分利用沙荒地已然还嫌不足,为使粮食总产再高出一块,人们亦一再减少素有“谷中贵族”之誉的稻米和小麦的播种面积,腾出土地来种植地瓜。在土地有限的条件下,在生产力亦有限的情况下(如生产工具、水利和肥料等并无重大改变或改善),倘若还迫切需要获取更多的食粮,也就只有更多种植那些单位产量更高的作物。
随着时间慢条斯理地前行,在日渐冷漠的太阳光下,或煮或蒸以致堪食的地瓜,也被中国农民越来越频繁地端上越来越无法保证体面的餐桌,而日益成为他们的主要口粮。当人口数量逐渐抵临甚或超出社会资源的警戒线,努力让自己的肚腹适应并满足于粗劣的食物,也就成了尽可能保障更多人能得以存活的最简便的有效途径。
不过这种途径也并非没有限度。如果说在现实逼迫——人口仍在一意孤行地激增,耕地的增长却已力不从心——的状况下,“肉食”可以转化为“素食”,“素食”亦可降格为“粗食”,那么也就似乎找不出理由,来阻止“粗食”向“不得食”的过渡。
这种无疑会带来普遍绝望情绪的过渡,将发生于何时?
——唯有土地能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