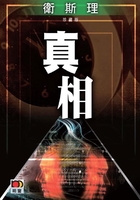自我与索尔相遇之后的几个月里,最令我难忘的是他送给我二十五朵玫瑰的那一天。那束玫瑰是他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事实上,也是第一次有男人送我花。索尔和我在图书馆发生不快之后,就没有再给我打过电话,我担心他是因为我大发脾气的行为而犹豫了。那三天,我如坐针毡地等着他的电话,心里自责不已,再一次为自己总是做出不经过大脑的冲动行为而后悔。
后来,索尔送了我一枚胸针,那曾经是属于他外婆的首饰。我喜欢这枚象牙胸针,但这枚胸针所带来的喜悦永远比不上我那天上完课后,从大学心灰意冷地回到家中,发现那束玫瑰时的喜悦。玫瑰不同于珠宝。玫瑰是活物,因此同所有活物一样,无法久留。我不知道他是否曾告诉他母亲他给我送过玫瑰,但她最终还是知道了他送给我胸针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忘记她看到那枚胸针时所说的话。
那天下午,我母亲在家里为韦斯特蒙的一个有钱人裁制礼服。回溯过去,我想她当时应该正跪在地板上用她的大剪刀裁剪出一个样板,舌头从两唇之间探出,抵着嘴角一边。这时门铃响了。她站了起来,整理好便服,抚平上面的褶皱,寻思是不是我们隔壁的勒克莱克夫人来了。但开启门后,她看到的却是一辆写着“蒙特利尔市罗比乍得花店”的货车。
“这束花是给丽贝卡……啊,”送货员仔细查看货单,“怀斯曼的。请在这里签字。”
当然啦,我并不知道那个男人是否有所迟疑,但在我的想象中他迟疑了。我的头脑总会加强我的记忆痕迹,直到有时候我都记不清哪些事是真的,哪些事是我编造出来的。我将这种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归咎于我每周都要读一两本书这个终生习惯。
我母亲试图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可以看出她的兴奋,但也只是猜测她大概是又接到了一件礼服的订单罢了。“过来。”她说着牵起了我的手,领着我到餐厅去。我还没见到那束玫瑰呢,花香就已经钻入鼻尖了。这束花插在桌子中间的深蓝色花瓶里。黄昏的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似乎仅仅洒在了那束玫瑰花上。玫瑰那娇嫩的花瓣,红得令人陶醉。
“爸爸送的?”我忘了父母的周年纪念了吗?
她看着我,就好像我问了一个傻问题一样。“不是,是给你的,是索尔送的。”
“索尔·戈特斯曼?”
我的母亲笑了起来,双手乐呵呵地扣在下巴上:“当然啦,你还认识几个会给你送花的索尔啊?”
我从两朵玫瑰之间拿出卡片时,双手都颤抖了。我有些着恼,因为我没办法表现得冷静而又老道,装出收到这份礼物一点儿也不意外的样子来。
丽贝卡
一朵玫瑰代表我们友谊萌芽的一天。
索尔
不知所措中,我失手掉了卡片。我对上一次约会的疑虑消散了。我等不及要打电话告诉杰姬了。事实上,我甚至想要站在我家前廊上大声喊出这件事情,好让整个蒙特利尔都听到。
“抱歉我没有把花留在盒子里,”我听到母亲说,“我只是想尽快把它们插进水里。”
我们并肩站在那儿,默默无言地凝视着这束鲜花。透过敞开的窗户,收音机的声音从隔壁那栋房子里传了过来。我听到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新闻播报员声情并茂地形容着人们夹道欢迎伊丽莎白女王访加的热闹场面。我仿佛感受到他们是在为我而欢呼的。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玫瑰呢。”我母亲说着,摇了摇头,似乎无法理解如此奢侈的行为,“我婚礼上的鲜花都没有这么美。”然后她就开始考虑起实际的问题来:“记得把花瓣留起来,收到一个亚麻袋子里,放到你的梳妆台上。”
我抱住母亲,忍不住取笑她:“只有你才会想到这种事。”任何东西她都会留起来,就连好些年前做裙子剩下来的碎布头她都还留着。
“为什么不呢?你这辈子都会记得这一天的。”
“我好开心啊。”我低声呢喃着,把脸埋进她的脖颈中。
“他一定非常喜欢你。”她轻柔地说着,然后伸直手臂把我推开,看到了我的眼泪,“好啦,这种时候可不该流泪,应该为此感到开心啊。”我点了点头,抿紧了嘴唇,免得止不住颤抖。“你只能年轻一次啊。”她说着,撩起围裙拍了拍我的脸颊,擦干了上面的泪水,“我听到你父亲的声音了。”
“我不想让他看到我这个样子。我下来前,别让他去看那些花。”
我在楼上用冷水洗了脸。我记得曾经她是如何形容她婚礼上的鲜花的。她十岁从巴勒斯坦的小城采法特来到加拿大,从此就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她和父母姐妹一起,坐三等舱到马赛、里斯本和爱尔兰的科夫去。科夫是前一年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停泊的最后一个港口,知道这件事后,她就对横渡大西洋产生了恐惧感,即使是在八月的暑气中,也依然忧心冰川会嘎吱嘎吱地碎裂。在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上岸后,她发誓她再也不坐船了。
我擦干脸,梳了梳头发。在楼梯口深吸一口气后,我理平自己的半身裙,回到楼下。我父亲正在厨房的水槽边洗手,我走上前去吻了他一下。
“我们今晚在餐厅里吃饭。”我母亲说着,就让我父亲这个一米八有余的高瘦男人回到客厅去。
“到客厅里去放松放松吧。”我说道。
“那还不如待在这儿和我的宝贝姑娘们聊聊天呢。”
“算了吧,你累了一天了。”我母亲坚持道,“跷起脚来放松放松,看看报纸吧。”
他面带狐疑地看着我:“好吧,好吧,别把我给推出门去啦。”
我和妈妈拿出精美的瓷器和布餐巾,咯咯地笑了起来,就像过家家的小女孩一样。
“你们别想戏弄我,”他从客厅里喊道,“我知道你们一定在密谋些什么。”
最后,我们终于同意让他进餐厅了。他怀疑地瞧着自己在餐桌旁的位置,坐下前还认真地检查了一下他的椅子。我母亲念完祈祷后,就开始上汤了。我父亲皱着眉头,目光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来回逡巡:“我投降了。”
“迈克尔,就算有头熊在那儿,只要它没咬你,你也是看不到的。那些顾客竟然没有在你的眼皮底下大肆偷窃,这真让我感到惊讶。”我父亲是公园大道伍尔沃斯超市的副经理。
她递了一碗汤过去,对上他的目光,偏头指向桌子中央。
“什么?”他说道。
这也没用,她终于抬手指向了玫瑰:“索尔送了这些玫瑰给贝卡。你闻不到花香吗?”
我半含期待地希望父亲能问问“这个索尔是谁?”,因为他还挺健忘的,尤其是妈妈想让他去修修家里的东西时。“你的新欢,呃?”他吹了一声口哨。
“他只是一个朋友。”我说。
“这份礼物对‘朋友’来说太贵重了些吧。”
我母亲点头表示赞同:“我也是这么跟她说的。”
“没有哪种好东西是我女儿配不上的。”
我从花瓶里抽出一支玫瑰,掐掉末梢。我绕过桌子走到母亲身旁,把玫瑰的茎插入她毛衣上的纽扣孔里,然后吻了吻她的头顶。她把目光从我们身上移开,声音沙哑哽咽:“快喝汤,不然就要凉了。”
我母亲并不反对多愁善感,只是不喜欢这种情绪出现在她自己身上而已,尤其是在被猝不及防偷袭的情况下。在巴勒斯坦度过的童年时光,以及大萧条时期的物资紧缺,已经将她的人生观打磨得犀利而又理智了。
成长时期,我从未觉得我们家是穷人。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家一直都在为钱发愁。除了父亲的收入外,母亲也凭着自己缝纫的才能贴补家计。她可以把一个普通的服装样板变成一件美丽而又独特的东西。即使到了五十多岁,身体发福之后,她也从未停手,依然继续跪在客厅给衣服缝边,或者剪裁样板。
她看上去总是一副年轻的样子。她那头曾经及腰的长发,直到六十多岁都依然如丝绸般乌黑发亮。有一天,她毫无预警地就把头发给剪短了:“每天都要好好梳头,我都厌倦了。”我父亲迅速藏起自己的震惊,说他喜欢这个新发型。她这一生中,从孩提时起,就一直习惯用围巾把头发包起来。我习惯了她头戴围巾的样子,以至于乍看到她露出头发来,竟然认不出来。
她的肤色比大多数人要深,但肤质光洁细腻。她的眼睛小而犀利;她的牙齿有点儿不整齐,这让她不怎么敢露出笑容。因为不怎么笑,而且嘴唇也薄,人们总觉得她的神情中流露着不以为然的样子,但事实却鲜少如此。
她因为减肥失败而感到沮丧时,我父亲安慰她说,他就喜欢她“漂亮丰满的样子”。“一个男人要带着自己的女人在舞池中转圈,总得有个下手的地方才行啊。”他会这么说,然后抱起我母亲,带着她转起圈来。她会叫他放她下来,免得伤到他的背,但她的笑容和压抑的笑声都说明了她的喜悦。
我父母几乎从不争吵。即使偶有争吵,主题也通常是我父亲的赚钱大计。他会生出一个念头,比如当第一个电视机销售商,然后就信心满满地大谈特谈他的计划,但一旦遇到阻碍,比如没办法筹措到需要的资金,他就会很快地失去兴趣,从此闭口不提此事。我父亲是个梦想家,而我母亲却务实而且踏实,一直都在为了让我和哥哥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奋斗。
那天晚上上床前,我蹑手蹑脚地溜回到楼下去欣赏那些玫瑰。房子里暗沉沉的,只有街灯透过客厅窗户照进来的些许光线。暗淡的灯光下,花的色彩和娇艳都显露不出来,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轮廓。只有一阵花香隐晦地暗示着视觉的不可靠,让人想起玫瑰的娇艳。
回到楼上,我撞见了刚洗完澡从浴室出来的母亲。“我太兴奋了,睡不着,”我说,“我必须得再看看那些玫瑰。”
“索尔是个出色的年轻人,而且非常在乎你。”
“我对他的喜欢比对其他任何人都多。”
给了母亲一个晚安吻后,我就回到床上去了,庆幸她没有问我爱不爱他。我知道她是不会问这种问题的,但我却已经开始自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