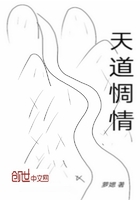直到永和宫的大门近在眼前,灵璧几乎是跪着从肩舆上下来,她周身的力气皆被抽去,青筠哭着将她扶起来,光怪陆离的人跟在她身侧,搀扶着她,拉扯着她,将她送入正殿。
不知是谁站在门口,叫了一声妹妹,灵璧看不清,只有躺在床上的那个小小人影……
“胤祚……”
她叫了一声,听见的人皆落下泪来,灵璧推开青筠的手,扶着门框走进西梢间,世界一片黑白,唯一的亮色是红的,鲜红的、粘腻的、温热的,血,从胤祚小小的头上涌出,那么多,从纱布里渗出来,染红他的小脸、他的脖颈、他的衣襟……
怎么会有这么多血呢?灵璧伸出手,狂乱地擦拭着血,企图用自己无力的十指阻挡那血的涌出,可是没有用!
没有用啊!那血顺着她的指缝涌出,一如胤祚的生命,如同指间沙,不断流逝。
“不会的,”她捧住胤祚的肩膀,将他抱住,“不会的,胤祚,你看看额涅啊?”灵璧摸着胤祚曾经黑漆漆的眼,抚过他浓黑的眉,“你,你怎么不给额涅笑了?”
胤祚,他是那么乖的孩子,只要额涅抱着,他就笑。
“额涅抱着你,你给额涅笑笑,好不好?求你了……求你了!额涅最疼你,你给额涅笑笑!”
嘶哑无力的哭号响彻整个大殿,灵璧抱着胤祚逐渐冷却的身子,那冷侵入她的体肤、她的心肺、她的魂灵,几乎将她撕扯成了碎片。
不能活!如何活?
皇贵妃、安嫔拦住要上前劝阻的荣妃、端嫔、布贵人,皇贵妃以从未有过的冷静语调道:“没用的,胤祚是她的半条命,没了,她就死了一半儿了。”
端嫔哭得双目红肿,“胤禛呢?快让四阿哥来劝劝啊!”
皇贵妃回神,她已是病骨支离的人,却慌忙带人去寻四阿哥。
可无论是谁来,都没有用了,灵璧将每个人试图接近她的人推开,她无视了胤禛的眼泪、无视了皇贵妃的怒吼、无视了端嫔的劝慰。从天光大亮到日暮沉沉,灵璧只抱着胤祚,干枯的眼里流不出泪来,只余无尽的绝望与哀伤,她不许任何人来碰,内务府带了人来,却被她赶走。
曼冬、元冬小声啜泣着将她砸碎的瓷片收起来,唯恐瓷片扎伤她,夜已深沉,死亡的气息弥补于曾经祥和安宁的正殿。
终是茯苓、青筠端了热水进去,茯苓将灵璧凌乱的鬓发别在她耳后,“主子,六阿哥骑马,肯定出汗了,咱们给六阿哥洗干净,好吗?”
再怎么说,也要让六阿哥体体面面地走啊,茯苓不敢说,勉强咽下冲口而出的呜咽,温声道:“主子,您松松手,咱们给六阿哥擦洗擦洗。”
灵璧迟登登看向怀中的胤祚,鲜血在她手上凝结,满是血污的手覆上胤祚被血块斑驳的小脸,“是啊,咱们胤祚可是干净的孩子,帕子拿来。”
青筠忙绞了帕子,递给灵璧。
皇帝是在和厄鲁特部宴席散后,才听闻胤祚殁了的消息,梁九功惊慌地看向他,皇帝脚下一软,从汉白玉台阶上倒了下去,若非裕亲王在侧,定是要摔个头破血流。他摆了摆手,双眸之中是可怕的空洞。
外男不得擅入后宫,裕亲王将皇帝送至日精门,对着梁九功点了点头,带着人去了箭亭:好端端的,阿哥怎会从马上摔下来,必得彻查!
皇帝匆匆赶到永和宫时,灵璧正跪在地上,她的背影看起来那样瘦小,如同狂风之中,不耐摧折的一朵蒲公英,风再大些,她便要折断、消散。可她的动作看上去又是那样虔诚,一下、一下,似乎将那些夺去生命的血擦干净,她的胤祚便能跳起来,抱着她,亲昵地挨挨蹭蹭,在她怀里撒娇,求她给自己唱悠摇车、吃梨丝缠金糕。
皇帝悄无声息地走到她身后,待看清胤祚的模样时,哽咽出声,那曾经是一个鲜活的、调皮的孩子,他不怕自己,是唯一一个叫自己阿玛的儿子,可是眼下他满面青灰地躺在地毯上,了无生息。
皇帝屈膝蹲在灵璧身侧,伸手环住她纤细的脊背,颤声道:“灵璧……”
灵璧却听不到了,她只是认真地、机械地擦拭着胤祚的身子,将青筠拿出的那件元青色衣裳给他换上,缥缈的、沙哑的歌声响起:“吊膀子,拉硬弓。要拉硬弓得长大,快睡呀,好长大,长大把弓拉响呀!拉响弓,骑大马,前敌去找你阿玛。阿玛出兵发马啦,出兵发马打罗刹。大花翎子亮顶喳,功劳分给你爷俩。”
她轻轻地唱,从暗夜沉沉,唱到天光大亮,她一天一夜滴水未进,嗓子干痛得几乎出血,可是她还是唱着,胤祚最喜欢听着这首歌入睡了。
一夜过去,皇帝下巴上生出淡青色的胡茬,梁九功引着裕亲王走到门口,皇帝揉了揉脸颊,“查得如何了?”
裕亲王压低了声音,“奴才在马鞍子里寻到了银针,马身上也有被针扎过的痕迹,想来是马受疼,一时克制不住,把六阿哥摔下去了。”
吊着手臂的太子赶来,他为了保护从马上摔下来的胤祚,飞身去接,却不想被栅栏和胤祚的体重双力伤到,小臂骨折,手腕脱臼,“皇阿玛,此事绝不是这么简单!”
皇帝看向他,“疼吗?”
太子压抑着悲愤,“儿子连弟弟都不能保护,疼算什么!儿子只觉得自己没用!”
皇帝长叹一声,眼中满是恨意,“查!上驷院、内务府全部查!看这根针,是怎么留在马鞍上的,制作马鞍的奴才全部锁拿下狱!一一拷问!”
裕亲王对着李太医招了招手,李太医忙活了一夜,此时眼底血丝密布,他揖手道:“皇上,太子所言非虚,此银针确实有古怪,微臣以银针刺小鼠,那小鼠竟似疯了般的在笼子里乱窜,不多时便死了,口鼻处皆有血,此针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