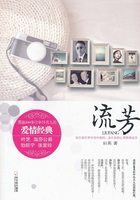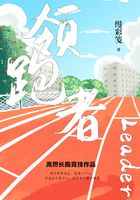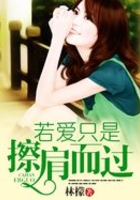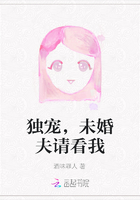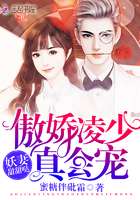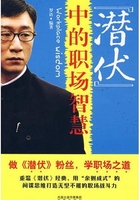一
我的《中国人口发展史》在去年出版以后,碰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编辑先生希望我组织一些书评,而且最好能在影响大的报刊上发表。这自然是很正当的要求——出版社不怕赔钱,以很快的速度、很讲究的印刷和装帧出了你的书,现在到了让行家来说话的时候了,你得让别人来证明一下书的质量呀!再说,书的销路、出版社的声誉、编辑的水准等,都需要这些书评,这是而今的通例,拙著自也不能例外吧!但这着实使我伤脑筋,找谁?写什么?
当然最好要找名家,名气越大,写出的书评影响越大,拙著的知名度无疑就越高。可是名家人人是忙人,又基本都是老人,搞我这一行的人本来就不多,目标更为集中。一位前辈告诉我,请他写序言、评语、鉴定一类的应接不暇;要请他们花时间看完30多万字,再写一篇文章,实在于心不安,不敢启齿。办法还是有的,我替季龙(谭其骧)师处理来往信函中就曾不止一次收到过对方已经“代拟”妥的文章,只要谭老签个字就行了。我照例都是退回去的,自己岂能这样做?自告奋勇为我写书评的朋友不是没有,只是目前知名度还差些,不知大报刊的编辑是不是看得上眼。所以我一直不开口,免得让他们做无效劳动。
而今的书评,老实说合格的极少。除非存心与你“过不去”(并无贬义,只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一般都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赞扬,余下这百分之几虽像食盐之于佳肴一样不可或缺,却绝不会有食盐那样的味道。即便是批评文章,也往往是小骂大帮忙,甚至是与被批评者串通了的双簧,只待读者上当,好打开书的销路。这倒不是文人无行,大多也是被“经济规律”逼得急了的下策。这类书评我一般是不看的,所以我很怀疑,别人写我的又会有多少人看?欢迎批评的话我说过不止一遍,真正求得友人的批评并且愿意写成文字却并不容易。
一拖已近半年,还无法向编辑先生交差,下一本书倒快出了,眼看旧账未清又要添新账。正为难间,《读书》登门索稿,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何不将写书的经过做一番自白,让读者对拙著的来历有所了解?这样虽不无王婆卖瓜之嫌,总比让人写、让人读那些逢场作戏的书评八股强些。如蒙《读书》不弃,编辑先生的债大概也可算还了一半吧!
二
我对历史的兴趣开始于读高中时,但只是兴趣而已,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曾经觉得应该将帝王的谥号、陵号、尊号或习惯称号与纪年编在一起,为此花过不少工夫。后来又发现北洋时期政府的更迭无工具书可查,想试着编成表格。最后自然都没有完成,不是知难而退,而是兴趣转移了。尽管当时少不了对未来的种种梦想,却从未做过研究人口史的梦。
十几年后的1978年,当我成为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的研究生时,我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地理,具体方向还没有确定。第一学期时先生给我们讲《汉书·地理志》,提到志中户口数字的价值,我觉得很有意义。课程结束时,先生要我们每人选一个郡试做一份注释。为了完成作业,并能在户口数字方面有所发挥,我特意将整部《汉书》翻了一遍,找到了一些与户口有关的资料。看了以后,却对《地理志》中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是西汉户口最多年份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不久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看到他也有这样的看法,不过王氏并没有举出具体的证据。于是我将自己的理由写成一篇短文交给谭师,他认为我的说法可以成立,收入了《复旦学报》的一期历史地理专辑。
这使我对西汉的人口问题有了更大的兴趣,就想读一些前人的论著。但查找的结果却使我大失所望,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劳干发表了两篇论文(《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两汉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册,1935年12月)以后,还没有什么超过他的研究成果问世。而某些已被视为定论的说法,如西汉初只有600万人口,虽然得到梁启超的肯定,却是毫无史料根据的臆断。这时我萌生了研究西汉人口的念头,并就已经发现的几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谭师看后就问我:“何不在此基础上写成毕业论文呢?”这无疑坚定了我的信心,就此确定了研究的方向。到1980年9月,我在谭师的指导下写成了《西汉人口考》,对西汉人口数量的变化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次年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并成为我的硕士论文。当时离毕业还有一年多时间,我除了当谭师的助手以外,就继续研究西汉人口,将范围扩大到人口的分布和迁移这两方面。1982年3月,我读谭师的在职博士生,因为有了前一阶段的基础,所以到第二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此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评阅我的论文时,有好几位老前辈鼓励我继续努力,并希望我能从西汉往下研究。就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几天,受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资助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人口”丛书编委会在南京开会讨论历史人口部分的撰写工作,邀我到会。当时我还不知深浅,在会上做了半天报告。会议结束时,我接受了在谭师指导下撰写《中国人口·总论》第二章《历史人口》中1911年以前部分的任务。这部分计划的字数虽只有数万,却涉及中国人口史的绝大部分,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原来的范围。于是我酝酿着全面研究中国人口史的长远计划,写一部中国人口史的梦想也开始了,时为1983年10月。
但在初步摸索之后,这个念头就有了动摇。尽管我事先对历代户口数的种种难解之谜已有所了解,却没有料到困难竟如此之大。研究了一下东汉的数字就感到束手无策,三国、南北朝的更无从入手。我越来越觉得像走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岩洞,其大无边,不知尽头在何处,也不知脚下的路是通向哪里,寻找回到洞口的退路已经与发现新的出口同样困难了。
三
1985年7月,我去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目的之一就是借他山之石,来攻中国人口史的难题。
我在写硕士论文时,从王业键教授讲学的报道中得知何炳棣教授《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一书的主要观点,感到很有说服力。但在上海和北京的各大图书馆中却借不到这本书,所以无从研读。因此到哈佛后的第一周,我便迫不及待地读完了此书。对书中的内容和观点我还来不及消化,使我震惊的倒是国内学术界的闭塞和保守。
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学者重新发现了清初户口统计数中用的是“丁”,而不是“口”,因而当时的实际人口应该是“丁”数的好几倍。但不久就有人指出,早在几十年前萧一山、孙毓棠等人就已经有过正确的结论。接着,争论转入“丁”与“口”的比例问题,并且至今还没有取得结果。可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步入了歧途,因为清初甚至明代大多数时期的“丁”与“口”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比例关系,而何炳棣这本出版于1959年的书已经做了很严密的论证。所以这场看似十分热烈的讨论,其实不过是重复二三十年前的认识过程的无效劳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我在美国一些大学中问那些中国学研究生时,他们几乎都知道“丁”的真正含义是“fiscal unit”(赋税单位),而不是“population number”(人口数量)。
我丝毫无意贬低我国的学者,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长期的封闭,这使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学者既没有了解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条件,也失去了学习的能力。我也并不认为对何氏的结论不能提出异议,但不应该置之不理,因为确实有人根本不愿意了解这些,却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这大概是长期封闭形成的一种特殊心态吧!
我参观了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和图书馆,发现在那些被世人誉为一流水准学府所列的中国人口史研究文献中,很难看到中国人,特别是大陆学者自己写的论著,即使在收藏宏富的大图书馆中,也几乎没有中国人写的中国人口史著作。语言和交流上的障碍自然是原因之一,但事实上我们的确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书来。一些我们有条件研究的课题也没有进行,应该取得的成果却让外国学者捷足先登,而外国学者已经发表的论著我们又长期不闻不问,作为一个中国人能不感到痛心?能不为之内疚吗?
1986年春,我参加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次讨论会,听来自纽约的B教授报告中国历史人口的数量和分布。他的报告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却相当狂妄自大。他大言不惭地声称从不采用中国学者的说法和证据,尽管他所用的历史政区图和分地区的人口数据分明是取自中国人的著作。在回答我们的批评时,他竟说:“我不需要任何证据,我认为我的说法是正确的。”还表示与中国学者没有共同语言,“或许我们的学生才能一起讨论”。
像B教授这样的人,我至今还没有遇见第二个,但那天的情景是我终生难忘的。只要我们还没有拿出举世公认的中国人口史研究成果来,B教授之流就不会绝迹,更何况世界上也还没有一部高质量的中国人口史。所以在我重新踏上祖国的大地时,尽管依然没有发现通向出口的捷径,但已经不存在任何返回入口的念头了。
四
在完成《中国人口·总论》第二章的数万字初稿时,我已深知中国人口史留下的空白和必须重新研究的问题太多,要是没有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要写出一部高质量的中国人口史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准备先从人口的迁移入手,写出一部中国移民史,作为中国人口史的一部分。但这样一部人口史既不能在短期内完成,目前又很需要一种比较简明的中国人口史,所以就产生了写这本《中国人口发展史》的动机,并且在我的梦做了九年之后,即1991年问世。
这本书是介于《中国人口·总论》第二章1911年前部分和我所梦想的人口史之间的中间产品,或者可称为一项阶段性的成果。正因为如此,我能写入书中的只能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止的研究结果,以及国内外已发表的有关论著中我所认为是正确的那部分。与国内外已有的有关论著相比,自认为有所进步、有所贡献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论述了中国人口史的空间范围、时间范围和具体内容,并以此为框架撰写全书。与以往一些局限于人口数量变化的论著相比,内容更加全面,涉及一些前人尚未注意的方面。
第二,在论述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力图纠正一些长期沿用的错误成说,如所谓大禹时的人口统计数、《周礼》中的人口调查制度等。同时对历代官方户口统计数、方志中的户口数和家(族)谱中的人口数据的性质和价值做了较系统的分析,有助于人们区别历史上的户口数与实际人口数,使中国人口史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上。
第三,对自公元前3世纪来的各个主要阶段的人口数量确定了大致的范围,其中不少是前人从未提出过的,如从秦汉之际以来各次人口谷底的估计数;有的是与以往的说法不同的,如明代人口的峰值等;有的是巩固了已有的结论,如宋代人口,根据我新发现的论据,我认为铁案可定,颠扑不破。
第四,在人口构成、再生产、分布和迁移方面,对史料的发掘和运用做了一些尝试,尽可能使现代人口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对应的位置。尽管有些还只是极其粗略的估计,有的只是出于直觉的假设,但对研究方法和学科构建不无意义。
至于错误和缺点,当然是客观存在,但这还是请读者们来指出。因为在主观方面,我是尽量要避免的。如果明明知道,或者已经发现了还保留着,岂不是与读者开玩笑,和自己过不去吗?
中国学者在自己的论著或报告的前后,往往要说其中必定有很多错误一类的话,而西方学者又会大惑不解:既然有那么多错误,还有什么发表的必要,为什么自己不先纠正?其实,大多数作者的本意和我并无二致,自己写的、说的岂但不错,并且必定是有发明、有贡献的,却不愿坦率地说出来,唯恐有狂妄自大之嫌。我以为大可不必,所以直截了当说了,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
五
对于我的同行和相关专业的读者来说,上面这些话已足够了,甚至是多余的,因为该看的会看,能用的会用,要批评的你也逃不了。但对大多数非专业的读者,我还想说上几句,这本书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没有关系,你们大概绝不会花上6.65元去读这30多万字。
简单地说,可以了解中国人口的过去,知道今天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中国人是怎样发展来的。这样说可能还过于抽象,那就谈几个与今天有密切关系的例子吧!
在今天讲中国存在巨大的人口压力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政府高级官员也一直在说人口形势相当严峻。但在50年代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建议要适当限制人口增长时,却受到了从最高领导到专家学者的一致批判。这当然有复杂的政治因素,但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潜在的人口压力也是事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不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
西汉从公元前202年至公元2年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是7‰左右,如果这个今天看来相当低的增长率保持下去的话,到公元75年中国的人口就会突破1亿,而不会迟至12世纪初的北宋。如果1850年后的中国人口还是以清朝前期的速度以每年约10‰递增的话,那么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时就该有7.45亿,1953年该有11.29亿,而不是普查结果的5.83亿。如果从公元初开始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2‰,而不是实际上的不足1‰,那么今天的人口就会接近32亿。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数字和假设实在算不上什么危言耸听,因为同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人口增长率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前23年中除了1960年外都超过20‰,厉行计划生育的1987年也还有14.8‰。
这些理论上的高峰之所以没有出现,竟完全是天灾人祸的功劳。如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到解放战争结束,近百年间的天灾人祸使中国少增加了四五亿人口,仅太平天国战争这11年间损失的人口就有1.12亿。所以到1953年人口普查时,有6个省的数字比1850年还少,其中包括号称鱼米之乡的浙江,而江西的人口竟下降了31.5%。
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人类已经不可能,也不需要靠天灾人祸来调节自己的增长的时候,消除人口压力的主要手段就只能是计划生育了。
人口压力的大小当然是与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它是与生产的发达程度成反比的。中国历来的人口稠密区一般都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相反,人口稀少区倒基本是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水平也不高的地方。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不一定发生在人口最稀疏的地区,却从来没有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爆发过。以长江三角洲和浙北平原为例,这里早在东晋南朝时就已成为人口较稠密的地区,从五代以来一直居全国人口密度的前列,明清以来更稳居首位。从五代以来,该区又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生活最富裕舒适的地区,从来没有发生过稍具规模的农民起义或破坏性的暴乱。主要原因无非是两点:精耕细作的高产农业生产了充足的粮食,发达的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养活了大量非农业人口。
所以,人口压力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影响社会的发展,但并不是人多了就一定会穷,一定要乱。在同样的自然资源条件下,不同的经济模式或生产方式完全可以供养不同数量的人口。这在中国历史上就能找到有力的证据,也能给我们以启迪。计划生育固然不能放松,但彻底消除人口压力的根本途径还是发展生产。在正视中国严峻的人口形势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
这些大概是每一位关心中国人口问题和前途的人所乐意了解的吧!那么本书也应该是他们所乐意阅读的。当然,对一般读者来说,全部看完可能会感到枯燥,那就不妨选一些看,或者先从最后的余论看起。
六
《中国人口发展史》出版了,但我的人口史梦想还远没有实现,我的目标是一部大型的、世界第一流的中国人口史。作为基础研究的一部分,我与同事研究和撰写中国移民史的工作正在进行,一部约50万字的《简明中国移民史》已经交稿,不久也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多卷本《中国移民史》的前两卷即将脱稿,后三卷可望在这两年内完成。我希望接着就能联合国内同行开始这项准备已久的工作。
但是一些基础研究目前还难以进行,这本来是不可缺少的。例如,如果我们能对全国现存的家(族)谱按随机抽样的原则选取一部分,将其中的人口数据建成历史人口数据库,中国的历史人口研究就完全可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在技术上并不存在太大的困难,所缺的就是经费和人员。
我不禁想起了前年访问法国历史人口中心的见闻。法国的历史人口研究成就是世界公认的,法国学者正在进行一项巨大的工程——收集数百个家族300年来的人口数据,建立历史人口数据库。当我问到他们的经费来源时,意外地得知,其中工作量最大的收集资料和抄录卡片竟主要是由退休人员义务承担的。
中国的家(族)谱资料远比法国丰富,起点也早得多,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持续500年或更长的历史人口数据库,足以代表当时的上亿中国人,这将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早在1931年,袁贻瑾就利用广东中山李氏族谱的记载,制成了该家族1365—1849年的生命表。多年来,我国台湾的刘翠溶和美国的李中清(James Lee)等人已在进行这方面的实验。但这样一项巨大的工程显然不是几个人所能完成的,需要更多的同行共同努力。
1990年8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会议上,秘书长夏蒙夫人邀我参加委员会。面对着100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委员,我作为唯一的中国人宣布了我的《中国移民史》计划。在写完这篇文章的两星期后,我将再次访问巴黎,向法国同行做我们的研究报告。我还收到了历史人口委员会中唯一的一位亚洲执委、日本的速水融教授的邀请,参加明年初在东京召开的“1500—1900年亚洲人口讨论会”。我最大的遗憾是参加这些活动的中国学者太少了,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学者更快地走向世界。
1985年在美国第一次看到别人用电脑写英文论文,觉得我们能用电脑写中文论文大概还很遥远。想不到《中国人口发展史》成了我用电脑写成的第一本书,这已经超出我当年梦想的范围了。所以我更加相信,随着人类的进步和中国的发展,我的人口史梦将不会是梦,尽管这个梦已做了十年,或许还要做上个一二十年。写到这里,泪水突然滴落键盘,我只能就此打下一个句号。
1992年4月22日零时于寓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