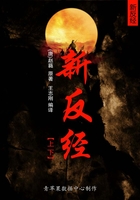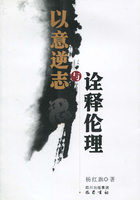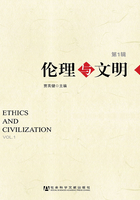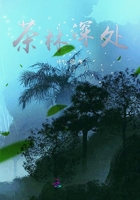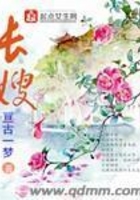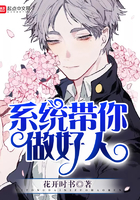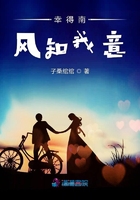巴门尼德的“存在”范畴是针对赫拉克利特的学说提出的。“存在”范畴的起源是希腊人对世界统一性的追求。这种追求在爱利亚学派诞生之后,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从爱利亚学派开始,对世界的具象性推测,把整个世界归之于一个或几个经验物的自然哲学开始被超越了。自然哲学对世界统一性的追求因其以个别经验物来表述“阿派朗”,以具体指称抽象,所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始基”只能以抽象的方式被表述,而抽象的方式就意味着用概念来表述。爱利亚学派就是这样一种表述的开始,尽管这种表述还没有完全摆脱具象性的思维。希腊哲学到此“开始”了一个方向性的转变,由自然哲学向“ontology”(存在论)的转变。这一转变的起点,是“存在”范畴的提出,这一概念的提出也成了西方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
爱利亚学派之思想的起点是对“一”的独特认识,亚里士多德作了如下归纳:
还有些人却认为万物只是“一”,虽然在他们说法的优劣或者和自然事实是否一致上,彼此并不一样。讨论他们和我们当前对原因(始基)的研究并不合适,因为他们并不像有些自然哲学家那样肯定存在是“一”,它又是从作为质料的“一”中产生的,他们说的是另外一种意思;别的那些自然哲学家要加上变化,宇宙是在变化中生成的;而这些思想家却说宇宙是不变的。可是这些是对我们当前的研究密切相关的:巴门尼德看来是牢牢抓住作为逻各斯的“一”,而麦梭里说的是作为质料的“一”,因此前者说它是有限的,后者说它是无限的。而塞诺芬尼是第一个说出“一”的,但他没有做出清楚的说明……[28]
这个“另外一种意思”意指什么呢?
塞诺芬尼(又译作“色诺芬”)第一个提出了“一”,而这个“一”又和神纠缠在一起。塞诺芬尼的全部理论的核心集中在他的残篇(23)—(26)中:“有一个神,它是人和神中最伟大的;它无论在形体上或心灵上都不是凡人(DK21b23)。神是作为一个整体在看,在知,在听(24)。神永远在同一个地方,根本不动;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对他是不相宜的(25)。神用不着花力气,而是经他的心灵的思想使万物活动(26)。”[29]
塞诺芬尼思想表面上是一神论,但其实质,是一种寻求更高统一性的尝试,是对“始基”的神秘表达。希腊人把自己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归于一位神,如火的使用、培栽、酿酒等,同时把整个自然存在归之于诸多神。当塞诺芬尼说有一个不动不灭,单一整全的神时,他开始把宇宙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并试图从作为社会、自然原因的诸神背后寻求更加普遍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神”,虽然仍然用了“神”这一拟人化的意象,但它本质上是抽象的,因为除了“神”这一意象对它的限制外,它是无限的。对于从多神到一神这一过程,恩格斯说:“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越来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则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30]恩格斯想表明,自然在抽象思维的发展过程中被蒸馏为“一神”。现在,离哲学的真正诞生只有一步了,那就是把“神”这个最后的意象也抽象掉,完成这一步的是巴门尼德。
巴门尼德用一个抽象的概念“存在”取代了“神”,但麻烦的是,思想一开始就陷入了和语言的冲突之中,因为被我们权且译为“存在”的词,在希腊语原文中是系词“eimi”,以及其现在时主动语态第三人称单数estin;其中,性动名词eon,或加冠词To eon;还有其不定式einai。它们相当于汉语中的系动词“是”。
在汉语语法中,系词不能脱离表语和宾语而单独使用,也不能作为主语,而“存在”一词却可作为主语和谓语、宾语,唯独不能作系词,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为了避免以辞害意,我们暂停使用“存在”这一译名,而是以汉语系动词“是”来直译巴门尼德的“eimi”。这样既有助于我们从汉语的思维习惯中跳出,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存在”范畴在其本源处的意蕴。
巴门尼德在他的残篇中向我们提出一个范畴“是”。巴门尼德的前提是,首先承认有这样一个“是”,它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巴门尼德只描述这个“是”的特征,而不是追问这个“是”是什么,也不论证有没有这个“是”。这一描述集中在了他的著作残篇8之中:“还只剩下一条途径可以说,即:‘是’。在这条途径上有许多标志表明:因为它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会消灭,所以它是完整的、唯一的、不动的、没有终结的。它即非曾是,亦非将是,因为它即当下而是,是全体的,一和连续的。”[31]
巴门尼德在描述什么?被他描述的这个“是”究竟是什么意思?
有一种回答认为,巴门尼德所说的“是”是系词抽象化的结果,是把系动词“是”本身绝对化的结果。陈康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形象地说明这一绝对化过程:“这字所表示的意义可以从以下见出:设以‘甲’代表‘每一个’,‘甲’是‘子’、‘甲’是‘丑’、‘甲’是‘寅’……‘存在’只是‘子’、‘丑’、‘寅’……中之一,譬如‘寅’。‘甲是’绝不是‘甲是寅’……它也不同于‘甲是子’、‘甲是丑’……中的任何一个。‘是’和‘是子’、‘是丑’、‘是寅’……的分别,乃是前者是未分化了的,后者是分化了的。”[32]这样一种把系词绝对化的结果是,系动词“是”与主语相脱离,和表语式的宾语相脱离,摆脱了语法束缚而独立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但这样一种解释似乎把巴门尼德所说的“是”过于抽象化了,和巴门尼德对“是”所作的描述不相一致,不能解释为什么巴门尼德会对“是”做一个近乎具象性的解释。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从语义的角度“是”具体表示什么意思。汪子嵩等在《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作过词源和语义上的解释,他认为“是”这个词,也就是巴门尼德所用的eimi,它的本意“有显现、呈现的意思,包含后来‘存在’的意思”[33]。也就是说,“是”原来是一个实义词。俞宣孟先生说:“系词之被用之系词,是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实义词,它的三种主要意义——生命、显现、在场,具有对于所提到的东西的首肯、确认的意思,无论所提到的是人还是物。对物的首肯方式是指出它的显现、在场,对人的首肯方式除了上述表达外,还特别指出他是生命(活的,从自身中出来并活动和维系在自身中)。”[34]
汪子嵩、王太庆先生的结论与之相似,只是更广一些。他们说:“由此我们可以试图说明的‘是’的意思:第一,作为某个东西而存在(‘存在’是‘是’所包含的一种意义);第二,依靠自己的能力起这样的作用;第三,显现、呈现为这个样子。”[35]
以上的结论明显有海德格尔的影响(参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译,商务本,第71—72页)。通过这种字源学的再阐释,系动词“是”转化为实义动词“显现”,从而有可能将这一动词转化为动名词形式。这样,它就可以做主语和谓词了。
现在的问题是,在理解巴门尼德的“是”的时候,究竟是应将系词抽象化还是将系词实义化?这应当从巴门尼德著作的根本目的来探究。亚里士多德说巴门尼德的思想有“另外一种意思”,说他是牢牢抓住作为“逻各斯”的“一”,这很值得玩味。从巴门尼德思想的现有残篇看来,巴门尼德的思想和自然哲学家是有不同的,他不是寻找某种“始基”,而是力求指出一条通向真理之路。如何认识世界,如何从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中抽象出其统一性,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巴门尼德并不停留于将世界统一于一物,而是进一步地想到:“人们苟有所思,必有实指的事物存在于思想之中,‘无是物’就无可认识,无可思索;所以宇宙间应无‘非是’,而成物之各是其是者必归于一是。”[36]也就是说,要把整个世界作为统一体来进行理性认识,那么它的前提应当是这个世界“是”,而不是非“是”。这就是巴门尼德的那句名言:“一条路是,[它]是,[它]不可能不是,这是确信的道路(因为它通向真理);另一条路是[它]不是,[它]必然不是,我告诉你,这是完全走不通的死路,因为你认识不了不是的东西,这是做不到的,也不能说出它来。”[37]将这句话中的“是”转换为“显现”,那么意思就成为,世界(或许可以说——始基)只有显现出来,呈现出自身,只有当它存在着,才能被我们所认识。以此为基础,我们就可以理解巴门尼德的这句名言:“思想和‘是’是同一的。”
从以上的论述中,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巴门尼德所用的eimi及其变格翻译成“是”是恰当的,因为如果我们从“显现”的角度来理解eimi,那么,完全可能从巴门尼德的思想中发现一种新的思想因素,它同以往的思想方式不同的地方在于:以往的哲学(自然哲学)总是把“始基”当作某种经验物,某种感性存在的无定形体,而巴门尼德则开始追问“始基”的显现问题,把“始基”的“是”理解为一个“始基”显现自身的过程,并将这个显现过程和人对“始基”的理性把握结合起来,即把“是”的过程和“思”的过程统一起来。
但是,如果单纯地从“显现”的角度理解“eimi”,把诸存在者的存在都理解为“显现”,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种绝对化倾向。“eimi”作为系动词,它联系着主语名词和谓词,正如我们在具体用系词时总是说:某物是……它是不能脱离具体存在者而独立使用的。换言之,它是对某物的某种确证、确认,而这一确认本身我们可以理解为某物呈现出或显现出某种属性。如果把“显现”绝对化,把它和对具体事物的确认相分离,那么,这是不符合巴门尼德思想的针对性的。
巴门尼德提出“是”的学说,是针对赫拉克利特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都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任何东西都既“是”又“不是”,如同“活的火”,它在任何一个时间地点上都既“是”又不“是”。这样一种“万物皆流”的观点在本质上取消了事物的确定性。这样一来,就不可能认识事物,不可能获得真理。基于此,巴门尼德才提出了“是”,而不是“不是”。也就是说,出于对真理的追求,“是”一方面指事物首先要呈现自身,显现自身;另一方面,它要求被思考的对象必须是确定的存在者。因此,当巴门尼德用“是”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个概念至少暗含两种意思:第一,事物自身显现出自身;第二,事物是在场的持存[38],即显现之后有其稳定性。就第一层意思而言,如果将其绝对化,将“显现”认定为绝对的、永恒的,那么,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主张:事物“存在又不存在”。事物存在着,这我们不得不承认,但事物总是在变,总在永恒的显现、永恒消失的运动之中消逝,因而又“不存在”。这是巴门尼德不能同意的,所以他说“是,不可能不是”,即一个东西不可能存在而又不存在。在此,巴门尼德显然是不承认将“显现”绝对化的。
那么,他是不是完全倾向于第二层含义呢?如果将“eimi”的“持存”这一内涵绝对化,那么我们将面对这样的问题:凡持存者必定是在时空中的存在,是实体性,也就是物质性的,这种时空存在必定是变动的,因为物有其多样性,它们的生成和流变是现实的,不可否认的。这样我们就无法面对巴门尼德提出的“是”的标记:第一,它是不生成也不消灭的;第二,它是“一”,是连续不可分的;第三,它是不动的;第四,它是完整的,形如球体;第五,只有它是可以被思想的。[39]把“eimi”考证为“显现”显然是受到了海德格尔对physis/logos的阐释的影响,受到了海德格尔的真理观、存在观的影响。但海德格尔这样做,是为了给自身的理论找根据。为了确立所谓“思”的本然状态,海德格尔几乎把柏拉图之前的重要希腊哲学家的思想都阐释为对“存在”的原始经验,阐释为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解说:这样一来大家说的都是同一回事了。比如,他说:“人们总把形成(becoming)的学说划归赫拉克利特而认为是和巴门尼德尖锐对立的!其实,赫拉克利特是和巴门尼德说同一回事。”[40]这是一种先立其意,后辨其辞的做法,是主题先行式的解释,当然也有道理。但是,哲学家们说的真是一回事吗?哲学在发展,思维在发展,哲学史的任务不是笼统地说“大家说的是一回事”,而是理出每一个人和其他人所说的不同之处。
在此,我们遇到了理解巴门尼德思想最困难的地方:如果我们把他的“是”理解为绝对的“显现”,那么我们就把他和赫拉克利特混而为一,抹杀了他的理论的针对性。连带的问题是,如何将显现与上文所提到的“是”的标志联系起来;为什么要把这个纯粹的显现理解为“一”?如果把“是”理解为实体,那么我们就无法将这种时空中有限的实体(存在者)与不生、不灭、不动、不可分的、完满的“一”联系在一起。那么,要符合他给出的“是”的标记,就必须把它理解为至大而无外的宇宙体,但结果就会像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中指出的那样:“当宇宙实体或世界本原(始基)的概念在巴门尼德那里拔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拔高到存在的概念时,似乎要把个别事物同这个概念统一起来,其可能性是如此之小,以至于事物的现实性被否定了,这个统一的存在永远是唯一的存在。原来为了阐明世界而形成的这个概念,其内部已发展到如此地步,如果坚持它就一定要否定它原来要企图阐明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爱利亚学说就是无宇宙论:万物的多样性已沉没在这全一之中;只有后者才‘存在’,而前者只是欺骗和假象。”[41]
如果巴门尼德所说的“存在”(“是”)真如文德尔班理解的是一种作为“始基”的宇宙物的话,那么他的指责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一指责并不仅仅是针对巴门尼德的,这一指责适用于全部“始基”学说。但问题是,连亚里士多德都不认为“是”是“始基”,认为巴门尼德有“别的意思”。那么,巴门尼德到底在说什么呢?一方面,不能把“是”理解为纯粹的显现;另一方面,也不能理解为“始基”。这是一个两难境地,要摆脱这一两难境地,就必须回到巴门尼德的文本中去。
陈村富先生在《希腊哲学史》中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近代西方学者激烈争论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主语问题,这是从语法关系中提出来的问题……当巴门尼德用estin(it is)表述存在时,人们问这个‘it’是指什么?即‘存在’的主语是什么?”[42]有人认为是“存在”(第尔斯、康福德),有人认为是“没有任何特殊规定的,充满空间的总体”(策勒),也有人认为这是个无人称句(像it rains这样的句子)。对此问题陈先生认为这是一个虚假的问题,因为参与争论的人把范畴的含义与其语法意义混淆了,“对于作为表述‘存在’的estin,其中的It is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它们合起来才表述‘存在’这个范畴,根本不存在指什么的问题”[43]。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巴门尼德残篇中大量出现的estin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只有在后接不定式时才是没有逻辑主语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意思就转变为“it is possible to…”,在这个词作联系动词时是有逻辑主语的。还得结合残篇的语境来寻找逻辑主语,不能说没有逻辑主语。笔者认为这个逻辑主语不是别的,就是巴门尼德所说的“一”。
尽管巴门尼德的思想和探索始基的思想相比,确实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有一些不一样,但或许我们把巴门尼德与希腊人对“始基”的探索隔得太远了。不能说巴门尼德的思想与探索“始基”无关,一些早期的希腊哲学专家曾认为在巴门尼德所处的时代,人们还不知道物体和非物体的区别,如策勒。柏奈特认为,巴门尼德所说的eimi还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存在物,所以他认为应当把eimi译为what is,而不是更加抽象的being。文德尔班也认为,巴门尼德的“是”就是“实体性,即物质性”[44]。这样一来,这个“是”和希腊人的“始基”又有多大距离呢?
距离在于,巴门尼德的“是”确实有“始基”的意味,但巴门尼德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始基”上,而是对“始基”作了更进一步的抽象,进而研究“始基”如何显现的问题。这一抽象的结果,是将“始基”进一步抽象为“一”,把“始基”从经验物中解放出来。
塞诺芬尼的“一神说”认为,诸神是世界之诸多现象的原因,而一神是诸神的原因。“一神说”包含着对作为整体的世界之原因的概括。巴门尼德把“神”抽象掉而只剩“一”。这个“一”,它是对“始基”的进一步的“抽象”。对于巴门尼德来说,“始基”的存在是不可怀疑的,承认“始基”“在”是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是认识世界的前提。而“始基”作为世界的统一性,不应当是某种经验物,而应当超越于所有经验物。这种超越规定了“始基”只能是“元一”,而不能再有其他规定性。但这个“一”也不是黑格尔所说“是纯粹的抽象”,“始基”在巴门尼德这里摆脱了经验物的具体形象,但并没有摆脱经验物的实在性。换言之,巴门尼德所做的就是给“始基”换了个名字,将之命名为“一”,不是将“始基”纯粹概念化。这个“一”就是“it”,也就是estin的逻辑主语。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巴门尼德的“是”究竟在说什么。我们已经从字源的角度将“是”理解为“显现”,现在又将这个“显现”的逻辑主语认定为“一”,这样一来,巴门尼德所说的estin就是指“一之显现”。前面我们说过巴门尼德思想的本旨是探寻真理之路。“一”作为概念性的“始基”,作为世界的统一性,我们可以推演出它就是真理的本质,就是“不可动摇的圆满的真理”[45]。这样一来,“一之显现”就等同于“真理显现”。
前面我们将“是”释义为“显现”,现在将“显现”的逻辑主语确定为真理,为“一”,如此则“estin”的意义显示为:真理之显现,或“一”之显现。这样一来,巴门尼德的“‘是’,不可能不是”这个句子就可解释为“真理显现,不可不显现”。按此解释,则作为真理本质的“一”与其自身的显现是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并不存在绝对的不显现的“一”;唯当真理(或者说“一”)呈现出自身,才能被我们把握,它不可能不显现,因为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可能领会真理,思考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真理本质的“一”,“一”的显现和我们对真理的领悟与思考,是三位一体,不能分割的。依此观点再来看巴门尼德所说的“是”的五个标志,我们就可以把它们表述为:第一,真理之显现是永恒的,不生成也不消灭;第二,真理之显现是“一”,是连续不可分的;第三,真理之显现是不动的;第四,真理之显现是完满的,无处不在的,故形如球体;第五,只有真理之显现可以被思想,被表述,只有真理之显现才有真实的名称。
让我们逐一来看:
第一个标志,是对“一”之显现的绝对性的强调。“一”本身是抽象的结果,它是对在“生成”与“消灭”中的世界诸存在者之抽象,因而当然是不生成也不消灭的,而“一”及其显现是一体的。也就是说,显现是“一”的唯一规定性,或者显现即“一”,故而可以说“一”之显现是不生不灭的。
第二条标志强调“一”之显现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是一个整体。“一”作为最高抽象,如果是不连续的或可分的,那么它还没有达到对整体世界统一性的概括,而“一”即“一之显现”,“一”的无限性体现为“一之显现”的无限性,故此,真理之显现是“一”,是连续不可分的。
第三条标志说真理之显现是不动的。或者我们会问,显现本身是动词,怎么能说是不动的?应当这样理解:“一”之显现是均一的,没有变化的,由于“一”的不生不灭与不可分割性,故而“一之显现”就必然体现为匀一与无限。
第四条标志可以看作前三条的综合,“一”作为一切真理之本质,一切原因之原因,它具有最高的普遍性,因而它和它的显现(从表述上我们不得不用“一”和“一的显现”这种易引起歧义的说法。巴门尼德用了一个词来表示“一”及其显现,而汉语却不得不分开说。这会让人觉得此二者是两分的,但实际上二者一体的,是“estin”)是完整的。这第四个标志就是巴门尼德追求的“不可动摇的圆满的真理”。
第五个标志是我们将“estin”理解为真理之显现的学理依据。作为世界统一性的“一”,作为圆满的真理,怎样才能被认识被领会?在巴门尼德看来,要领会和认识真理,首先要有一个前提,即“真理显现,不是不显现”,如果真理不显现自身,那么真理的领会和认识就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理既显现又不显现,这将引起混乱,所以,真理必然是绝对的显现。以此为基础,巴门尼德推出:“所谓思想就是关于‘是’的思想,因为你绝不可能找到一种不表述的思想。”[46]这就是那个伟大的命题:“是与思想是统一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谈译名问题,将“eimi”及其变格统一译为“是”,这一译名重点突出了“纯粹的显现”这层意义,这一译名的好处在于传达出了“显现”的绝对性,它不带宾语,也无须主语,是无所依傍的、绝对的“过程”。这是以汉字“是”这一词传达“eimi”之原始意义的传神所在。但这一译法也有不妥之处,因为它把绝对的“是”和相对的“是”割裂开了。绝对的“是”是从诸多的系词“是”中抽象出来的,作为纯粹的显现,它既不带宾语,也无须依傍于主语,这一译法就“being”绝对意义而言,是准确的。但这一译法忽略了“是”总是某物,或者“所是”的“是”。正如巴门尼德在残篇中所说的:“没有‘是’在其中得到表达的所是,你便找不到思想。离开所是则无物是,亦不能是。”此译文以抛开所是而单纯地从中抽象出“是”,不把estin当作“it is”而只看作单纯的“is”。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巴门尼德“离开所是则无物是,亦不能”这一思想的,而且,将系动词绝对化、抽象化,进而赋予其实词意味,这里猜测的成分多而学理的依据少,而且没有结合巴门尼德哲学的针对性。这一点体现在把“是”绝对化,包含把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化”的倾向。将“是”与“所是”彻底割裂,这正是用“是”翻译“eimi”及其变格的问题所在。
再看原有的译名“存在”。这一译名的问题是明显的。汉语在使用“存在”这一词时,总是指时空存在,是具体事物的存在,因此,这一术语在汉语中缺乏抽象性,它总是和具体的意象结合在一起的,而“eimi”都是由系动词抽象出的,且系动词本身就是从实义动词抽象出来的。因此用“存在”译“eimi”,则eimi包含的“绝对的显现”这层意义传达不出来,而且,容易导致汉语读者将其视为具体的某物。这一译法也有好的一面:在西方语言中,系动词“是”有时态、人称语态的变化,还可以以动名词的形式充当名词;但在汉语中系动词“是”不能单独作名词,而且缺乏语法上的独立性,它只能充当主语和谓词之间的联系纽带。西方语言中系动词则有比较大的独立性,我们经常能见到这样的句子:“God is”“I am”等。这些句子中系动词用汉语“是”来直译是不恰当的,它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汉语系词必须带谓词,因为西语中的系动词除了语法意义外,还有“显现”、在场的实用意义,而汉语的“是”缺乏这一实词意义,用“是”来传达“显现”这层意思,是缘木求鱼。这时候用“存在”一词来翻译“eimi”,则其包含的显现、在场的实词意义,就比较恰当。
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存在”一词缺乏抽象性,和“是”相比,只是一种特殊的、分化的,或者说具体化了的“是”,用它来译“eimi”及其变体也不是很恰当。但是我们旧就主张用“存在”一词来译eimi/being。除了上文提到的实词意义外,“存在”一词最突出的优点是它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至少能够让译文通顺。这一点正是“是”缺乏的。而且,汉语有这样一种特点:任何一个单词都无固定词性,它的词性取决于它在句子里的位置,取决于它的功能,因而“存在”一词可以充当动词、名词乃至形容词,这是“是”不能比的。它能够传达“是”不能传达的“being”这种动名词(on)意义。从解释学的角度来说,尽管“存在”一词本身缺乏抽象性,但是我们可以对之进行抽象性的阐释(况且由于其在哲学文本中普遍出现,它已经被抽象化),可以赋予它“显现”这层意义,把它描述为一个过程。比如,在对海德格尔著作的翻译中用了“存—在”这种形式,就可以基本传达出eimi/being的原始意义,而无须强迫中国人接受不符合汉语表达的“是”。
采用“存在”这个译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是”只能传达这一范畴的源初意义,只是这个范畴的一个历史阶段,而从这个范畴的历史发展来看,从这个范畴后来的实体化、本体化来看,用“存在”一词更尊重这一范畴的历史发展。这一点将在“存在”范畴的历史展开中体现出来。
巴门尼德提出的存在范畴是对哲学的巨大贡献,为西方哲学确立了存在论的中心。巴门尼德之前的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对始基的探索具有明显的经验观察性质,而巴门尼德的研究则把这种探索进一步抽象化,并且将之推进到了人的认识问题。巴门尼德首次作了两个世界的区分:不真实的感性世界与真实的“存在”世界。前者是我们经验到的感性世界,是人们的“意见”,也就是感性认识的世界,它是变幻不居的、虚假的世界;后者是只有通过思想与理性才能认识的世界,它是真理的世界,是真实世界。这种区分对于西方哲学而言,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出现了存在与世界的对立,出现了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也就是意见之路与真理之路的对立,这样一种对立构成了西方哲学的真正起点。在这个对立的基础上,哲学的主要任务被确立了下来,如:两个世界的关系问题;两种认识(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后世所谓的“本体论”问题,也就是什么是“存在”的问题;真理问题等。
自巴门尼德以后,存在问题成为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因为“在后来的每一个世纪中,哲学家们都关心巴门尼德的存在论题”[47]。可以说,巴门尼德的“存在”确立了西方哲学的起点和中心。另外,巴门尼德为哲学确立了形而上学的方法。他的存在论赖以建立的前提是一个独断——“一显现,不可能不显现”,但他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以这个独断为起点进行理性推论,从概念本身中推导出概念的性质。巴门尼德是第一个正式从前提推出结论而不是独断地宣布的哲学家。这在哲学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是思辨哲学迈出的第一步。后来,这种方法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中,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甚至在黑格尔那里,都是最主要的方法。
如果对存在的理解还只是在最抽象层面上的诗性阐发,如果存在范畴还不能借助概念表达其内涵,我们就不能指望它能与具体事物的存在结合起来。就美学而言,对存在本身的思考还没有展开的时候,美的存在还不是问题。因而我们可以发现,古希腊的伟大艺术始终缺乏一种与之相应的理论反思,也就是从认识与观念的角度展开的理论概括,那是一个有艺术而没有艺术理论的时代。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我们并不认为古希腊人在艺术领域内处于一种“知的澄明”之中而不需要美学,而是认为他们缺乏反思美与艺术的必要的工具——概念及其体系。黑格尔曾经在什么地方说过古希腊哲学是“美的哲学”(也可译作“感性的哲学”)。他的意思是说,古希腊人只能以感性的形式进行理性思考,如以火、水、圆球等一个或者几个具体事物的意象作为思考的工具;然而,美学作为对感性事物的反思不能以感性的形式展开。那么,美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得了解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或者说,这门学科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美学这门学科是在18世纪由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命名的一门古老的学科。就从被命名的时间来看,它是年轻的,但就其研究的问题与研究的方法来看,它是古老的。按鲍姆嘉通的本意,这门学科是研究审美认识的学科,但实际上它一开始就和美的艺术审美活动结合在一起,是对美、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研究的学科。这种研究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首先,它要划定自己的对象,然后对对象进行解剖式的分析,而这个分析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进行判断的过程。比如,面对一个事物,我们首先对其进行判断:美还是不美,或者是不是艺术作品。其次,我们会分析它为什么美,会分析艺术作品的结构。这就是说,美学是从人的感受状态的角度对美的反思,是这样一种“知识”,一种“相关于感知、感觉和感受的人类行为的知识,以及规定这三者的知识”[48]。既然美学是知识,是反思,那么它必然是以概念的方式展开的,但现成的“概念”体系还没有诞生,因而在柏拉图之前不可能有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下以主体的感受状态为核心的“美学”。不能否认,在柏拉图之前就有对美和艺术的零星的思考,但这种思考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具象性的猜测,还不成其为“知识”,更不成其为美学,因此美学诞生的条件还不具备。对美和艺术的反思应当开始于这样一个时刻——具体事物的存在能够以观念的形式被表达。换言之,是存在者的存在被具体地分析而不是存在本身被抽象地表述的时候,因此,美学的诞生是和“拯救现象”[49]的努力结合在一起的,是在存在者的存在被揭示时才会有的。尽管此前仍有一些朴素的美学假说,但它们是猜测,而不是反思。因此我们认为在巴门尼德的存在观上,在“存在”还没有转换为具体的概念之时,还缺乏对美进行反思的基本思维工具。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样一种研究美的问题的理论趋势:思想的总体倾向是从存在论的角度探索世界的统一性。在这种探索过程中,存在论和宇宙论是统一在一起的,而希腊人最早对kalos(后来译为“美”,但这个词的源初意义为“完善”或者“圆满”)的探索完全来自一种宇宙论上的感受,是对世界整体的一种感受。他们在宇宙当中感受到一种完善与圆满,这个圆满状态的理论化表达就是巴门尼德对于“一”的描述。而后,通过对圆满的原因进行的分析,宇宙内在的规律性,可以被数学化方式表达的内在和谐,成为精神愉悦的本源。希腊人似乎天性上就易于从这种宇宙的和谐与完满感中得到愉悦。这就使得希腊人对美的性质的考察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根基扎在存在论与宇宙论之中,对世界之统一性的思考必定要贯穿美的领域,这奠定了美学的形而上学倾向。在巴门尼德及其之前的早期古典主义时期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朦胧而具有形而上学倾向的美的理论。比如,毕达哥拉斯对美的宇宙论式理解,赫拉克利特也把和谐与美归于宇宙的合乎规律性的安排。
这就是美学在希腊前古典时期的基本状态。人类的思维主要是在宏观的哲学格局中进行的,美学的发展还不可能,它只能作为人的其他追求,也就是宇宙论与存在论的附庸而被提出。但是,从存在论的角度对世界统一性的思考,从宇宙论的角度对世界整体性的感知,使得他们可以在存在论奠定的圆满状态上获得精神愉悦,并把对圆满包含的和谐、比例、中和、均衡等感受作为精神愉悦,或者说美感的原因。从这种存在论的状态,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巴门尼德之存在论中体现出的对世界之认识的粗浅的整体思辨性,使得对某个学科的专门研究还没有被提到思想的主要位置上,单独对美与艺术的追问与反思还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