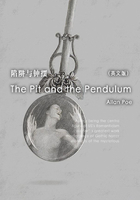一
柳元芷是有点名声的杂家,肚里藏了不少文坛内外的轶闻趣事,但他信奉述而不著,所以写出来的少。前些年退休在家,养花种草,搜读孤本,又是京剧票友,一口老生唱得字正腔圆。平日接待各路讨教的朋友,日子过得闲适而惬意。
市政协开会,柳老去参加。会结束了,他起身要离开,却看见市长桑雨眠从台上走下来,绕过一盆大铁树,一边朝他走来,一边招着手。柳元芷一愣,觉得市长像是招呼自己,想应,又觉得不妥,虽然他有点名气,也参加各种文化会议,但和官员没有多少私交,要是桑雨眠不是找他,贸然应允了,不是难堪吗?
他低了头,往前走,不料前面有个块头很大的人挡着,他想从边上擦过去,没想大块头一转身,撞上他。他倒退两步,跌进一张椅子里。柳元芷刚要爬起,一张眉毛修长的方脸出现在面前。
“没摔着吧?”
“没有,没有。”柳元芷平稳了身子,暗叫惭愧。忙中出乱,一时狼狈。看来桑雨眠正是找自己呢。
桑雨眠看他真没什么,放心了,说,“柳老当心,我有一事想请教你呢。”柳元芷忙表示谈不上请教。
桑雨眠引他进一个屋,在一张紫丝绒的长沙发上坐下来。两人坐下时,肩碰了一下,柳元芷感觉中他的肩膀还蛮硬。腥红的夕阳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投在他们的脚跟前。桑雨眠的脸上有些明暗不匀的凹影。
“柳老,你知道一个叫雪眠的人吗,三十年代末在上海的。”桑雨眠眼里透出期待的急迫神情。
柳元芷的思路刚才还在当下,一下被桑雨眠引进遥远的年代。他微微眯起眼,朝记忆深处去探寻。但脑子迟钝得很,沟沟槽槽似乎都被年代的尘埃填满了,而他的探寻像是秃了头的钻头,枉费力气,并没有发掘出期待的东西。
桑雨眠两眼攫住他,说,“从文化圈子里想,他是在那里活动的。”
柳元芷的脑袋有些发痛,这种发掘非常吃力,想停下,可又不甘心,一时就有些茫然。他看见一个圆头圆脑的人向他走过来,那人脸上抹着甜蜜的笑,像新开张的面包店里的一种果酱小面包,那人走路似乎不抬脚,但走得轻松,像是飘飘忽忽过来的。柳元芷收回目光,还是费劲地往记忆深处钻,历史的云雾是铁灰色的,他尽力把它们赶开,好像看见了几个穿青年装的年轻人,在旧上海的四马路上闲逛。他脑际深处一亮,仿佛某个断了很久的线路接上了。“哦!”他叫出声来。
“想起来了?”桑雨眠修长的略带银色的眉毛抖动起来。那个笑容像果酱面包的人也到跟前了,把脸凑过来,柳元芷认出他是市政府的秘书长舒阳。
柳元芷不肯定地说:“他是个作家吧?”
桑雨眠脸上的各块肌肉都鼓起来了,凹影不见了,“对,是个作家,一个现代派的作家。”
柳元芷想趁着脑际里的亮光多看一点,可是光焰在快速地减弱。他不无遗憾地说:“有这么一个人,常和蜜蜂派的艺术家在一起。他像是一个幽灵,看不清哩。”
桑雨眠笑了,说,“像幽灵?柳老说话幽默。你知道,他是我的大哥,胞哥呢。离开家乡时,他把姓拿掉了,大概一直没有再加上。”
“真的?”柳元芷也兴奋了,“他要大你不少吧?”他还想再发掘些,可脑袋里已经黯下来了。
桑雨眠说:“他出走的时候,我不过两岁。我八岁时,他回过一次家。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只知道他是一个现代派的小说家。建国后才听人说,他早就死了,害肺痨死在亭子间里,也不知道他当作家的成绩怎样?”他话说得很和缓,脸上的表情显得复杂、丰富。
柳元芷的眼光悄悄移开,不看桑雨眠,他为不能提供更多的情况而内疚。
“不急,慢慢来。隔了这么长一段历史,不容易一下想起。不过,我们柳老是有大学问的人,不会被这个难倒的。”舒阳用热烈的语气说。
柳元芷不能说全部同意他,但心里还是愉快的,因为秘书长当面说了他好话。
二
回到家里,柳元芷还在想这事。他想,兄弟情同手足,两人其实离得不远,却音信全无,一个死了,另一个却许多年后才得知。这一个现在身居领导位置,可是却无从了解另一个的生平业绩,不免感慨一番。过了几天,也就忘记了。
一天,他在整理中国瓷器的资料,听得园门外汽车响,刘妈来说,有人来访。柳元芷正在研究的兴头上,想避客的,没来得及,人已经进来了,来的是舒阳。
“噢,请坐。”柳元芷起来拱手让座,他想搬一张红木的八仙椅,一下没搬动,舒阳忙过来自己搬了坐。柳元芷心里好诧异,秘书长从来没有登过门,今天来干什么?
舒阳在椅子里坐周正了,灵巧地转动他坚韧有活力的脖子,说,“柳先生住的地方真不错,前有竹子,后有流水小桥,汽车要拐几个弯才进得深来,我看,足可称个雅庐。”
柳元芷心里怪高兴,嘴里却说:“哪里称得上,是个陋室嘛。”
舒阳没有多拐弯,说,“柳老,我来还是为那天桑市长问的事,想详细了解雪眠的生平。”
柳元芷说:“这事情有点麻烦,怕我提供不了多少。”
舒阳笑了,笑得得体、可意,说,“柳老,您是我们市里活的百科全书,又是早年从上海过来的,您要是不了解,还有谁会了解?这段历史,都在您肚子里藏着嘛。他是我们桑市长的胞哥呀,这些年他从来没有提起,现在才想到问一下。”
柳元芷说:“你来鄙室是不是桑市长——”他原来要说指派的,但发现不妥,改口道,“他知道的?”
舒阳连连摇头,像是怪他不懂机理,可是马上停止了,说,“桑市长管着全市上百万人的大事,当然不会再三叮嘱。再说,雪眠是我们这里出去的作家,他的创作是人民的财富,我们有责任发掘。”
柳元芷觉得“发掘”这个词他说得特别用力。他不是不想提供,而是觉得无从回忆。但是当他看见舒阳一双发亮的带点湿润的眼睛时,忽然有一种理屈感。他移开目光,几片叶子从树上落下,在蓑棚上粘粘连连,贴着窗扇滑下,好像并没有枯黄,还呈着青色。
舒阳说:“组织上委托您了,也只有您柳老能胜任。如果必要,将来我们还要盖一个纪念馆。虽说这不是急的事,但也要抓紧。”
第二天,开来一辆越野吉普车,停在园门外,轮胎上都是泥浆。来的是下面县里的人,说雪眠是他们家乡的人,出一个作家是县上的光荣,怎样都要请柳老先生把他写出来,那是柳老对小县的关怀和贡献。当前正在修县志,写入一个现代派的作家,对招商引资都有作用。
柳元芷冷笑一声说:“你们的鼻子真灵。”
来的人说:“那当然,不光鼻子要灵,还要有汽车的速度。”
柳元芷觉得来者比舒阳还难对付。他们赶二百多里路来,途中遇到暴雨也不停车,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那种情况下,跟他们解释什么都是很难的。而且,他们随车带来了火腿、肉脯、银鱼、阿胶。这些东西柳元芷当然喜欢,然而都和雪眠联到一起,他就没法消受了。但他们一箱一箱往屋里搬,柳元芷拦都拦不住。
再过一天,市文史档案馆来人,也坐了一个小时。
第四天,政协的资料室也闻风而动。
空了一天,给柳元芷喘了口气,紧接着,东江大学的中文系也发现雪眠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作家。柳元芷坐立不安了。
已经是深秋了,他到湖边去散步,寒风从湖面上嗖嗖地吹来,头皮一阵发凉。他头发已经很少了,可能是遗传因子作祟,他祖父、父亲都脱发,他不到五十就开始脱了,现在有点惨不忍睹了,中间一大块铮亮发光,像一个鸵鸟蛋,四周还剩一点稀疏的毛。他觉得今天的寒风太和他过不去了,慌忙逃回家,赶紧叫刘妈翻箱找无檐软帽。帽子找出来了,他接了就往头上戴,心里就有几分踏实。这帽子是他父亲留下来的,浅咖啡格条的,很有年头了,但保存得非常好。柳元芷戴上后不仅形象大为改观,而且感到十分温暖,冬天的寒风凉雨能奈我何,有一种进了安乐窝的感觉。
不时有电话打来,虽然说的都是不急不急之类的客气话,可是,柳元芷却看见了电话那头一双双急如星火的眼睛。他知道,这些人面对的是一枚生了斑斑绿锈的铜锁,在他们的眼里,他是打开铜锁的唯一的钥匙。
他给上海的施教授写信了。施教授又是柳元芷的前辈了,他学贯中西,而且在创作上富有实绩,是上海三十年代现代派的一方领袖。信寄出了,他却担心起来,施教授已年过九十,会回信吗?
没想到还真回信了,柳元芷拆信时不由手抖起来,心里怀着崇敬感。施教授的思路依然清晰,他说,是有雪眠那么一个人,但是与他交往不多,交往深的恐怕是戴望舒了。
柳元芷叫苦不迭,戴望舒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仙逝了,叫他哪里去找?就有很多天不舒畅,园子里的叶落得更勤了,又不愿一下坠地化作泥,在空中划着尽可能曲漫的弧线。打开台灯,是一桌子银光,刺得他睁不开眼。
可是各方面并不认为他这把钥匙失效,舒阳除了打电话,还派人来探望,说要耐心,有韧劲,举了个旁的例子,举的是发掘失传的中医理论。县里的吉普车又长途跋涉来了。
继续送火腿、松花蛋、阿胶。柳元芷张着两手拦,说,“不用,不用,上次送的没吃完呢。”来的人说:“柳老,你多吃点。我们乡下多的是。”还说县里新盖了一个疗养院,条件不错,周围风景非常好,如果柳老愿意,可以去那里住着,慢慢回忆,慢慢写。
柳元芷端端正正坐在书桌前,窗开着,泥地里长着几株菊花,已近凋零,窗玻璃上有水迹,莫非晨露没干?他伏下头,额头碰到玻璃板,一片冰凉。便循着上次的思路往脑子里搜索,目光不敏锐,腿也疲软,仿佛是在尘埃腾扬的旷野上摸索。不由茫然,抬头,见阳光照在窗玻璃的水迹上,映出七色的光晕,须臾扩大,光晕中走出一个白脸的青年,眉毛又细又长,像铅笔随便划的一条线,时不时神经质地打个结。
“哦,雪眠,我看见你了。”柳元芷禁不住在心里呼喊,他终于看见他了,在尘封铜锁的记忆里,他睁大老眼,不敢漏一点光。他看见雪眠走过三马路的一个拐角,一个野鸡从电线杆后出来,吊住他的膀子,他甩手走开,雪眠走进一家小酒店,从衣袋里摸出最后几枚铜板,放在桌上。后来他醉倒在桌旁,像一滩泥。
柳元芷盯紧了雪眠,怕他在光晕里消失。忽然觉得不对,白脸的青年像是姓汪,那么他就是闽颜,也可能姓周,那就是跑马厅里输掉氅子的曹大洋了。窗玻璃上的水迹眼看要干了,白脸青年转过身,朝远处走。柳元芷只看得见他渐渐模糊的背影,急急喊道,“你是不是雪眠?”
不见回答,水珠挥发了。
柳元芷呆坐一会,又去翻那个年代他曾参与编辑的一些刊物,翻到小说一栏。那时的文人喜欢随便用笔名,用一个扔一个,一点不可惜。他查到的有子尚、孟垅、海啸、孔尼、瘦菊、亚夫、笑梅等等,不下百个,不知道哪些是白脸青年用的,也不清楚白脸青年真是雪眠吗,可惜他死得太早,才弄得无处查实。
正在惆怅,舒阳的电话到了,转弯抹角问进程。柳元芷说:“想起一些,可是年代久远,回忆不真切了,分不清哪些小说是雪眠写的。”
那一头嗯嗯了好些声,说,“这是一个很细致很费力的工作,柳老,辛苦你了。但是,真要分不清了,也不要缩手缩脚。中国乒乓队拿世界冠军。背后有多少队员在当无名英雄,在陪练啊。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同样设想,都是中国文学,这一篇那一篇,别人写的,还是雪眠写的,没有本质的区别。现在需要的是发掘雪眠。”
那一头叽叽呱呱的声音,还响了很长。柳元芷把话筒抓在手里,不听也不放下。
三
柳元芷在书桌旁干坐了两个上午,第三天上午,他走出门,一阵冷风吹来,光光的头皮一阵寒颤,才发觉没戴帽子,看衣帽架上没有,想起是前一天刘妈见帽子脏了,拿去刷洗了。他喊刘妈,刘妈走进,责怪自己,“真是老了,不中用了,白天晾出去,晚上忘了收回来。”刘妈上楼到晒台上去,好一会才下来,慌里慌张地说:“不好了,帽子不见了。”
“什么?”柳元芷吃一惊,急忙跟在刘妈身后上了晒台。晒台的一边靠着巷子,巷子里躺着一个衣裳架子,夹子上空空如也,据刘妈辨认,就是她晾帽子的夹子。无疑是风大,从晒台上吹落下来的。四邻去打听,有人说,“昨天傍晚看见一个背稍驼的农民工走过,停下来,好像捡了个黑乎乎的东西。”可是谁知道这个农民工是哪个工地的,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呢?
柳元芷如丧考妣一般,脸变了色,在屋里团团转。要问他日常生活用品中,哪一件最重要,首推这顶无檐软帽。这顶帽子是父亲留给他的,父亲一生用过无其数帽子,这是最后一顶,留给他时几乎是新的。柳元芷是到了年岁才用它,很快就体会到了它的好处,帽子的用料是英国的上等呢,坚实柔软,而且越戴越软,光脑袋塞在里面好像得了一个温馨熨帖的天然屏障,心也随之宁静。柳元芷用了许多年,只是帽沿有点破,让刘妈用金线滚了边。每年进秋,都会想起它。而现在已经是初冬了。
柳元芷说:“你怎么会这么大意?”
刘妈无言以对,满脸的羞愧、慌乱。
柳元芷开了园门,走出去,他步履蹒跚,又走得急急慌慌。初冬的太阳早已不旺,穿过云丝已经白惨惨的了。他问人,“见过一个驼背的人吗?”人们摇头,他从一个建筑工地走到另一个建筑工地。他头顶上的鸵鸟蛋发出灰色的光泽,清水鼻涕流了出来。当晚就感冒了。
舒阳来的时候,他还没有好透。舒阳问文章考虑得如何了。
他痛苦地说:“帽子不见了,头上少了保护,记忆也找不回来了。”
舒阳定定地看着他,脸上神情在变,像是新奇,又像是生气,轻轻吐出一句,“无稽之谈。”马上意识到,对柳元芷这样的人不宜讲这话。
柳元芷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不能自拔。这无檐软帽多好啊,寒冬时躲在里面。热烘烘的,软绵绵的,他闻到了父亲甚至祖父的气息,感觉到了家学的绵延。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他藏身在里边,听得见燕子啁啾,竹子拔节,看得见蜈蚣风筝上天,在空中振须舞爪。可是别人却无法影响他,进到他的世界里来干扰他,多么离奇、神往啊。他的文章只有在他独处的氛围里,才能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这个奥秘只有他知道。现在帽子丢了,窝不存在了,光脑袋随随便便露在外面,心就乱了。
县里的人又来了,档案馆和东江大学的人接踵而至。当他们得知因为丢了帽子而不能写文章,都觉得他矫情。有的还因之愤怒,幸而表现得都算含蓄。
柳元芷其实比他们还着急,他到衣帽店去了。拿了一顶戴头上,又硬又干,没有那种感觉,完全不是那回事。他换了一顶,再换一顶,仓惶逃走,害得柜台小姐朝他后脑勺瞪卫生球。骂这个老光头神经病。
舒阳已经在家中等着了,边上还坐着一个人,那人把柳元芷的头围量了又量,又看了头顶,和舒阳一起走了。
过了三天,两人又一起来,拿出顶帽子。舒阳说:“柳老,戴戴看吧,怎么样?上年纪的人受寒不得。”
柳元芷看,外表和丢的那顶挺像,也是无檐软帽,接过来戴,大小正好。
舒阳留意他的神色,说,“不错吧,这位是李师傅,是我们市里最好的做帽子师傅,给中央首长都专门做过。他按你说的样子,选了料,精心做了三天。”柳元芷听了,忙握他手表示感谢。
点灯了,柳元芷坐书桌前,头上戴了新帽子,暖和了不少,但感觉总有些两样,新的帽子还不熨帖,有些磨头皮、两鬓也有些不适,只能将就了。他想,总是要写,不能拂了舒阳的好意,人家精心特制了帽子啊。还有县里人,那么多的火腿、阿胶。还有档案馆、东江大学,不能叫他们太扫兴。
光晕出现了,白脸青年依稀地活起来了。柳元芷凝视着,心里喊,我就当你是雪眠了。没有办法,帽子丢了,心境都乱了。同时又对那个可能的汪闽颜或曹大洋表示深深的抱歉,我这个柳太守要乱点文坛谱了。他想,雪眠是个气性高而又孤僻的青年,那么,用独丘、瘦菊、子尚、昏鸦等笔名,就在情理之中。他把署这些笔名的小说又读一遍,归了类。心里说,要是损害了哪一个,请多多包涵。幸得大部分作者已经作古,即使活着,也到耄耋之年,哪里见得到他的文章?
四
辛苦了两个月,柳元芷终于写出了文章,先有一篇,再得一篇。各方争相来索取,大加称赞,说不愧是文章世家。蹊跷的是舒阳,唯独他没有出现,只派个小秘书来,把文章拷了去。柳元芷也不管他。又过了一个半月,就有印得漂亮的刊物送到他桌上,开卷赫然是他的文章。同期还有一篇报道,题目是《柳元芷扛鼎之力掘宝藏,桑雪眠熠熠才华重见天》。县里修志用上了。档案馆也备了资料。
柳元芷却不觉得高兴,好像刚刚还了别人的债。
那天,他出门散步,回来时从菜场过,买了几株青菜,却见菜场门口摆了个卖盐焗鸡的摊位,看上去鸡的皮色不差,就要半个。那提刀卖鸡的是个骨骼粗壮的中年人,他斜了半个身子,挥刀剁好,递一个盒子给柳元芷。
柳元芷回到家中吃,味道尚可,可觉得不对,仔细一想,不对,没有吃到鸡腿。就用筷子在剩下的中间翻,是呀,就是没有鸡腿。这怎么回事,一只鸡两条腿,他买半只,就得有一条鸡腿呀。难道剁的时候就手顺走了?怪不得那中年人要斜着身子挡他的视线啊。柳元芷越想越来气,倒不是一条鸡腿,现在的人怎么就这个道德水准?欺负我老头子?他写文章大功告成没有高兴,少了一条鸡腿,却真生气了。
他也不和刘妈说,出门了。没几步就到菜场口,盐焗鸡摊子前围了几个人,那骨骼粗壮的中年人一时秤鸡,一时挥刀,一时收钱,忙得不亦乐乎。他上前劈头就问:“我买半个鸡,怎么就少了我鸡腿?”
中年人也不看他,说,“鸡能不生腿?不生腿怎么走,你老头发昏了吧?”
柳元芷说:“不是鸡不生腿,是你没有给我鸡腿。”
“不给你鸡腿?我留着干什么,自己吃?我都吃腻了,还吃?”
柳元芷说:“我不管你留着干什么,你就是没给我鸡腿!”
中年人转过目光看他,“你这老头,今天是成心讹我?”
“我说的是实话,怎么是讹你?”
边上有人认识柳元芷的,插话说:“这是柳老,是我们市的大学者,是教授。”
中年人冷笑一声,说,“大学者就能赖鸡腿了?现在的教授都是‘叫兽’!”
柳元芷脸涨红了,“不许污蔑知识分子!”
中年人放下手中活,“你今天想干什么?我才开张三天,你是来踢我门牌!”说着抓起剁鸡刀,往砧板上一劈,那刀就直直地立起,咣咣抖动,发出一阵寒光。
柳元芷心里毛了,一边嘟哝,“你就是没有给我腿,”一边往后退,听那骨骼粗壮的中年人又说了句难听话,“还要讹我鸡腿,看我把他中间的老鸡腿剁下来!”周遭人笑了。
柳元芷又气又恼,只得逃开。回到家中他不说一句话,刘妈也不知为什么,不敢问。他早早上床睡了。第二天起来,似乎好些,但气还是不顺。
随便翻书,就到中午,忽然门外闹起来,他想问,却见两个青年人冲了进来,一个穿红衣,一个穿蓝衣,两个都是一脸怒火,好像是冲进来抓窃贼的。刘妈跟在身后,张着十根手指,像是抓不住了,也要做出个抓的样子。
柳元芷惊住了,半晌才说:“你们两位要干什么?”
那红衣的就说:“嘿,你干的好事!”穿蓝衣的不说话,却伸出一根指头,戳向柳元芷的鼻子。
他说:“你们两个,坐下说话。”
两个依然火气十足,但总算坐下来了。穿红衣的说:“那狗屁文章是你写的?”
柳元芷脑袋轰的一响,他的隐患就是这个,还果然是这!嘴里却在支吾,“是哪篇文章?”
“你知道,独丘、子尚是谁吗?是我们的祖父曹大洋的笔名,这是我们的先人写的小说,由上海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的领袖施教授作证,这容易吗?我们查了多少资料,费了多少心血!这已经是定论了,修进了我们曹家的家谱。你柳元芷算什么东西,胆敢冒名顶替我们先人的小说,毁坏我们家族的荣誉?”
柳元芷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他在乱点文坛谱的时候,就是心生惭愧,以为当年作家即使在世,也是耄耋之年,哪想到他们的孙子打上门来了!他一生没有做过这样的窝囊事,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
“你说!你为什么要抢夺我们先人的小说?”
“我,我是受人之托,想了解一个作家……”
“受人之托,就可以抢了吗?”
“我,我的帽子丢了……寒风吹得我头皮发麻……我心烦意乱……”柳元芷也不明白自己说了什么。
“呸!一派胡言。你必须登报声明,赔礼道歉。还要赔偿我们家族的精神损失费。”
柳元芷只得像鸡啄米一般点头。
蓝衣青年说了他进屋后的第一句话:“今天对你客气,要不,把你房子都掀翻!”
这一次柳元芷被吓得不轻,在床上躺了两天,才慢吞吞下地。出得门去,远远见了盐焗鸡摊子,不敢靠近,怕那孔武的中年汉子又劈利刀,绕了大圈子才走出来。徐徐走到城墙根,又见小桥流水。心思就有些活泛。忽然想,我骂这卖鸡的中年汉子,而我的所为和他又有何区别?他顺走鸡腿是作假,而我张冠李戴,夺人小说不也是作假?而且我是应市长之邀,才巧取豪夺,分明是讨好权贵,这作假的性质就比卖鸡的更恶劣了。
这么想过,柳元芷对卖鸡的不那么恨了,却对自己看轻了许多。沿着城墙、玉桥、湖边走过,柳元芷不由想了这个古城的历史,它在历史上因为贩盐而兴旺、繁华,又因反抗异族入侵而名垂青史。在这城市,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瑰丽的诗篇,嘴边不由滑过一首诗: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多美的意境,可是我柳元芷却做了什么,有辱斯文啊。
立春了,风中顿时少了寒意。偶见一排大鸟在浩杳高空中,振翎朝北飞去。柳元芷想,或许是勇敢的第一批。忽然听得楼梯上有刘妈的叫,分不清是惊喜还是慌乱,又听在哪里撞一下。柳元芷出屋看,刘妈从地下爬起,手举得高高的,手里抓的正是无檐软帽。
才找到了原委,那天刮风,帽子连着夹子没有刮到巷子里去,而是顺着西边的低屋棚滚落,恰好掉进两个屋檐中的夹缝里。而落到巷子里的夹子,是夹了旁的衣服。今冬雨雪少,帽子安安稳稳躲在那里,居然一点没损坏。
柳元芷哆哆索索接在手里,好像迎回一个以为死定了、却又重新归来的亲人。掸掉灰土,太阳里晒过,就能戴了。
这才是他的帽子,依旧是那么温馨松软,他的奇妙的独特的世界重现了,心也宁静下来。新帽子总是不好,虽然是特级师傅精心制成,但没有他的父亲、祖父的气息,而且感觉上不纯粹。只有戴上自己的无檐软帽,才会从心灵和肉体上都觉得和谐。
他想,原本完全可以不叫人特制的,只要朝西多走五步,搬一张椅子,踩在上面(刘妈正是偶然登上椅子发现的),那么帽子就不会无缘无故在缝隙里躲三个月。这样的话,他很可能就不会在文坛制造冤假错案,也不会让人打上门来。啊啊,他扼腕叹息。但是又想,恐怕不完全因为无檐软帽。
吉普车又来了,柳元芷没有给他们好脸色。可是,来人似乎并没有发觉,却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很好,水平很高,作品都提到了,分析得也透彻,但好像还缺了一点。缺什么呢,缺一个高屋建瓴式的评价,招商引资就说不响亮。望柳老再加一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比方说,伟大的作家,如果够不上,那就提,杰出的作家。”
柳元芷冷笑一声,只是摇头。来人就疑惑了,手一挥,车上就有人下来,又往屋里搬火腿、阿胶,搬松花蛋、感鱼。柳元芷伸了两手拦,叫上刘妈,还是不行。搬东西都是年轻人,他们老胳膊老腿哪里拦得住。
柳元芷急中生智,大喊:“我全部推翻了!我后悔了!”
这下有效果了,来人叫停下,问,“你怎么后悔了?你要把文章推翻?”
他肯定地点头,说,“我昧了良心,这些小说不是雪眠写的,是别人写的。这文章站不住脚,我是替他人做了贼。”
来人再问,“真要反悔?”
柳元芷说:“此刻不纠错,将来还带进棺材里去?”
县里人不再往屋里搬了,搬进去的还往外搬,装上车。吉普车开动前,一个人说,“以前两次白送了,喂老狗了。”
柳元芷听见了,大声叫:“告诉我,一共多少钱?你等着,我拿给你!”
车子开走了,没人睬他。剩下他还在叫。
五
舒阳登门是在一个星期之后,他进了书房,也不坐下,敞开了领子,颈子灵活地转一个圈,他说:“柳老,你怎么弄的,那两个愤青上市里来闹了,说政府支持你弄虚作假。你怎么能把他们祖父写的小说算成雪眠写的呢?”
柳元芷口吃了,“不是你让我写的?不是你说的,中国乒乓球队多少幕后英雄?”
舒阳说:“不错,是我说的。可是,我叫你把别人写的小说,说成是雪眠写的吗?我说了吗?”
柳元芷傻眼了,当时他一再搭桥,推波助澜,还叫人来定制帽子,怎么说变脸就变脸?他说:“当时不是你来动员我写的?你还说,必要的话,要建纪念馆……”
“一点不错,是我请你写的,但是,这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实事求是才对。我们不能伪造历史,投当官的所好。”舒阳撇起嘴角,“请你写,也是考考你的品行,没想到也是这么龌龊。”
柳元芷气昏了。舒阳什么时候走的,他都不知道。
柳元芷始终不明白,舒阳为什么像猫一样变脸。后来,市府有个高人点拨了他。舒阳早知道桑雨眠市长对他有看法,恰好桑雨眠提起哥哥雪眠,舒阳就从中搭桥,想借此事讨好桑雨眠,没料到桑雨眠并不领情,还来过问他一些违纪的事。刚好这里出了纰漏,碰上作家后代来闹,舒阳干脆翻脸,一起往柳元芷和桑雨眠身上栽赃。
柳元芷这才明白,冷笑一声,也不往心里去,第二天就忘干净了,倒是对那顶无檐软帽,多了一份感情。一直戴到戴不住了,才舍得从头上摘下来,又对刘妈反复关照,千万不能再丢失。
五月的一天,有人按门铃,柳元芷想起刘妈上街了,自己来开。他愣住了,来的是桑雨眠,单身一人,没有随从,也没有汽车。
“柳老,多日不见,身体好啊。”桑雨眠的长眉毛抖得很欢。
柳元芷说:“好,好,快请里面坐。”
桑雨眠喝了茶,两手放在膝上,说,“为我上次一句话,惊扰了柳老,抱歉。”柳元芷忙说谈不上。
桑雨眠的眼里露出潮湿的温情说:“其实我们大家庭中,我最爱的是我大哥。那次他回家,引我到后花园去,拿木桶浮在水上,人蹲在里边。一次桶翻了,我差点淹死。”柳元芷嗯嗯着。
桑雨眠又说:“我很想知道,我大哥的创作实绩究竟如何?”柳元芷就对他说实话,“雪眠只当过两年文学青年,参加了一些集会,写过两篇不出名的散文,后来不写了,去当小学老师,没几年就病死了。”
哦,桑雨眠眼里露出些失望,又露出些坦然,说,“这样好,我心里就有数了。”
两人移步到园子里,这是一个四方的小天地,两边墙上爬了青藤,开出粉色的喇叭花。另一边有个下挖的小池子,池里的假山玲珑剔透,一群金鱼在优雅地游动。
他说:“这个地方好。”他退下来了,有时间了。柳元芷说,“有时间好,常来坐坐。”
那天桑雨眠坐了一个多小时。两人分手时似乎很留恋,一再握手。桑雨眠走出一段路了,回头见柳元芷还站在门口,他又扬起手。柳元芷也扬手。
写于2016年8月24日南京老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