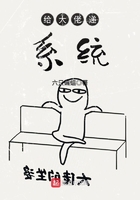乐越来的时候,病房里并不见钟吟的人影。她将两本《伦敦客》放到床铺上,在靠门的月白色的布沙发上落座,一壁揩着汗,一壁望着门外。今儿外头气温热,她又好巧不巧穿了件羊毛衬衫,虽说是乘家里汽车来的,可不拂躁意,总是发汗。
钟吟从门进来,见着乐越这副形状,问道:“我当你是跑着来的呢,怎么这样热?”
“我要是跑着来,兴许现在业已被送进急救室了。你是不出门,不晓得外头有多热,一个好生生的人,动也不动,端正立在日头下,可要不了半刻钟,保准是汗涔涔的了。”
钟吟捱着床沿坐下,拿起那本杂志翻看。乐越一贯知道她的喜好,每期的《伦敦客》她都会订阅,只是如今住在医院里,报差只会按着约定送去公馆,她还以为要等到出院以后才能读上了。
乐越汗落得差不离了,便伸手拉开了皮包的拉链,露出里面的宝蓝缎子,她又将手伸进去一些,一把捞出所有的衣裳,只见下面还有湖绿色的衬衫、藕灰的夹袍、淡粉红薄呢的旗袍云云不一而足,统共有那么五六件,俱是摺叠齐整了的。
“这是我今儿上你家里取来的,要不是你那个女佣给我拨电话,我也忘了你还需要几套换洗的衣裳呢。走的时候,她还特地把这两本杂志给我了,托我一并带来给你。不得不说,你这个女佣实在是周全妥帖的很,只是名字我没记住,依稀是叫紫什么还是红什么的。。”
“紫荆。”钟吟道:“她确实是个仔细稳妥的人,大约是因着打小没亲人的缘故吧,什么事都是自己操持,故而懂得多。”
乐越点头应了声,又道:“嗐,我也不同你多言语了,司机还在楼下等着我,这就得下去。”
钟吟蹙眉问道:“你还有要紧事么?”
“下个月就要开学,今儿约了同学一道儿温书,你知道开学即要测验了,我这两个月连书都没翻呢。我现在预备回去洗澡换身衣服。”
钟吟眉头一舒,旋即笑道:“你们英文书院,向来规矩颇多,总是要顾着书本,还要顾着实践,我看你实践倒是丰富得很,只是苦了你还要念书背英文。”
“谁说不是呢?”乐越说完便作辞了,离开时还顺手带了只橘子走。
中饭前医生来作了例行检查,同昨天一样,喜笑颜开地恭喜她恢复得不错,但只是还需要留院观察一阵儿,以防万一。钟吟也微笑着道谢,除此之外,也并不觉得有甚么可喜之处。
医生前脚刚走,只见门口走过三五一行人,除了为首的以外,后面跟着的人俱是穿著军服,看样子,是朝着冼斯年病房去的。
昨天冼玉律说的那番话又重新响在耳边了,甚至一个字都没差错,一遍又一遍地,仿佛是谁不仔细,无意拨开了留声机的锁搭似的,于是声音便四散到这间房子的每个角落,搅得她脑仁有些痛。过了片刻,她起身下床去,预备到外面去走一走。却不晓得为何,竟无意识地走到冼斯年的病房前,当她反应过来时,人正站在门口,定定地瞧着里头的情形。
冼斯年正立在窗前,照旧是那套蓝白条的病服,许是裤子稍短,细长的脚踝便裸露在空气中,双手背在身后,右手食指轻轻地敲着另一只手的腕骨——他想事情的时候,手指总是习惯有节奏地敲点什么。
他身后的书桌前立了个男人,正是方才那行人中为首的那个。那人从背影瞧,个子不高,将头发剃得寸短,一件齐膝盖的深蓝布衫,下头露出半截细口的黑袴管——俨然是逊清的装束。
其实这样扮相的人寻常也不少见,下关的鞋帽庄里的伙计多是这样的,只是钟吟鲜少去光顾,镇日里所见的人俱是西装革履的绅士打扮,况且冼斯年身边又常见军装,故而甫一见此人,便觉得有些惊奇。
她心觉门前太过显眼,便挪到一旁的窗户前了,隔着窗又立了一阵儿,见内里冼斯年坐回桌前,面沉如水,手叩在桌案上,半晌一句话未发,而穿长衫的那人,倒也没再开腔了,两人一时有些沉寂。
她转身本想就此离了,未料迎面撞见项勣,见他左手揢了三盒三炮台,便问道:“烟瘾犯了?”
项勣笑了一下,道:“标下不吸烟,是傅先生方才说嘴里想叼点东西,这才跑了趟烟铺。”
钟吟才发现项勣露齿笑的时候,会露出右侧的一颗虎牙,尖尖小小的,倒可爱的很,于是她也笑了,道:“医院楼下开烟铺,掌柜惯会做生意。”
项勣道:“哪能呢,标下是驱车到东江饭店那边去买的,楼下可没有这样的生意。”
“我不耽误你们忙正事,这就走了。”
钟吟回到自己的病房,揿铃请护士将餐饭送来。照例是清淡的菜品,一例米粥,两碟素菜,一盅花胶鸡脚汤,另外还配有一小碟冷盘,大约是天热的缘故,热菜她都很少下筷,然而点心却很合她胃口,今儿的是藤萝花饼和乳茶。她正餐没吃几口便撩了筷子,转而拿起调羹,细细地品着那盏乳茶。门口骤然响起两下敲门声,她抬头看去,原是那天的小警卫,不过今次他的神情倒从容了许多,虽不至于平和带笑,但总归是不紧张了。
“有事?”
小警卫敬了个礼,道:“少将军请您过去一趟。”
钟吟也没作多想,放下手里的碗匙,用薄巾揩了揩嘴角,便随他去了隔壁。一进门,见冼斯年坐在茶几前也正吃着饭,另一边的沙发上坐着那个穿长衫的男人,这下钟吟才见着他的正脸。长方脸型,由于头发很短的缘故,便露出了很高的额头,眼睛虽不大,但却很亮,此刻正盯着钟吟瞧。
冼斯年招呼她,道:“过来。”钟吟过去跟他并肩坐在一条沙发上,又听他道:“这是傅先生,叫人。”
钟吟颇乖顺地一颔首,道:“傅先生好。”
傅茗的目光在两人身上扫了一圈,在刚刚听到冼斯年的话时,眼中似乎闪过一丝讶异。
“吟小姐好,久闻大名,今次终于有幸一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