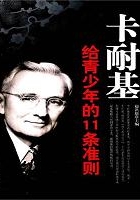外面有陈庆将军做主力,钟离越带着一批大军冲进王城,下面的士兵仍在奋力厮杀,他一个人手持长剑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城墙上走去。
钟离宥看着下面那些黑甲士兵,他们死后不会留一滴血,直接化为灰烬。他想起方才钟离越说是向阑国国主借的兵,是因为阿粟才借到兵的。这才明白为什么阿粟自那次出宫回来后容颜瞬间苍老,原来是为了帮助钟离越,为了钟离越她竟可以什么都不顾,这才知道原来自己一直都是个傻子被他们耍的团团转。
钟离宥站在城墙上,双手撑着城墙,闭着眼,再睁开时便看到那身处刀光剑影中的一抹绿,心不由自主地提到了嗓子眼。
“阿粟姑娘。”青衫伸手挡下了要刺向她的剑,一把将阿粟拉了起来。阿粟慌乱的看着四周寻找钟离越,抬头却见他已经站在城墙上,慢慢走近钟离宥。
钟离宥缓缓松了口气,忽然听到有脚步声,缓缓转过身。
来人正是钟离越,他拿起手中的剑指着钟离宥道:“你败局已定,这王位本就是我的,今日我便要你为我母妃偿命。”
钟离宥视眼前的剑为无物,冷冷的目光看着钟离越,道:“你根本就不配做清川的王。”
钟离越十分看不惯钟离宥这么高傲的样子,一剑刺了过去。钟离宥旋身躲过,一下子也拔出了剑。钟离越的剑术自小就比不上钟离宥,可如今钟离宥身中剧毒,这一运功又加快了血液的流通,也加快了体内之毒蔓延。
钟离宥刚举起剑便觉胸中一抽痛,他撑着剑呕出一口乌黑的血。钟离越一脚踢在钟离宥的胸口上,钟离宥一个不稳手中的剑脱落,重摔在地。
钟离越提着剑走过去蹲下身,狠狠道:“大哥这江山还是交给我来守护吧。”
钟离越站起来以一个成功者的身姿俯视钟离宥,缓缓举起了剑,钟离宥起不了身眉头拧作一团。最后一瞬钟离越闭着眼睛猛地刺下去,钟离宥缓缓闭上双眼,眼角有清泪流下。
正当那剑尖与钟离宥只有毫厘之差时,只听“铛”的一声,一颗碎石将钟离越手中的剑打落。
阿粟飞身而下挡在了钟离宥身前,看着钟离越质问道:“你不是答应过我会饶他一命的吗?”
钟离越愤怒的青筋暴起,道:“是他冥顽不灵,我留他不得。”
钟离宥捂着胸口吃力的站起来,冷静道:“九弟我一直没告诉你,其实父王的遗诏写的是将王位传给我,是贵妃得知此事谋杀了重病的父王私改遗诏,怕我得知此事,便给我下毒,是她逼我反,我只能反给她看。”
钟离越亲耳听到从他口中说出的这一番话,一时像被什么震住了。连连摇头,不敢相信挥动着手中的剑,道:“你胡说什么,父王明明那样宠爱母妃,母妃怎会下此毒手?你就是想来个死无对证,我才不信你的鬼话。”
阿粟看着钟离宥回过身,突然明白了什么,钟离宥才是真正的清川之王,那颗帝星也是钟离宥,原来自己一直都弄错了,钟离宥才是真正的慕子阡。阿粟才知原来这一切不过是老天是和她开的一个玩笑,她本想来救的人,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她伤透了心。不知道,现在想弥补还来得及吗。
钟离宥叹道:“在这宫里哪有什么真心,只不过是为了自己。”
先王因为钟离越母妃的原因对钟离越十分疼爱,反而对钟离宥十分严厉。后来父王老了,陪在他身边的人却一直都是钟离宥,哪怕病了也要检查他的功课,看他练剑。钟离越依旧是他十分疼爱的孩子,随着钟离越的长大他也看出来,父王真正欣赏的人是钟离宥。
为此钟离越还特意问过母妃,说父王是不是不喜欢他,是不是他不够优秀,怎么什么事都比不过大哥,每当这时贵妃都会十分肯定的回答,父王最疼的人是他,所以最后知道父王将王位传给他时他虽然吃惊,却也没有起疑心。
直到宫里谣言四起,他还是对母妃深信不疑,他是父王最疼爱的儿子,这王位也应该是他的。当看到钟离宥亲手杀了他母妃时,便对钟离宥恨之入骨。
钟离越根本就不想知道钟离宥说的话是真是假,他只想为母妃报仇。钟离越再次握紧了手中的剑,冲向钟离宥。阿粟再也不能坐视不管,开始使用灵力,最终将她开始一力保护的人,置于剑下。
钟离越道:“你说过我是你的恩人,你怎能忘恩负义?”
“我从来都不欠你什么。”阿粟心中懊悔,可如今一切的已无法挽回,她淡淡道,“若你退兵,我定会饶你一命。”
“呵呵。”钟离越冷笑两声,吹了一下口哨只见一大批黑甲士兵奔了上来,“要我认输,除非我死。”
阿粟收回了剑,顾着对付走上来的这些黑甲士兵。她脖子上戴着的绿石链沾了她的血,一直在发光。阿粟这才想起这石链是师父给她的一定有特殊意义,阿粟握着那颗绿石一下子将它从脖子上扯下来紧握手中,她的手被那颗绿石扎出了血,那绿石的光芒散发的越来越强,阿粟已经感觉到它强大的仙力。
阑国国主正摆弄着棋子,突然他的手像是被定格住了在棋局上无法动弹,棋局中的棋子一下子全都悬浮起来,而这边那些黑甲士兵也被定格住了,动作万千不一。
阿粟将绿石链抛向空中,那绿石链光芒四射。阑国国主面前的棋子一下子碎成飞灰,这里的黑甲士兵发出一阵阵的惨叫声,顿时身体粉碎如尘埃坠地。
阑国国主元气大伤,一口鲜血喷在棋局上,微皱了一下眉头,这是他第一次有表情。
所有人抬头看着这令人震惊的一幕,熠城中的人瞬间减少了一半,如今黑甲士兵全被消灭,钟离越就只剩下几个誓死相随的人和陈将军的两千士兵,败局已定他们却还在负隅顽抗。
钟离越看着这一幕,已经知道复位无望,瘫软着身子靠着城墙坐下,缓缓拿起掉在地上的剑,架在脖子上,闭上双眼落下一滴悔泪,自刎于这城墙之上。
尚有余温的鲜血溅在钟离宥身上,钟离宥看着自己的衣衫,惊得回过身只见钟离越脖子鲜血如注,握着剑的手也缓缓垂下。
钟离宥先是一惊缓缓走过去,陪着钟离越与他一同依靠在城墙上,道:“我知道贵妃做的事与你无关,我不想杀你,但也知道你早已容不下我,九弟我本来是要打算……”钟离宥看着坐在他旁边再也不说话的钟离越心中直发酸,想说什么却也说不出了。
尘埃落地绿石链的光芒越来越弱慢慢隐退下去,飞了回来。阿粟的灵力太弱,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强大的仙力,她强行使用绿石链也被仙力所伤,还未将绿石链收回便口含鲜血,晕倒在地。
陈庆的两千士兵,也知大势已去,有的士兵已经放下武器投降了,其他本就不想与自己人交战的也都纷纷放下武器。陈庆见状愤怒不已,杀了几个投降的人,可越是这样便越没有人信服。越来越多的人放下武器跪下投降,慢慢的到处都是跪着的士兵,陈庆拿着刀一个人站在他们中间,显得格外突兀。
一位与陈庆并肩作战多年的老将拉开了弓,在陈庆没有注意的时候,一箭射去陈庆一个踉跄,随后从身后赶来的士兵将他拿下了。
转瞬之间这繁华的熠城被浓浓的血腥味包围,白色石板上血迹斑斑,到处都是尸体和鲜血,那些羽箭无情的插在土地上插在血肉上,笼罩在每个人周围的都是肃杀之气。
事过几天王宫内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陈庆被逼交出了解药,钟离宥体内的毒也解了,醒来时又听到一个噩耗丞相死了,是被陈庆杀死的,那日陈殷死在牢狱中,丞相前去找陈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还听说阿粟还在白莲宫昏迷不醒,钟离宥还是命人将解药也给了她一份。
这几日上朝天师和许多武将都纷纷提议说阿粟这个奸细留不得,应该处以极刑。钟离宥虽然对阿粟已失望至极可说起要杀她仍狠不下心来,所以对于此事他一直没有回应。
白莲宫如今的气氛与往日大不一样了,院中好多枯叶都没有人打扫,风吹着落叶唰唰而下格外萧瑟,一眼看去竟是半个人影都没有。
“姑娘你醒了?”一直伺候阿粟的贝罗道。
阿粟扶额坐直了身子道:“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钟离宥呢?他体内的毒可有找到解药?”
贝罗道:“姑娘你已经睡了五天了,那天血战中九殿下自刎,九殿下虽然有错。但王上还是将他安葬在了王陵,陈将军被押进了天牢,王上的毒也已经解了。”
阿粟看着外面随风而落的树叶,喃喃道:“他死了。”
其实他有什么错呢?是自己允诺他,要帮他复位的,可最后也是自己将他的希望覆灭。阿粟现在才知道自己真的错了,不该执意窥探天机,造成了这一切一切的误会,如果她没有下山钟离宥还是清川的王,大家都还好好的。
丞相死了,最近又发生了此等大事,就再没有人提立后的事。不过发生了这件事后,大家都知道钟离宥对那只猫妖已经没有任何情意了。
书房内钟离宥正在批阅奏折,楚遥雪在一旁低头磨墨,这几日陪在钟离宥身边的一直都是楚遥雪。
钟离宥拿着那个奏折好久都没有换过,像是在思考什么,随后突然道:“听说十月二十三是个好日子。”
楚遥雪不知钟离宥何意,便也没答话。钟离宥也没有多说什么,将那个折子放下了,继续看下一本,每当看了一阵子他都会下意识看楚遥雪,以为楚遥雪也会靠在自己的肩上睡着,可每当看楚遥雪时楚遥雪都会面带微笑回看钟离宥一眼,随后有些脸红的低下头,钟离宥都有些犯困了,楚遥雪看着还是十分精神。
“你们听说了没王上要与进宫不久的秀女楚遥雪成婚了,我今日还看到锦衣局的人在制凤冠霞帔。”
“真的吗?王上不是一直喜欢那叫阿粟的姑娘吗?”
“都在制凤冠霞帔了,还有假。”
“你们还不知道吧,那阿粟其实是只妖怪。”
“什么,妖怪?”
“真的假的。”
“怪不得把王上迷的神魂颠倒的,原来是个妖怪。”
“……”
后花园中修剪枯枝败叶的宫女私下里议论着。
阿粟又在补落下好久的针线活儿,那兰花真的是越绣越不像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么忙,她要么在院中种种花草,要么就看看小说。总之就没有闲着,她不敢闲下来,因为一闲下来,她的脑海中就会闪现出钟离宥的样子,她被禁足了,现在在白莲宫不能出去。明明两个人同在一个地方却连一面也见不着,阿粟真的很想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阿粟坚持将兰花绣完,突然听到外面有抽噎声,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这宫里根本没有其他人,贝罗也已经去端点心了,可她停下手中的针线活儿还是听到了。
阿粟将锦囊放到一边走出屋去,才见躲在墙角偷偷哭泣的人是贝罗,阿粟走过去蹲下身问:“贝罗,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贝罗连忙擦去脸上的泪,摇了摇头。
“那你怎么难过成这样?”阿粟将她扶起来给她擦泪,抱了抱,安慰道:“好了好了,别哭了。脸哭花了就不好看了。”
阿粟不太会安慰人,不知道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贝罗哭的更厉害了,她边哭边道:“姑娘,王上要立楚遥雪为王后了。”
阿粟拍着她背的手瞬间停了下来,脸上一下子布满灰色,贝罗的哭声她都感觉听不到了。贝罗也感觉到阿粟有些不对劲,轻轻推开了她。阿粟吸了一口凉气,红着眼眶笑道:“傻丫头,王上成婚是好事,你怎么哭了?”
贝罗看着阿粟,还在抽噎道:“姑娘,你不难过吗?”
阿粟勉强挤出一个笑脸,道:“都说了这是好事,你不是去拿点心了吗?我都饿了。”
贝罗抹去泪水道:“那好,我这就去给姑娘取。”
这贝罗真是小姑娘心性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了。阿粟转过身连背影都显得凄凉,扶着门走进了屋中。
“你想一辈子不嫁,那我就一辈子不娶,我们俩就这样打一辈子光棍吧!”
阿粟想起钟离宥说的这句孩子气的话,不知不觉就笑了,笑着笑着便两眼含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