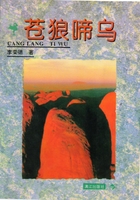创作小说十篇
一
尚可在安的追怀仪式上认识了宁,这表明他是安的朋友,宁也是。当时他们说不上一见钟情,只是点头致意,相视一笑——在那种肃穆的场合,所有的情感都被裹上了黑色,相视一笑已经很不容易了,表明两人的心灵已经很默契,要知道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后来便有了这趟结婚旅行,当然这是很后来的事了,其中还发生了很多别的故事。
不过他俩结婚后,只有一次提到过安,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这又说明无论是他,还是宁,都并不过于看重那位年轻美丽的死者,当然也有可能恰恰相反,因为过于看重而有意回避提到她。
回想起来安的追怀仪式是很特别的,据说很合乎她生前的品味。仪式在她常去的一间咖啡屋里举行,播放的是《安魂曲》,摆放的是鸢尾花,花束旁边搁着她的照片。这一切都是她的朋友们为她精心安排的,显得那么周全细致,好像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照片上的安很沉静,也很陌生,至少他觉得是这样,好在脸上还有那丝讥讽的微笑,这一点是他熟悉的——他正是透过那种讥讽,感觉到了她那无法安顿的灵魂。
他认识安时,她已经不是处女了。
——早就不是了。她笑着说。
他是临近中午醒来时,听见她这样说的。
——介意吗?她又问。
他说他不介意,只是好奇罢了。
——我知道男人都是有些介意的,虽然嘴上不说。
他说他真的不介意,只是好奇,如果她真是一位混沌无知的小姑娘,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你也没有资格介意。你什么时候失贞的呢?可能十八岁吧。
他说哪能啊,哪能这么早。
——可是你无法证明,对吧?一定是个老练的女人夺走了你的贞操。她说。
他笑了,用笑表示认可。
后来她进洗手间漱口去了,他们没再往下探讨这个话题。幸好没再往下探讨,否则还真得逼他去回想一些泛黄的往事,他望着墙上的那幅油画想。画上的花瓶里插着一束玫瑰,撒落的花瓣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殷红。
当然这世上无论是喜欢安的人,还是安喜欢的人,都不止他一个。
他们为她送上鸢尾花和《安魂曲》,说她如何如何喜欢凡·高和舒伯特,还夸赞她多么多么有气质,多么多么高雅等等。可是他并不记得她提起过凡·高或舒伯特。他只记得她喜欢肯德基,每次都会把鸡翅啃得精光。他想或许她跟他们在一起时,是喜欢舒伯特或者装作喜欢舒伯特的,而跟他在一起,她就喜欢睡懒觉,啃鸡翅,把那个不幸早夭的奥地利作曲家给忘了。
他并不知道她有那么多朋友,要不是她死了,也见不着他们。她曾经不时提到过这个那个,可是口气很淡然,跟提到哪位时常在报上露面的政府官员也差不多,要是他们当中谁死了,她是不会去送花圈的。可是他们都来送她,而且神色都很肃穆,围坐在几只烛光闪烁的桌子前低声说话。只有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站在一旁,看看他们,也看看安。
他站在一旁,是因为他到得最晚,里面光线黯淡,又不见熟人,只好站着。那个女人好像一直守在门边,守了一会儿,就走过来说:
——是尚可吧?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我们通过电话。我知道在这些人中,安最……看重你。
这个女人就是宁。
他听得出来,宁原先想说安最喜欢他,可犹豫了一下,把喜欢说成了看重。看重就看重吧,能被人看重也不容易呀,况且还是被安看重呢。
他点点头,问她叫什么。她说出了她的名字。
尚可和宁站在酒店十四层的一座阳台上,两人都没有说话,望着一阵一阵飘落的夏雨。他们终于没能避开安。安像一根引信,一根长长的引信,懒懒地逶迤在他们身后,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她都尾随着,看上去好像只是一根细细的绳索,可是一旦被点着,就会迸射出惊人的火花。
站在这么高的地方,好像位置很好,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四处都是同样高耸的大楼,在青灰的天色映照下,深色的窗玻璃全都泛着阴沉的光。不过要是你往下瞅,还是可以看见一些东西的。
下面有一条横街,两侧是典型的南方骑楼,在其中一座骑楼凸出的平台上,放着一盆红玫瑰。
那些个头瘦小肤色黧黑的南方人,正疾速穿行于墙面斑驳的骑楼下,如同蝼蚁一般匆忙。穿行于骑楼下,既可以避雨,又可以躲避阳光,还可以躲避目光,最适合于从事秘密活动了,怪不得当年革命总是首先在南方爆发。在这座城市你见不到伞花,一朵也见不到。那种色彩斑斓的伞花只存在于梦中。
他们站在阳台上,望着无伞的雨天,各想各的心事。那些雨滴随风飘落,黏附在阳台前的法式栏杆上,慢慢结成水珠向下滑动,滴落,晶莹的圆形渐渐被拉长,拉成椭圆,随后呈心形继续往下坠落,落向那条横街,落向那盆红玫瑰。
水珠每次被拉长时,后面的世界也跟着变形,变出的形状非常奇特,因为那是平日见不到的世界,难怪安有一次说过,雨天的世界更真实。他正在回味安很久以前说过的那句话,忽然就听见宁说:
——安很聪明,制造了一个幻觉,留给我,自己却走了。
说完她转身走进屋内,撇下他一个人,跟风在一起。他斜睨翻飞的雨珠,又想起了安的另一句话:我更愿意听风的声音。那是有一次他和安吵架后,安的一句自语,那句话的前半句是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听见宁提到安,他有些惊讶。虽说两人各想各的心事,但毕竟相处了半年,有时也会想到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她提到安时,他恰好也想到了那个年轻女人。当然他经常想到她,暗暗想,只是嘴上从来不说,此时他想到她,完全是因为看见了骑楼平台上的那盆红玫瑰。
这座亚热带城市的居民,家家都喜欢养花,可是家家又都装了铁栏杆,所有的花草看上去都跟被囚的鸟儿一般寂寞。那盆红玫瑰是个例外。它被随意搁在凸出的平台上,似乎无人料理,却开得分外灿烂。
——你信吗,昨晚一片花瓣掉在我的脸上?真的,我的脸都感觉到了,凉凉的。我知道你不信,所以没说。
那天早晨安先起来,洗漱完毕后这样对他说。她的内心与她的名字恰恰相反,总是很不安分,总是会冒出一些奇怪的念头。
卧室墙上有一幅油画,色彩很鲜艳,远端是阳光下的几栋木楼和一架风车,近处就是一束殷红的玫瑰。他醒来时发现她在洗漱,就支着脑袋观察那幅画。那是他第一次认真观察那些粉色的花瓣,发现它们非常性感,并非只有粉色一种颜色,除了粉色,还有浅红和深红,错落有致地组合在一起,宛如女性的性器官,显得神秘而娇美。他甚至还感觉到了花瓣上的露珠。
他把这个发现告诉安。她见他注意那幅画,就说出了前面那句话。
——不是花瓣,是泪水。他说。
她坐在梳妆台前描眼眉,听见他这样说,手停了下来。
——跟我在一起,你不快乐,是吗?他又说。
——不是。不完全……是这样。有的东西与你是……没有关系的。她说。
——与谁有关系?
——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敏感?可能吧……有人就这样说过我,还说敏感的女人只适合于做情人。
听见宁提到安,他说:
——其实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只是不想说罢了。她确实很聪明,所以从来不结婚。
这是他们婚后头一次提到安,也就是这句话,点燃了长长的引信。
二
得知安的死讯时,他也是在广州。
他并不喜欢那座城市,可是因为干的是首饰推销,或者又叫假首饰推销,不得不每隔十天半月就往那边跑上一趟,像甲虫一样在那些阴暗的骑楼间穿行,谁叫那边的胖妇人都喜欢戴戒指呢。
不过自从安离开后,他也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
他终于明白,其实活着就是适应,忍受就是成熟。每次坐在飞越两地的航班上,他眼中是云,心中也是云,宛如生活在幻觉中。他知道自己依旧怀念安,很痛恨自己的依恋心理,可是内心的另一个声音又会说:人不能毫无依恋呀,若是那样岂不成了薄情寡义?
他常常独自在广州的小巷里四处游走。虽然他去过广州无数次,可是他也知道,在那座陌生的城市里,他只是一个异乡的假货推销员,一个失恋的假货推销员,永远也不会有本地人的优越感。若是走进哪条死巷,随便哪位胖妇人都可以操着硬朗的粤语把他骂出来。可是他依然愿意游走于那些幽暗的小巷中,在一盏盏昏黄的路灯下彻夜彷徨,想想昨天,想想前天,想想安。
得知安死讯那天晚上,他就这样走了一夜。
他不停地走呀,走呀,穿过一条条幽深的巷子,又穿过一座座阴暗的骑楼,从红花岗走到黄花岗,从越秀山走到海珠桥。这个世界本来就很陌生,安死后就更陌生了,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只有走动才有安全感。
他一直走到星辰退隐,曙色熹微,才筋疲力尽搭上头班航班,想赶回去见安最后一面,哪怕见到的是一张死去的脸。
安有一次问他:
——你在想什么?我每天睡觉前,都会想起下午两点左右见到的人。
——要是你见到的是猪呢?他说。
——也会想起来。我觉得下午两点是我一天中的生命高峰,过了那时段,剩下的时间只能算苟活罢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问:
——你喜欢吃饭吗?
见他不回答,她就说:
——饭是一种慢性毒药,吃了以后会慢慢死去,抵抗力好的能拖上七八十年,要是差一些,三十年就会见效。
他笑笑。每当听见这类怪论,他都会笑笑,用笑表示对她的欣赏。
——这种毒药最适合于我这种人了,不想活,又害怕死,只好拖着。她接着说。
他说他不这样想,能活着毕竟还是很美好的,可以看见很多事情,看见树发芽,看见月全食,还可以看见贪官被判刑,恶人被枪毙。要是他以后有钱,还可以陪她去旅行,去意大利划船,去奥地利爬山。
——然后呢?她问。
他说一生能这样过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就继续吃饭,或者吃慢性毒药,对吧?我们还是先别去想什么意大利,去西山公园看看花吧,凭本市身份证,一个人只要一块钱门票。
那时已经是四月下旬,下着淅沥的雨。
——只怕樱花都谢了。他说。
——那也没什么,樱花谢了,就看别的花呗。
樱花果然谢了,在雨中一瓣瓣凋落,把地上的水都染红了。
他们走在雨中,看了桃花,李花和杏花,走到一棵杏花树下时,她看看左右无人,就踮脚吻了他一下。
他问为什么。
——不为什么,就为高兴。好久没这么高兴了。她说。
他住在城市的另一端,一个月只见她一两次,并不知道在其余的日子里,她过着怎样的生活。虽然她偶然也会说起,这家酒吧如何,那间舞厅如何,这个王八蛋怎样,那个老混蛋又怎样,但在他听来,那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他不知道她平日过得怎样,只知道跟他在一起,她是快乐的,至少有一点点快乐吧。
他想吻她,但她避开了,顺手摘了一片树叶。
——在一个百分之九十的贪官污吏都逍遥法外的时代,我一个平头百姓,摘了公园里的一片树叶,算得上犯罪吗?她忽然问。
他说当然算不上。
——可是那块木牌上说摘一片树叶,罚款十元,好笑吧。她说。
他说管他呢,要是哪天坦克再进城,他不会觉得奇怪。
——还是古时候好,关山万重,家书万金,一重山抵一两金,现在什么思念也没有了,一个电话过去,什么都抵销了。她的眼神有些黯然。
他一直不明白她说的那个电话,是想打给谁的。
他当时并没有去想,告诉他安死讯的那个女人是谁。听到安的死讯后,他的脑袋一阵空白,只把传送死讯的声音当作命运的声音。
宁过后说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安经常跟我提起你。
他问安为什么从来也没有跟他提起过她呢?
——她害怕我夺走你。宁闪烁着目光说。
见他没有反应,她又说:
——我们当然是朋友,可是女人的友情一旦跟男人有关,也就跟嫉妒有关。她经常跟我提起你,可是她并不知道,我嫉妒一个男人那么爱她,一直都暗暗嫉妒。
她捋了一下头发,又说:
——我还鼓动她跟你闹别扭。
他说安从来没有提到过她,也没有跟他闹过别扭。安跟他分手,是出于别的原因。
后来他们就离开了《安魂曲》和鸢尾花,走上了灯光闪烁的杉湖北路。
——知道她是为谁死的吗?宁问。
——当然不会是为我。他说。
——当然不是。她说。
——为谁?
——一个男人。
——谁?
她不说。
安提到过的男人在他脑海里迅速闪过,星星剧院的瘦高个、红会医院的吴大夫,还有小聂和小郭,好像都不太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安从未提起过的人,她要是心里有谁,自然不会轻易提起。于是他想到了她在杏花树下提到的那个电话。无论是谁,毕竟存在着那么一个人。他有些伤感。
宁见他这副模样,不失时机地提出:
——上我那儿坐坐吧,不远。
这时候他们刚好来到一个岔路口,本来顺着左边的林荫大道走到头,搭10路小巴就可以回来他在南窑的家,可是他没有拐向林荫大道,却选择了随她横穿马路走向右边。
与一位装扮肃穆的女人一道横穿马路,对他来说还是头一次。
安就不一样了,她总是很在意自己的扮相。每次出门前都要在镜子前折腾几十分钟,还说要是不打扮好,她抵死不出门。
他说你不是挺漂亮的吗?
她左照右看,就是不放心。
——我从来不照镜子,还不照样活得好好的。他又说。
——那是你自信,自信就不用照镜子。她说。
——我是男人,男人不怕脸皮粗。
——也许吧。她承认。
尽管他取笑她打扮,可是他承认,她清清秀秀光光亮亮地走在他身边,他还是很得意的。
他坐在宁的客厅里。这里没有玫瑰花,但是有茶。宁似乎有些紧张,不停地走来走去,出入于各个门洞,一会儿端来茶,一会儿换音碟,嘴上说着斯特拉文斯基不好听,肖斯塔科维奇也不好听,还是听柴可夫斯基吧。其实他哪个斯基都不想听,只想听风。
安就像旷野上的一阵风,来去自如,他始终无法追随。他四处推销廉价首饰时,她在小城机关做小职员,他回到小城想跟她长相厮守,她却跟一个陌生人走了,这次他赶到医院,她又先行去了火葬场,等他赶到火葬场,她已经化作青烟,穿过烟囱跑上了蓝天。跟她相处他总是慢一步,永远都慢一步。
——我在冰岛等你。
这是安最后一次约他出来时提出的见面地点。
冰岛在中心广场的西北角。他刚踏上东南角的南美火地岛,就远远看见她站在秋风中,站在冰岛的位置上。风吹动着她的裙裾,她茫然望着过往的人流,显得那么孤单。人们匆匆从她身边走过,有的走向好望角,有的走向北极圈,有的走向西伯利亚,谁也不理会她。只有他隔着宽广的太平洋,挤过人流向她靠近。
他们刚在距离冰岛不远的一家酒吧内坐定,她就说:
——我已经厌倦了。
——厌倦什么了?他问。
——生活。
——哪种生活?
——你就没想过改变改变?她幽黑的目光看着他。
他问她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幽黑的目光暗淡了下去。
——我知道我是个庸人,你迟早会厌腻的。可是我喜欢你,你是我唯一喜欢的。他说。
她避开他的注视,叫女招待端来两杯啤酒。
——你明天又要出门?她问。
他说是的,这次去深圳和东莞,机票已经买了。
——可以不去吗,或者晚几天再去?
——恐怕不可以,那里销售情况很好,我得去结清账目……
——你觉得这样下去,我们快乐吗?
他说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快乐。
——那还为了什么?她问,来了点精神。
——就为了活着,吃饱穿暖,看看树发芽,还有月全食。他说。
她眼中的亮光再次黯淡下去。
他们没有继续探讨哲学,听了几首流行的爱情歌曲后,起身离开了酒吧,无言地穿过广场,走过冰岛,走过英伦三岛,走过圣赫勒拿岛,沿大西洋走了一段路,最后在古南门的三岔路口分了手,他去他南窑的居所,她回她玫瑰盛开的住处。
宁不知何时换了一袭宽松的浅色长裙,坐在他的身边,手里端着一杯热茶。
——你在想什么?她问。
他说他在想刚才走过的那段路。
——杉湖北路吗?
——对,我小时候上学,总走那条路。
见她神情专注地望着他,他又说:
——古堡餐厅的楼上,就是我上小学的课堂。
宁啜了口茶,一笑,显然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但又不想打断他。
他本来还想展开对校园的记忆,说说古槐、石狮和长满春草的石板台阶——每次走过那栋华丽的商厦,他总会产生这些怀想,见她现出那种笑容,便没再往下说。
——你家里很整洁,跟你的牙一样。他说。
这回她真的笑了,露出一排细齿。
——你是头一个来这里的男人。她说。
——我不是头一次进单身女人的家。他说。
——这我信,看得出来。要参观一下吗?
她带他参观了她的卧室。里面也没有玫瑰,只有一个衣柜。当然还有一铺床和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只空花瓶,花瓶旁是一帧她自己的照片,穿一件白底青花上衣,站在一堵墙前,像是一只明代瓷瓶。
他把这个感觉告诉她。
——是有些古典。她说。
他把照片放回花瓶旁。
——我们去兴坪散散心,怎么样?草坪或花坪也可以。她又说,说得很随意,好像与他已是多年好友。
——行啊。他说。
这么快就答应,连他自己都有些惊讶。
——明早出发,怎么样?她笑着说,再次露出整洁的细齿。
这天晚上他没有走,在梦中闻到了栀子花的味道。他从来也没有闻过栀子花,可他相信那就是栀子花的味道。
都说安很性感,嘴唇如何如何,乳房如何如何,腰肢又如何如何,等等,男人对于可望而不可即的女人,总会生出非凡的想象力。可是在尚可的记忆中,安是一个真实的女人。
她总是默默地看着他,眼神在幽暗的灯光下闪烁光泽。当然她也会发出声音,发出那种短促而低沉的叫唤声,让你分辨不出是痛苦还是快乐,只有努力注视她的眼睛,从中发现那种温情的亮泽,这时你才能确定温暖的火焰,正在她体内冉冉升起。
安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见过她最美丽的时刻,他见过当生命的欲望逐渐高涨,女人的欢乐是如何焕发出来的。只要闭上眼睛,他就会想起她那黑亮的头发,修长的手指,优美的脚踝,还有小巧的乳房、平滑的小腹,和小腹下面的玫瑰花瓣。她说她的乳房不够大。可是他就喜欢那么小巧的乳房,喜欢它们的精致与敏感。只要是她身上的一部分,他都喜欢。他喜欢用下巴托住,轻轻啜吸那些粉色的凸起,感觉她的嘴唇和小腹一阵阵颤动。那些凸起很饱满,也很有弹性,比他想象的要结实得多。他特别喜欢她伏在他胸膛上的感觉,那样可以感受凉爽的气息吹拂他汗津津的肌体。他以为他把一切都忘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所有的记忆都蛰伏着,不到时候不会出来。
第二天他跟宁去了兴坪。五个月后两人结了婚,于是就有了这趟旅行。
三
其实在轮船上时,他和宁是恩爱的一对。
谁能相信他们会吵架呢。宁穿了一条白色长裙,手里拿了一件镂空黑色短线衣,这是她最喜爱的穿戴。他只穿了一身浅色西服,虽然简单,却也利落。他们总是并肩走在甲板上,身高相当,穿戴相当,连步伐都很协调,总是保持着从容的仪态,从前甲板走到后甲板,又从后甲板走到前甲板,有时还手牵着手。若是遇上熟悉的人,就同时做出愉快的微笑。
当然他们在轮船上没有熟人,用不着老是做出笑容,可是两天下来也不知不觉结识了几个乘客,其中一位系着粉色丝巾的金发小姐,是在二等舱的娱乐室里认识的。
她说她叫安娜,是意大利人,来自都灵。
他承认他一直很注意安娜,只要宁不注意,他就会看她几眼。
安娜什么地方吸引他呢?
孤单。
他很容易被那种孤单的女人所迷住,她们形单影只地穿行于车站码头,拎着行囊或背着背包,似乎很坚强,而实际很无助。这种女人身上有一种奇特的温柔,那种温柔藏在坚强的外壳后面,显得分外珍贵,不像那些看似柔弱的女子,等你满心怜爱靠近,触到的却是暗刺。
安娜坐在娱乐室的落地窗前,隔着窗玻璃看风景。窗外其实并没有什么景致,除了雨,就是海。因此她与其说是在看风景,不如说是在想心事。
娱乐室里什么肤色的人都有,大都身穿休闲装,有的玩牌,有的聊天,只有她孤单地坐着,守着半杯啤酒,粉色的丝巾如同孤独的旗帜,显眼地荡动在她耳际。
经过两天航行,他和宁已经相对无言,无论是往事还是现实,服饰还是心事,都或多或少谈过了,当然安是不谈的,那是个危险的话题。宁肯定也注意到了安娜,她虽然是个女人,但跟他一样也对年轻女人感兴趣,只不过他注意的是她们的眼神,而她注意的是时装。
不知是因为海风袭人,还是被安娜的穿戴所触动,没过多久,宁就说要回船舱换件衣服。
他走到落地窗前,跟安娜打了招呼。
——雨真大。他觉得自己的英文很蹩脚。
——对啊,不过感觉很真实。她的英文也不太顺。
——怎么呢?他问。
——各人感觉不同吧。
她望他笑笑。
安娜的眼神果然像安。
她知道他心中有一个安吗?不会知道。
她是别人心中的安吗?不知道。
——我为什么总在这种地方见到你?他问。
——你见过我?
——好像见过。
——你说这种地方是哪种地方?
——人来人往的地方。
——是吗?我确实总在走动,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没法在一个地方待久。
——爱人身边呢?
——那当然了。不过,爱人只是一个梦吧。你那位小美人呢?她四处望望。
——走开了。
——瞧,如今的女人都不太安分。
他和安娜还聊了些别的。后来宁回来了,肩上多了一件披肩。他为她们互相做了介绍,做得似乎很自然。可是后来宁说我知道你会去跟她搭讪,所以故意走开。
——大家同乘一条船,认识认识也好吧,万一船翻了,也有个照应。
——船翻了还不知道谁照应谁呢,先救她吧?
——当然先救你。他说。
——这么肯定?
——她会游泳。
观察女人与女人交往是很有意思的,常常会有一些意外发现,因为你会看到女人的另一面——更虚假或者更真实。安娜取出一盒烟,在征求了宁的意见后,抽出细长的一根叼在嘴上。我知道宁是抽烟的,但她拒绝了。
——你们是出来度蜜月吧?
宁的脸色有些窘,不过她整了一下披肩,马上就掩饰过去了,说:
——是呀,本来不想出来,最后还得依他。
——两个人真好,走到哪里都成双结对,不像我……
他插话说谁不知道如今的女子都喜欢单身,单身引来的就不只是一个男人的怜爱了。
宁也附和他,说:
——单身多好啊,想去哪就去哪,不像我们,经常为下一站去哪吵个没完。
——是吗?你们下一站去哪?安娜问。
——还不知道呢。你呢?宁问。
——我也没有想好。
他说一个年轻女子出门远行,总是有些想法吧。
——当然有想法,想看看这个世界有多大,哪里更适合自己生活。
——找到了吗?他问。
——还没有。我不太喜欢大城市,纽约哪是人住的地方。
——我喜欢。宁说。
安娜点点头,表示理解。她指间的香烟只过了一会儿,就剩下半截。
——你们呢,去过意大利吗?她问。
他说曾经想去,但没有机会。在书本上见过比萨斜塔、佛罗伦萨壁画、米兰的模特儿和威尼斯的桥。
她笑了。过了一会儿,说:
——我准备去桂林,听说那里的河流下游有一个小山村,可以通宵坐在山谷里看月亮,喝啤酒,小伙子也很朴实。你们去过吗?
——去过。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宁说。
——你呢,你也是?
他点点头,说:
——那地方叫阳朔。
轮船靠岸后,他们看见安娜背负着行囊,孤单地走在中国南方的雨中。
那根引信缓缓燃烧着。
宁摸出一根香烟,望着酒店外飘飞的雨珠,并没有点着。
她把玩了一阵那根烟,说:
——我总是不能完整地得到一个男人,这是为什么呢?只因为我不如安漂亮。可是我多么想完整地得到一个人,一个男人,而安活着时,这似乎就不可能。
她没看他,又说:
——你知道吗,我曾经很想结婚,就为了打乱她内心的平衡,是啊,她是从来也不结婚,可她依然害怕别人结婚,世上每结婚一个女人,她的内心就要承受一次打击,如果告诉她新郎曾经暗恋她,她甚至会丧魂落魄,佯狂醉倒在别人的婚床上。
她把烟掰成一段段,揉搓着里面金黄的烟丝。
——你知道吗,她曾经在我面前如何炫耀你?她炫耀你其实只是想炫耀她自己。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向自己的女友炫耀自己的恋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我有一次半开玩笑对她说:他那么有意思,小心我把他夺走哦。我以为她会笑成一团,可她却淡淡一句:不可能,他不可能看上你这种女孩。
她使劲闻了闻搓过烟丝的手指。
——我心中一阵创痛,可嘴上还故作俏皮地问为什么。她说她知道你欣赏哪种女人,反正不会是我。我怎么了,我觉得自己脑子比她管用,为人比她真诚,不就脸蛋没那么俊俏吗?她并不知道她说这句话时,嫉恨伴随着血液在我周身奔腾!好在那时她并没有注视我,否则她会被我的眼光杀死。
她将烟丝扔进烟缸,拍了一下手,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
——尚可,你知道吗?昨晚我在船上梦见你,也梦见她了,她系了一条粉色丝巾。我梦见她和你在船尾的甲板上说话。可是我并不痛苦,不但不痛苦,而且还坐在一旁,欣赏你们的表情。你们的表情都很痛苦,这正是我想看到的。后来她不见了,只剩下你站在栏杆边发愣,可我也不想过去安慰你,这下你该明白了吧,我并不爱你。
她幽幽地看着他。
——她活着时,我不可能完整地得到一个男人,如今她死了,我承认我还是不可能。你承认吗,你对待她和对待我是不一样的。你写给她的每一封信,我都看过,我甚至可以背诵里面灼人的句子,就好像那些句子是写给我的。别不好意思吧,你得承认那些句子没有打动她——或者只是暂时打动了她——可是打动了我。你要承认,你爱的是安,我只不过是安的影子,你太爱她了,所以哪怕娶她的影子为妻,也愿意,对吧?
他捧住她的手,贴在自己脸上,闻到一股浓浓的烟草味。这种味道他并不陌生,是烟叶燃烧以前的味道,非常纯正。他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这种味道了。他用力吸了一口,放下她的手,又捧住她的脸。暮色已经降临了,窗外幢幢高楼渐次亮起了华灯。他开始吻她,从额头吻到嘴唇,从下巴吻到颈项。在霓虹灯跳荡的灯光映照下,他注视着她那张泪光闪烁的脸,和那双燃烧的眼睛。
(原刊《上海文学》2001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