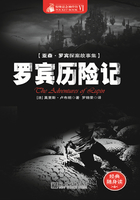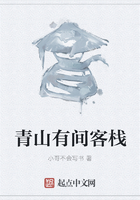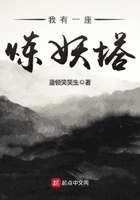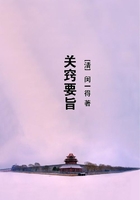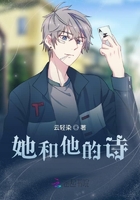访问文学评论家李陀的时候,他觉得80年代,跟今天对照有很多区别,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聊天聊出来的东西。“那时候重友情,朋友多--而且都是那种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可以信赖,可以交心。那时候的朋友信赖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个尺度?我觉得有,就是可以争论,你的朋友是可以争论的朋友--不是一般争论,而是凑到一起,以争论相激,以争论为乐。”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查建英虽然跟书里的甘阳、李陀等人立场不一样,但是依旧能够谈得下来,即便可能常常会有一些激烈的争论,就是仗着当年交下来的友情。
甘阳,这位80年代非常年轻就已经成为文化热中一派思想领袖的人物,也说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当年他们这一帮知青,回到城里的时候,慢慢身上就会有一种江湖气。“比如说会有一个口耳相传的圈子,会越传越多,你在这里,别处人家会知道你,很微妙。流传实际上是很广的,可以传得很远。”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晓得在北京某个地方一个小圈子里,你读书读得多,思想特活跃,才华特高,把一伙人都说服了,于是本来属于这个小圈子里关于你的想法会慢慢慢慢传出去,甚至传到好远的外省去,这就是甘阳所谓的“口传的圈子”。仗着“口传圈子”里对他的推崇,后来甘阳做起事来的时候也得到了很多帮助,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
可是大伙儿天天这么聊天、神侃,到底侃些什么东西呢?大家在书里说了,当年的文化热就是注重讲思想。这所谓思想给人一种聊天聊出来的感觉,底下的基础好像不是很扎实。
当年李泽厚曾说,进入90年代,很多人谈王国维、陈寅恪,而不谈陈独秀、李大钊,于是他概括出一个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的公式,也是当年很有名的说法:80年代有思想,90年代有学术。这个思想和学术的对立到底有多准确呢?或许这个说法太粗糙,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是,80年代的人学养方面可能的确有点问题。
访问陈平原的时候他说:“我们批评当下学术风气败坏时,往往举出80年代作为对比,不知不觉中将其理想化了。作为过来人,我很欣赏80年代的生气淋漓;但我必须承认,80年代的专业著述,大都激情有余、功力不足。套用胡适谈新诗的一句话,来描述我们这代人的工作,那就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可是这些人在聊,总不能光是聊,他们总得有养分,那养分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些人总不可能是80年代一改革开放就从冻土里面长出一棵树来,所以肯定在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潜流了。
关于这一点,艺术评论家栗宪庭说:“比如说上海《12人画展》,就隐藏着这样一条线索。即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短期的小规模现代主义。”有一些东西就是这么流传下来,而且后来资讯匮乏的时候,他们吸收资讯的方法也很特别。像著名画家罗中立的画里有美国超级写实主义的影子,他是怎么认识到人家东西的呢?居然是在一个外国的旧报纸上面看到一个画片,就这样学懂了一种外国绘画的方式。
前两年,查建英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的时候,曾经有人批评这本书以及里面访谈的那些文化名人,说他们太自恋了,说这帮人老觉得自己80年代的时候多牛逼、多了不起,然后就使劲回忆。其实仔细看完就会发现这本书完全不是这个感觉,相反,他们有很多的反省和反思,反省的正是一些关于80年代的神话。
说起来今天很多人怀念80年代的理想主义,怀念80年代的人有思想、有激情,喜欢谈文化,怀念80年代的时候刘再复一上台讲他的《性格组合论》底下居然有上万的观众,怀念那个时候诗人在大学里面可以招摇撞骗、泡妞。可是那个年代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书里就有很多反思。
比如查建英在跟刘索拉谈的时候,刘索拉说得也够狠,她说:“其实想想,80年代的中国有点像欧洲18、19世纪--信息不发达,哪个国家发生点儿什么艺术上的事也就进入史册了。80年代的中国现代派,其实就是靠着进来的那一点儿信息,加上胆儿大,敢把那点儿信息叮铃咣当地攒巴出来一点儿东西,其实也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从来没发生过,于是乎大家就觉得:哇!整个国家就冲着这几个人去了,把他们的成果夸大,夸张了多少多少倍,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她说结果那时候连老外都被唬住了,后来很多老外看中国艺术,说:“你们在什么西方物质基础都没有的状态下实现了这种现代艺术形态,使第三世界出现了现代艺术,这就是价值。”刘索拉说:“你要是整天听这种第三世界艺术价值观,就只能对艺术创作抱着侥幸心理,就永远不可能享受艺术创作的真正快乐和获得在艺术上的真正魅力。”
此外她还评论了民国时期的中国音乐家讲究对学问的追求:“文革前的音乐家也是只有一腔热情为民族为革命,而不会动辄就想什么历史意义的。真正的精英意识应该是指对专业质量的纯粹追求,而不针对作品的社会轰动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起,我们的社会有了那种当兵就要当拿破仑的意识。”显然她的批评指的是当前的中国文化界,但她把这个病根追溯到了80年代的问题上。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人物比较特别,电影导演刘奋斗。其实刘奋斗本来不是这一伙儿80年代的文化明星,相反,他是在80年代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跟我年纪差不多。
这本书找他有点儿像保持距离重新反思甚至是批判80年代种种现象的感觉。
他说话果然够狠。他说:“整个80年代那种什么伤痕文学,包括小说,都是面目非常可怖、非常狰狞,很痛苦。我×,受苦了,我得赶紧跟哥们儿几个说说,我受苦了。我挺怕这种人的,这种人我自己觉得在心态上都有点儿像街边卖大力丸的一样,拿起一块砖头‘啪’先把自己脑袋拍碎了,流着血说:大爷,您给一点儿吧,再不给多不合适,带着孩子不容易啊!”他用这么一个比喻也真够挖苦的。至于刘奋斗为什么后来在大陆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里没有出现,有人说因为他谈到了一些学生闹事的事情。可是我看他这一段觉得就像查建英所说的,他这番话简直能够上《人民日报》当社论了。
他批评80年代末期闹事的那帮学生,他说:“我不相信,一个大便完了不冲厕所的人能管理好国家,你们是大学生,不是孩子啊……因为我住在那个地方,有时候在教室、学生宿舍和学生们打打麻将,我都能看到,我×,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十八九了,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大小便完了,您冲水成吗?我说你们真想要改变中国,先从大小便冲水开始。”看来他实在太关心大小便冲水的问题了,他认为这是国家前途所系。
后来他还批评了一下中国的文化艺术,大家都说现在中国的足球不行,可是刘奋斗有这么一个想法:中国足球队的水平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中国文化界、思想界、艺术界的水平。在这些方面我们并没有比足球表现得好了多少,我们大家都是一批机会主义者。譬如搞电影的人,永远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和热情在后面,总是做了一件事算一件事,慢慢一步一步改,一步一步来。他认为这样做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但是为什么大家瞧不起中国足球,却没有很瞧不起中国的文化艺术呢?那是因为“中国有句老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整个行业容易被遮羞,不像足球似的那么难看,立刻见真章”。
但是话说回来,80年代是否真的有那么不堪呢?这本书里很多人都提出了很深切的批评和反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80年代也有它的重要作用。
阿城被誉为是这本书的受访者里面讲得最好的一个人,他说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大家重新拾回常识的过程。以前二三十年里面,中国逐渐出现了文化断层,很多常识不见了,怎么做人,什么叫做知书达礼,这些东西都没了,而找回常识或者说重新发掘人性的过程我们永远要记住,这对80年代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觉。
这本书里面还访问了陈丹青,他记得80年代早期,他到美国第二年的时候,在《纽约时报》上看见一张黑白照片,报道山东潍坊举办国际风筝节,一群人挤着、笑着,仰望天空。“我一看,几乎要哭出来:他们笑着,一脸苦相,那种长期政治磨难给每个人脸上刻印的苦相--要是我在中国看这照片不知会怎样感受。我不知道是难受还是宽慰,总之心里委屈,为几代人委屈:中国人不闹运动了,知道玩儿了!放风筝了!”
作者小传
查建英,笔名扎西多,自由作家、撰稿人。曾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Pop、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等。其中ChinaPop被美国VillageVoiceLiterarySupplement杂志评选为“1995年度25本最佳书籍之一”。
《七十年代》Ⅰ
酝酿在70年代
80年代并不是突然之间在真空里面爆发出来的,它前面一定有一个背景,而这个背景从时间上讲自然就是70年代。70年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60年代“文革”爆发,中国文化受到了很严重的摧残,80年代是开放思想,文化热,整个中国进入一个解冻、花开的时期。夹在中间的70年代貌似比较平淡,但今天在我们国家很多重要领域里面的中坚分子都是经历过70年代,从80年代开始踏上社会的舞台,他们身上烙着70年代留在身上的印记。为了追溯这样一个历史轨迹,给大家介绍一本新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十年代》。
这本书的概念看起来跟《八十年代访谈录》差不多。
可是诗人北岛跟评论家李陀主编的这本《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访谈录》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本访谈,它是邀请了几十个人,一人写一篇回忆,一人写一篇自述。在这些回忆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对那个年代的感觉、印象是不同的。这里面绝大部分的人都有过知青下乡的经历,但是知青下乡体会到的东西也有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是从这里面找出了一些共性。
什么共性呢?70年代到80年代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种一帮人聚会的状态。在70年代,这种聚会尤其令人觉得好奇。每一个人都提到当年的聚会,我们知道那种聚会是有风险的,所以他们私下聊些什么、看些什么、听些什么,交换一些什么样的灰皮书、黄皮书,交换一些怎样的唱片、讯息,这些都是我所好奇的。
张朗朗《宁静的地平线》写道:“1970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草棚里、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在那个年代,大面儿上看来是个文化贫瘠的时代,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80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勃发。”
朱正琳也说,那些知青下乡的村子,原来是隔绝的,管得很严的,但是到了1976年,已经实现了村村通。村村通后,大家已经意识到表达权利对于思想自由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于是就发生了一件当年很有名的事情。当时有几个写诗的朋友到北京,把自己创作的诗歌贴在北京街头,后来索性成立了启蒙社;接着又有几个画画的朋友到北京街头举行了一个飞行画展,被称为“五人画展”;还有一个人只身到天安门广场站了几天,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是要求继邓小平访美之后他要访问美国。70年代末,这些人到底搞什么呢?其实这背后有很深的政治含义,用大白话讲,他们要求的就是“公民旅行”,或者说是公民出国的自由。
这些人在70、80年代的时候,如此活跃地跑来跑去,天天谈那么多事,到底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北大中文系李零记录下这段回忆,起了个小标题叫做《没电话,怎么约会》。他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回忆,痛苦地回忆,就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电话普及已经是90年代的事了,那时候这些人怎么约见面有很多种说法。李零问过,有人说是这回约的时候顺带约好下回;也有人说直接串门,挨家挨户串。那时候大伙儿怎么能够一起骑车到百里外凑到一块儿去始终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些问题对做知识分子史研究很重要,不要把它当成鸡毛蒜皮的事,必须要搞清楚,这里面可能说明了一种社会网络。这种群体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出现跟结合,消息流布的机制是怎么样形成的,都很值得研究。当然,你也不要把这些小型的沙龙想象成法国启蒙时代那种很文艺、很高雅的沙龙。它无非就是大伙儿凑一块儿,可能在某一个人的家里,聚一聚、聊一聊,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只是发生在一些批斗的场景中。
韩少功说他第一次看到手迹本,也就是手写的文学,是有一回去抄家。当时他们是红卫兵,抄走了一个老人的书。那个人是老南洋华侨,当过美军翻译,一见红卫兵的模样就知道要挠到哪儿是痒处。因此这个人老跟他们讲故事,他们逼他交代,其实是想认真地听他说故事。谁知老人一说就说了很多,说万恶的美帝国主义怎么样怎么样,重点却是放在可口可乐多好喝、巧克力多香上。结果大伙在这个挨批斗的南洋华侨老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过去所不知道的南洋知识、海外知识,这是一种说书,也是一个读书的过程。
本来要批斗一个人,要他交代的一个场面竟然慢慢变成了一个沙龙,变成了一个集体学习。说到兴奋处,这个南洋华侨还会跟这些红小兵们说:“你们连枪都不会擦还拿什么打仗?不是胡闹么?”这些“革命小将”们听到也并不生气,他们继续听这个老人家“教训”他们,给他们讲这世界之大。
都说60年代是焕发理想的年代,满腔热血,但是到了70年代,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个幻灭的年代,但幻灭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却很难说。比如知识青年下乡,发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田间地头的农村生活没有之前所说的那么好,甚至还不如解放后自己出生时的城市好,能不幻灭吗?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像林彪叛逃、毛主席去世,对很多人来讲这都是值得回忆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标志着某种意识形态,甚至是某种信仰,在那一刻被时间停住,留给人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