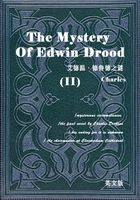不搞科学管理,不搞法制,只能是使人们在各种运动中练得头脑过于灵活,嘴巴过于精巧而已。你现在随便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传达文件让他们讲艰苦,他们立即就能讲出他们如何如何艰苦,艰苦得简直就在饥寒交迫之中,艰苦得都能使你落泪;如果文件要他们讲幸福,他们嘴巴一变,就能讲出他们幸福得彩电冰箱空调一大堆,人均增长多少多少钱,已经富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了。(笑声)这种弄虚作假本来是不断搞运动造成的,却又用运动的形式来解决弄虚作假,这就使我们的弄虚作假发展到极至。
我不认为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趋向表扬与自我表扬,而是我们现在毕竟改革了,运动这种一阵风的形式对人们渐渐失去了权威性,也使人们感到腻烦了。于是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你要这样,我偏要那样的黑色幽默。
问:如果在“文革”时你不是一个“狗崽子”,而是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你会不会成为一个造反派?
答:我肯定会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你想想当时是多么热火朝天的时代,所有的口号都那样的激动人心,所有的理想都那样的光辉灿烂,当国家成为政治欺骗的主谋时,谁也难逃法网的。哪一个有热血的想进步的青年会不响应国家的号召呢?
问:我是“文革”以后出生的青年,从我学到的知识来看,“文革”是“四人帮”搞的,“四人帮”能代表国家吗?
答:“四人帮”是以后的说法,当时号召你造反的就是党中央,就是国家最高领导。最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都戴着“红卫兵”的造反派袖标,你还能怎样呢?如果说一个掌管最高权力的,洞察一切的英明领袖也能被“四人帮”欺骗卜年之久,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太荒唐也太可笑了!
问:从现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性文章来看,人们对“文革”恨透了也伤透了心,给我的印象是,几乎是一声令下,人们就把平日里朝夕相处的领导打翻在地,甚至活活折磨而死,这种招之即来的凶狠使我很难理解。你能理解吗?
答:老干部们在“文革”当中确实吃苦受罪倒了大霉,但要说这种冤屈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并不以为然。从表象来看,“文革”似乎是平地一声雷就爆发起来的,实际上这个大灾难是有着无数个小灾难垫底,才会走向疯狂的高峰。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各种运动,把人们打成右派,打成右倾,打成反革命,砸碎饭锅大炼钢,逼着老百姓排队吃大食堂,最终把全国人民带进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坦率地说,“文革”之前,我们的干部远不是老百姓的父母官,老百姓是有一肚子气的。所以,“文革”的炮声一响,就能迅速地调动干百万人的仇恨。总觉得“文革”之前是风调雨顺相亲相爱的年月,这是人们不自觉的误区。
问:“文革”是最压制文化的时代,据说你在“文革”期间读的书最多,为什么?
答:“文革”期间是我读书的大好机会,因为城市到处响着武斗的枪炮声,你就不用去上班工作了。另外,几乎所有的业余爱好都属于资产阶级范畴。所以你惟一的能力就是看书。实际上看书是更可怕的爱好,因为几乎所有的书都被打成反动的书。但当时所谓不反动的书全是枯燥无味的假话,你无论怎样下定决心都看不下去,所以你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看“反动”的书。我们有妙法,就是用“革命书”的封面套在“反动书”的上面,你就可以大看特看。更妙的是报刊上不断地批判什么书,这简直就像做读书广告似的。因为根据经验,越是老百姓愿看的,越是有意思的书,上面就越批什么书.所以,我们每天都密切注意批判动向,只要看到一本被批的书名,就赶紧去寻找。在寻找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大家都是这种阅读心理,因此每个读书人的积极性全调动起来,寻找和交换各种书比现在还容易。
生活杂谈
问:你是球迷吗?
答:我曾经是球迷,但现在不是了。因为我迷了多少年后,渐渐地觉得不太合算,整天叫喊得嗓子冒烟,激动得心跳一百八十下;有时为了看一场球赛,工作不干了,孩子也忘在托儿所里不接了,还自己搭上车钱和门票钱,自己花钱买红布写标语,甚至还得同妻子吵上一架。结果呢,我所有狂热的希望全都付之东流。
突然的一天,就像上帝用智慧的手指在我的脑门上弹了一下,我大梦初醒,觉得我这是中邪了吗?世界上难道除了足球就没有别的吗?我们的足球就是踢遍天下无敌手,工人就不下岗了吗,经济就会腾飞了吗?住房问题,失学问题,假冒伪劣等等问题就解决了吗?当年我们有一阵子乒乓球打遍全世界,结果丝毫也没改变当年残酷的生活,反面使那种残酷更有了存在的理由。
当然,也许我老了,热血不再沸腾了,脑海不再翻浪花了,所以,也就冷静下来。人一冷静,理智就占了上风,就不会再进入非理性的球迷状态。
问:你说球迷是非理性状态.是贬意还是褒意?
答:这并不存在贬和褒的意思,不用说球迷,所有的什么迷都是非理性。一个人要进入非理性不是件容易事,不是你想进入就能进入,而是一种情不自禁,一种疯狂的忘我。实际上成为真正的球迷是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你必须从生理、心理到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热爱足球事业,你必须不计任何个人得失,即使你只挣几百元工资,还要省吃俭用,有时还得忍饥挨饿,但却能全心全意地为那些挣几十万元的足球富翁们鼓掌打气。这种狂热在局外人看来是疯子是傻瓜是神经病患者的状态。只能用非理性才能解释才能支撑。如果你的理性很强,你就会严格地计算你行为的得失,你会痛惜你每一分钟的光和热,当球迷如此地不合算,你能干吗?
问: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能冲向世界?
答:既然我不是个真正和虔诚的球迷,对中国的足球就缺少那种深入骨髓般的了解,他们什么时候能冲向世界,我就不敢说了。如果非要我说,那我就直说几句,我们中国要想冲向世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早该冲出的都没冲出去,足球冲不冲出去有什么意义!(掌声)问:什么是幸福?
答:有人说幸福是发财,有人说幸福是爱情,有人说幸福是升官,有人说幸福是感觉。幸福往往像海平线,无论你怎么努力追赶也追赶不到;可当你回过头来,却发现,你后面竟然也是海平线。这就是说,你已经幸福过了。这就像一个诗人说的,人和幸福就是鱼和水的关系,等到鱼被钓到岸上晒成了鱼干,它就知道水的幸福滋味了。
因此,幸福其实是很抽象的,它像影子一样时时刻刻地伴随着你,你却只能是在回忆里品尝,或是在想象中遥望。如果此时此刻你切切实实能感觉到你幸福,这不是奇妙就是奇怪,很可能是你的脑袋出了毛病。一个人要是时时刻刻感到自己幸福,绝不会再有前进的动力和创造力;一个作家要是能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幸福,也绝对地写不出可以称作是作品的东西。(掌声)问:我们的新闻媒体,为了报导经济发展和前进,不断地选出一些代表人物出来唱赞歌,说现在的生活多么多么的幸福,你以为这是幸福还是宣传?
答:任何一个拍着胸脯说自己很幸福的人,从旁观者看来都是很滑稽的。奇怪的是我们的新闻媒体却乐此不疲,经常搞这样肤浅的宣传花样,找几个代表人物说自己活得多么多么的幸福。这不但让我们自己感到可笑,可能更让外国人感到可笑甚至可悲。这种拙劣的宣传方式我们用了半个世纪,土改时我们用这种方式宣传我们多么多么幸福,人民公社时我们用这种方式宣传我们多么多么幸福,“文革”时我们干脆就狂喊我们是更更幸福和最最幸福。其结果呢,我们不但是一穷二白,而且还是处在初级阶段,就是说我们离幸福还挺遥远。可是看看人家富裕的国家,尽管人们活得很幸福,但没一个人在电视和报刊上说我活得多么多么幸福,反而更多的是指责生活的不足。因此,人家就越来越富。
问:邓先生,中国有句老话: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你认为这是一个人思想的升华还是僵化?
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奇妙,你可以回答是升华,也可以回答是僵化。因为一个人经历得多,才能见识广。为此他就会知道什么是阴险,什么是狡猾,什么是口是心非,什么是笑里藏刀,就很难再被欺骗和愚弄。过去喊着美好的口号搞的各种害人害社会的运动,大都是年轻人一马当先,或批判或造反,穿着绿军装,带着红袖标,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结果沦为政治的炮灰,下场很惨。但老人却绝大多数不上这个当,所以,一般阴谋家都愿意利用年轻人,他们知道年轻人头脑简单,非常好骗。
成熟就是件好事吗?成熟的人往往会不由自主地陷入经验主义,这就使他对事物的看法变得很顽固。三十而立标志着一个人有了自己的基本观点,这样,而立之年以后的先进东西就很难进来;四十而不惑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对所有的事物都怀疑,都不动声色;五十知天命更是刀枪不入的高手,他既不前进也不后退,既不兴奋也不悲哀,既不勇敢也不胆怯,反正一切自有定数,像漂在水上的一块木头,悠然自得随波逐流。社会上如果全是这样成熟的木头,历史就不会前进了。
问:希望你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老人和年轻人的思雏特点,可以吗?
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老祖宗从远古的时候就开始总结,而且还留下了一些很精彩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两句:年轻人总是相信许多假的东西,老年人总是怀疑许多真的东西。我想这两句话足够我们用几个世纪,用不着我在这儿概括什么了。
问:如果你遇到一个非常凶恶的邻居怎幺办?
答:这个问题几乎就不像是一个问题,但细细想起来,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有邻居。(笑声)你走路时撞见一个凶恶的人,你可以和他打架,打赢打不赢都没啥问题.你以后很少能再撞见他甚至永远也不会见到他。但邻居就不行了,只要是有了纠纷,那你就算是倒了大霉,无论你打赢了还是打输了都永无宁日。所以,你的邻居无论怎样凶恶,你最好是不惹他。
但他要是凶恶到你不惹他,他也不让你安生,那你就来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是进法庭打官司,或是图穷匕首见,与他大打一场。但不管打赢打输,你都得赶快搬走,搬得越远越好。(笑声)问:我们经常嘁“理解万岁”这个口号,你也认为理解确实万岁吗?
答:我认为一个文化层次低的人不会有宽容的理解,我认为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才喋喋不休地强调理解,所以,我看到为数众多的人都在喊“理解万岁”,往往感到有些滑稽还有点悲哀。(掌声)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理解是最无用的东西,如果我要是乞求理解,今天我不但一事无成,而且还会被人当作傻子来嘲笑。
问:你认为精神重要还是思想重要?
答:如果这两种东西能分得开的话,我认为思想比精神重要。无论正确与不正确的思想,都能使你坚定不移地向前走你要走的路,无论幸福还是痛苦你都心甘情愿。但精神却没这个力量,他可能促使你干你不想干的坏事。比如说勇敢的精神,或是勇往直前的精神,听起来铿锵作响,觉得正确无比。但这是个极没有原则的东西。你要是在希特勒的领导下,你越是有勇敢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就越是侵略别的国家,越是杀害和平的人民;比如说勤劳或勤奋的精神,在当年瞎指挥的极左年代,你越是有勤劳勤奋的精神,你就越是大建土高炉,九炼废钢铁,实际上是勤奋地搞大破坏。如果当年搞大跃进,搞“文化大革命”,要是没有那么多的精神,争天改革也不会这么艰难了。(掌声)问:假如你不是出生在城市,而是出生在穷山沟里,你会不会感到这个世界不公平?
答:刚刚出生的几年我不会对生我的山沟产生什么恨,反而有山有树有草会使我有诸多童趣。但长大以后,我会知道我是农村户口,是个没有工资的农民,是个不能在城里居住的倒霉蛋。我要为“农转非”而奋斗,为进城而拼搏;我就知道我一生下来就面对不公平,就像长在阴沟里的树,要想方设法地挪到向阳坡上。过去,你只要是个农民,你就注定“农”一辈子。你就是进城当一百年工人,人家也叫你民工。
不过,上帝还是有着深沉的公平,一个在农村长大,再到城里闯事业的人,那就不可估量了,他凭着最底层生存的精明,会迅速地学习和掌握知识,实际上是会迅速地应用知识。他知道这个世界应该怎么对付,说得好听一点的就是怎么来驾驭。不信你看所有的城市,不管是大城市小城市洋城市土城市,当官的几乎全是先土后洋的人来担任。(笑声、掌声)问:你喜欢看“东方时空”里的“焦点访谈”节目吗?
答:我知道很多人都喜欢看“焦点访谈”,因为这个节目敢大胆地揭露社会上的黑暗和不公平,使观众看了解气解恨。但坦率地说,这种新闻“包公”实际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有正在发生着的不公平事件,都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并非是哪个人的思想道德问题所致,而是体制的产物。在缺乏科学和民主的管理体制下,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的包公式访谈,无论多么努力,也只能像在牛身上一根根拔毛,这边的毛还没等拔完,那边的毛早就长出来了.只能使人更感到悲哀。所以,我不怎么看这个节目。
问:我楼上的邻居是个十足的坏蛋,每天晚上都把地板踩得咚咚响,让我很难A睡,关键是我脑神经不好,这就更惨了。我曾心平气和地上去说过几次,但他们还是照样踩得“咚咚”响。真把我气坏了,有时气得我真想冲上去与那个坏蛋邻居大打一场,至少是痛骂他一顿。否则我就会被这个坏蛋活活折腾死!
答:你千万不要冲上去和邻居打架,那更会要你的命,你想想,你要是打不过人家,反倒被人家痛打一顿,多不合算,这样你就是能睡着觉,也会疼痛得睡不着。反之,你要是能打过人家,那更不得安宁,你把人家打痛了,人家当然不甘罢休,这就造成你每天都得神经紧张地预防人家报复,甚至还要做好到法院打官司的准备。另外,从此你头上的楼板不是踩得“咚咚”响,而是会像打雷一样变得“轰轰”响了。
所以,我帮你想了三种解决办法:一、你要是有能力,最好搬家。当然,搬家不是件容易事,那你就采取第二个办法,买个耳塞子,据说有美国进口的耳塞子,隔音质量最好。如果你戴耳塞子不舒服,就采取最后一种办法,再次心平气和地到邻居家,告诉他们你实在是受不了声音的干扰,为了不再有声音,你就说给他们家买块地毯,他们大概就会不好意思了。如果他们同意你给他们买地毯,那我也只得投降了,因为你这家邻居确实是坏蛋,而且是全世界最坏的坏蛋。(笑声)问:经常在电视里看到你参与的节目,很羡慕您的幽默机智和镇定自若。我这个人其他方面还算可以,就是没有口才,不会说话,属于那种煮饺子的茶壶,肚里有却倒不出来,请问邓老师,我怎样才能把我这该死的“茶壶嘴”打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