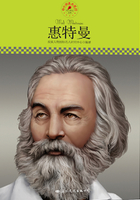我所以这么好奇,是因为自己也一直被索序者所困,虽也勉力写了一些,却仍负债累累,虚诺频频,不知何时才能解脱。
迄今我写过的序言,应已超过百篇。其中当然包括为自己出书所写的序跋之类,约为四十多篇;为画家、画会所写的英文序言约为十篇;为夏菁、金兆、於梨华、何怀硕、张晓风、张系国等作家所写的中文序言,不但置于他们的卷首,而且纳入自己的书中,也有十篇上下。余下的三十多篇,短者数百字,长者逾万言,或为专书所写,或为选集而撰,或序文学创作,或序绘画与翻译,二十年来任其东零西散,迄未收成一集,乃令文甫与素芳频表关切,屡促成书。而今奇迹一般,这三十几个久客他乡、久寄他书的孩子,竟都全部召了回来,组成一个新家。
序之为文体,由来已久。古人惜别赠言,常以诗文出之,集帙而为之序者,谓之赠序;后来这种序言不再依附诗帙,成为独立文体,可以专为送人而作。至于介绍、评述一部书或一篇作品的文章,则是我们今日所称的序,又叫作叙。古人赠序,一定标明受者是谁: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几篇,都是名例。至于为某书某篇而作的序言,也都标出书名、篇名:例如《史记》中的《外戚世家序》、《游侠列传序》;若是为他人作品写序,也会明白交代:例如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苏轼的《范文正公集叙》。
古人的赠序和一般序言虽然渐渐分成两体,但其间的关系仍然有迹可寻。苏轼为前辈范仲淹的诗文集作序,整篇所述都在作者的功德人品,而对其作品几乎未加论析,只从根本著眼,引述孔子之语“有德者必有言”,并说“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欧阳修为同辈梅尧臣的诗集作序,也差不多,直说作者“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畜,不得奋见于事业”;至于作者的文章,只说其“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而作者的诗风,也不过一句“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便交代过去。这种风气一直传到桐城文章,例如刘大櫆写的《马湘灵诗集序》,就只述其人之慷慨,却一语不及其诗之得失。孟子对万章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种“知人论世”的文学观对后代影响至大,所以欲诵其诗,当知其人,也因此,古人为他人作品写序,必先述其人其事。在这方面,一般序言实在并未摆脱赠序的传统。
二
古人为人出书作序,既与为人远行赠序有此渊源,所以写起序来,着眼多在人本。序人出书,不免述其人之往昔;赠人远行,不免励其人于来兹。而无论是回顾或前瞻,言志或载道,其精神在人本则一。苏轼论苏辙,说“其文如其为人”;毕丰在接受法兰西学院荣衔时也说:“风格即人格”;其理东西相通。不过中国的传统似乎认为,只要把其人交代清楚,其文就宛在其中了,结果对其文反而着墨不多,不但少见分析,而且罕见举例,当然文章简洁浑成。
近三十年来,半推半就,我为人写了不少序言,其势愈演愈盛,终于欲罢不能。今日回顾,发现自己笔下这“无心插柳”的文类,重点却从中国传统序跋的“人本”移到西方书评的“文本”。收入这本序言集里的文章,尤其是为个别作家所写的序,往往是从作者其人引到其文,从人格的背景引到风格的核心,务求探到作者萦心的主题、著力的文体或诗风。
我不认为“文如其人”的“人”仅指作者的体态谈吐予人的外在印象。若仅指此,则不少作者其实“文非其人”。所谓“人”,更应是作者内心深处的自我,此一“另己”甚或“真己”往往和外在的“貌似”大异其趣,甚或相反。其实以作家而言,其人的真己倒是他内心渴望扮演的角色:这种渴望在现实生活中每受压抑,但是在想象中,亦即作品中却得以体现,成为一位作家的“艺术人格”。
这艺术人格,才是“文如其人”的“人”,也才是“风格即人格”的“人格”。
这艺术人格既源自作者的深心,无从自外窥探,唯一的途径就是经由作品,经由风格去追寻。所谓郊寒岛瘦、所谓元轻白俗、所谓韩潮苏海,甚至诗圣、诗仙,都是经由作品风格得来的观感,不必与其人的体态谈吐等量齐观。
我为人写序,于人为略而于文为详,用意也无非要就文本去探人本,亦即其艺术人格;自问与中国传统的序跋并不相悖,但手段毕竟不同了,不但着力分析,篇幅加长,而且斟酌举例,得失并陈,把拈花微笑的传统序言扩充为狮子搏兔的现代书评,更有意力戒时下泛述草评的简介文风。
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果不把作者的生平或思想交代清楚,就无法确论其人作品。例如温健骝前后作品的差异,就必须从他意识形态之突变来诠释,而我与他师生之情的变质,也不能仅从个人的文学观来说明,而必须从整个政治气候来分析。同样地,梁实秋的尺牍,也应探讨他晚年的处境,才能了解。遇到这种情况,写序人当然不能不兼顾人本与文本。
三
为人写序,如果潦草成篇,既无卓见,又欠文采,那就只能视为应酬,对作者、读者、自己都没有益处,成了“三输”之局。反之,如果序言见解高超,文采出众,则不但有益于文学批评,更可当作好文章来欣赏,不但有助于该书的了解,更可促进对该文类或该主题的认识。一篇上乘的序言,因小见大,就近喻远,发人深省,举一反三,功用不必限于介绍一本书,一位作者。
我为人写序,前后往往历一周之久。先是将书细读一遍,眉批脚注,几乎每页都用红笔勾涂,也几乎每篇作品都品定等级。第二遍就只读重点,并把斑斑红批归纳成类,从中找出若干特色,例如萦心的主题、擅长的技巧、独树的风格,甚至常见的瑕疵等。两遍既毕,当就可以动笔了。
至于举例印证论点,这时已经不成问题,只须循着红批去寻就可,何况许多篇目已品出等第,佳句或是败笔,一目了然。例证之为用,不可小觑,一则落实论点,避免空泛,二则可供读者先尝为快,以为诱引。举例是否妥帖,引证是否服人,是评家一大考验。常见写序人将庸句引作警语,不但令人失笑,甚至会将受荐之书一并抛开。
至于篇幅,正如其他文章一般,不必以多取胜。中国传统的序言大多短小精悍,本身就是一篇传世杰作。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原为东晋永和年间、一群文人在兰亭修褉咏诗而作。时隔千年,当时那些名士的诗篇已多湮没,这篇序言却一文独传。《兰亭集序》长约三百字,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也是为诗集作序,只有一百十七字:当日那些俊秀到底写了什么佳作,再也无人提起,只留下了这篇百字的神品,永远令人神驰。近人的序跋也有言简意长,好处收笔而余音难忘的:钱钟书的几篇自序,无论出以文言或白话,都经警可诵。当然,序言不必皆成小品,也有长篇大论,索性写了论文的。萧伯纳正是近代的显例:他的不少剧本都有很长的自序,其篇幅甚至超过剧本自身,而且论题相当广泛。
序言长短,正如一切文章的篇幅,不能定其高下,关键仍在是否言之有物,持之有理,否则再短也是费词。当代学者写序,以长取胜者首推夏志清。夏先生渊博之中不失情趣,为人作序辄逾万言,而又人本文本并重,有约翰生博士之风。我这本序言集里的文章,长短皆为参差,逾万言者也有五篇,其尤长者为序《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一九七〇—一九八九》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两篇,都几达一万四千字,可谓“力序”了。
为一群作家的综合选集写序,既要照顾全局,理清来龙去脉,又要知所轻重,标出要角、主流,所以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当然难免。《文心雕龙》序志第五十就说:“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三百作家二十年》与《当缪斯清点她的孩子》两序,面对那么多作者,背景迥异,风格各殊,成就不一,实在难以下笔,更遑论轻重得体,评价周全。例如《三百作家二十年》一文,对于诗、散文、小说三者虽然勉力论析,但对于戏剧和评论却照顾不足,终是遗憾。
四
序言既然是一种文章,就应该写得像一篇文章,有其结构与主题,气势与韵味,尽管旨在说理,也不妨加入情趣,尽管时有引证,也不可过于饾饤,令人难以卒读。序言既为文章,就得满足一般散文起码的要求。若是把它写成一篇实际的书评,它仍应是一篇文章,而非面无表情的读书报告,更不是资料的堆砌,理论的练习。
对我而言,为人作序不但是写书评,更是一大艺术。序言是一种被动的文章,应邀而写。受序人不外是一位作家,往往也是文友,对你颇为尊重,深具信心,相信你的序言对他有益,说得轻些,可以供他参考,说得重些,甚至为他定位。理论上说来,这种关系之下,受序人有点像新郎,新书有点像新娘,写序人当然是证婚人了。喜筵当前,证婚人,例如为李永平所写的那篇《十二瓣的观音莲》,就是小驻香港,在胡玲达高楼小窗的书房里写成,而为潘铭燊作序的那篇《烹小鲜如治大国》,也是休假之年去联合书院客座,在大学宾馆寂寞的斗室里,三夕挥笔之功。至于序王一桃的《诗的纪念册》,则是在温哥华雅洁的敞轩里,坐对贝克雪峰而得。旅途而能偿债,可谓闲里偷忙,无中生有,回国的心情为之一宽。
此地所收的序言三十多篇,当日伏案耗时,短则三数日,长则逾旬。如果每篇平均以一周计数,则所耗光阴约为八月,至少也有半年。人生原就苦短,能有多少个半年呢?当日之苦,日后果真能回甘吗?如果受序人后来竟就搁笔,我的序言不幸就成了古人的赠别之序,送那位告别文坛的受序人从此远行。这,也算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吧,思之令人黯然。不过当日之苦,也近多成为日后之甘的,那就是见到受序人层楼更上,自成一家,而我为其所写之序在众多评论之中,起了定位作用,甚至更进一步,成了文学史的一个注脚、一处坐标。
做了过河卒子,只有任命写序。想到抽屉里还有四篇序要写,不如就此打住。
一九九六年初夏于西子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