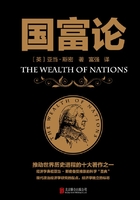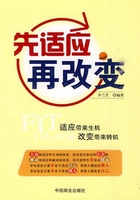1873年(癸酉)制造局译《列国岁计政要》,梁说此书出后“齐州之士宝焉”(2:59)。此后20年间未有类似的书出版,直到1897年5月,“知新报馆乃始得取去岁所著录者,译成中文附印于报末,乞叙”(2:59)。那时梁才25岁,尚未出国,他写的这篇短序,基本上是在解说书中所列各国各部门(民部、学部、兵部、海部、户部、商部)的预算额,说明从此书可知各国财政的强弱状况,以及各部门所分配到的经费比例。从经费增长的角度来看,“区区之日本,昔之文部省岁费不过十三万余圆者,今且增至二百五十三万八千余圆”(2:60)。从列国对各部门预算编列额的变动,梁指出一项事实:“户口之表,中国等恒居一,疆域之表,中国等居四,国用、商务、工艺、轮船、铁路、兵力诸表,中国等恒居十五以下,或乃至无足比数焉。”(2:61)他的用意很清楚:读者可以从此书知晓各国的兴衰状况,以及各地和平或战争可能性之大小(看军费预算即可知)。简言之,这是一篇介绍性的文字。
政府预算既为世界潮流,1910年清政府规定各省试办,由度支部编订例式。此项册式大抵根据日本的模式,内有预算例言22条,之后分成下列项目:(1)总则,(2)在京各衙门预算,(3)各省预算,(4)编订预算方法,(5)附则三项。之下有“各省试办预算报告总册”,内分:(1)岁入经常门,(2)岁入临时门,(3)岁出经常门,(4)岁出临时门,(5)地方行政经费经常门,(6)地方行政经费临时门。此6门之下各分若干类,每类之下又分若干款,每款复分若干项,再分若干目(25上:70)。因为这是试办性质,所以广征各方意见以备修改。梁写此文的目的,是要对这项册式的内容提出修正意见。大体而言,此文的内容都是具体技术问题的讨论,时过境迁无须评引。此文的意义,在于显示梁对清末的政府预算行政改革,在此时怀有相当的期望:同一年中央政府向资政院提出预算案,资政院审查修正后即将付诸议决。就形式看来,此事俨然有立宪国的做法,但梁细看此项预算案后大感失望:“而其最奇怪不可思议者,则收支之不适合是也。……据其所知者,则入不敷出之额约五千万两。……此可谓之决算案耳,不能谓之豫算案。此可谓之岁费概算书耳,不能谓之豫算案。此可谓之财政报告书耳。……若在他国有此等四不像之预算案出现于议场,……断不肯无益费精神以为之讨议。”(25上:159-160)
梁对1910年预算案的评语是:“内容卤莽灭裂,贻薄海内外以笑柄。且各部臣、疆臣视同无物,纷纷请变弃。”去年的事情既已无法追补,梁建议下列诸项原则,供筹制宣统四年预算案时参考。(1)收支宜必求均衡,(2)编制之事宜由行政官担任,(3)编制权宜集中于度支部,(4)编制宜以春间着手,(5)体例格式宜厘定(25下:28-30)。这几项原则当然都没有实现,因为宣统三年十月清廷被推翻,民国成立了。梁对预算问题有这么好的认知,但他在1917年任财政总长时,却没有编列预算的作为,或许是因为任职期过短(4个月)而未能一酬壮志。
3.3.3试拟预算
1912年五六月间,梁在日本写了一篇长稿《治标财政策》,分上下篇,析述中国岁出、岁入的诸项内容与经费额度,手法上几乎是在编列、解说中国政府的年度预算,此文到了该年年底才发表(29:51-82)。梁在此文刊布时写了一小段附语,说他的目的是在提出一个大纲,作为他日政府编列预算、整理岁计的基础。这是一篇纲要性的文字,他希望读者不必拘泥于具体的数字,而应在整体精神上体会他的用意。
为何取名《治标财政策》?大概是因为当时已推翻清朝,所以梁积极提出国家的预算大纲供读者讨论:“吾昔常言,处今日中国而言理财,非补苴罅漏所能有功,必须立一根本的大计划焉。……一面估算本年可得之岁入实数几何,当以何法征收之;一面估算本年万不可33)缺之岁出实数几何,当以何法撙节之。……然后中国财政竭蹶之程度若何?……原因安在?乃可得而察也。”这是原则性的宣称,应无人反对。他真正的用意,是针对当时的国务总理:“唐氏绍仪报告本年财政现状,比附前清宣统三年预算案,更任意虚构……而国民亦熟视无睹。……夫我国过去、现在之财政状况,无确实统计可供参考,……以吾研究,则岂惟无所谓岁计不足云尔,实及适得其反,而赢余可至二万万元内外。……固已足以支持危局以待将来之进取焉矣。吾故名之曰治标的财政政策也。”(29:52)
此文分上下篇,上篇论岁出,篇幅较长(29:53-77);下篇论岁入,较短(29:77-82)。梁把重点放在上篇的原因是:“我国财政竭蹶之原因,其缘岁入觳薄而生者不过十之二三,其缘岁出冒滥而生者实居十之七八。”(29:53)梁先析述目前各项岁出入的项目与经费额度,然后批评其中的弊端,之后依自己的见解,来估算合理的项目与额度,最后评比两者在性质上的差异,以及额度上的差距。在岁出方面,梁分中央政费与各省政费两层来解说,但在岁入方面则只有中央级的说明,没有省级的分析。在中央岁出方面,梁分十项析述:(1)中央公署费,(2)外交费,(3)内务费,(4)财务行政费,(5)教育费,(6)国防费,(7)司法费,(8)实业费,(9)交通费,(10)拓殖费。在这十项当中,梁对(1)中央公署费(29:53-58)和(6)国防费(29:61-64)着墨最多,对(5)教育费(29:60-61,共3行)、(8)实业费(29:65,共两行)和(10)拓殖费(29:66,一行半)着墨最少。以下举(1)和(8)为例。
中央公署费需要长篇幅讨论的原因,是由于前清的旧衙门因政体变更,他认为可以废撤者有34处,例如军机处、翰林院、宗人府等等。此外,他也主张裁并海军部,把理藩部裁并内务部,因为梁认为其中的政费浮滥,冗缺冗员过多:“据言庚子以后外务部,其真办事之司员不及十人,余皆伴食耳。而此十人者,每日办事又不过二小时。……外务素称繁部犹且如此,他部可知。”(29:60)他所罗列的各署人员编制和经费预算,到底应各为多少才是合理,其实难有定论,他心中所订的标准是“请比附日本以为标准可乎”(29:55)。
依照这项标准,他拟议的中央公署内,每部所需的员数是76人(从总长到额外司员),经费11.4万元。地大物博的中国,一个中央级部会的编制这么小,未免过俭。依梁的盘算:“总统府费、国务院各部费、国会两院费、审计费、平政院费合计约需六百余万元。今以优待前清皇室费四百万元,实共需一千万元。”(29:58)这样的预算相当有趣:掌管全国主要行政的总统府、国务院等等诸多大型的业务机构,其经费总额竟然只比已无功能的前清皇室优待费多两百万元!梁对此事的本末轻重竟有如此判断,让人意外。在实业费方面,梁只有两行说明:“宣统预算案报农工商部经费一百一十万一千五百九十两有奇。除部员领薪水外,不知所办何事。今除部费外,一时实无他种特别职务可指,暂可全撤,或置十万元为预备费可耳。”(29:65)梁对掌管全国实业(工商)的最高主管机构有这种见解,用这种草率的态度来处理,让人怀疑他对此部的理解有限,读者对这样的预算议案怎么会有信心?此文刊出后,各方的评论颇多,梁写了一篇《军费问题答客难》(30:5-7),辩解其中的“国防费”部分。梁原先的论点是:全国陆军的编制以二十师为适,他也计划把海军部并于陆军:“以上海陆军经费……合计约共需四千二百余万,视宣统预算案约可节省一万四千余万元。”(29:64)当时舆论对此项军费预算的说法有许多评论,梁不得不出面解说。他一方面承认自己“于军事上之智识缺乏殊甚”,但也质疑“现在国中号称军队者六七十师,其足以对外者有几?恐虽军事当局亦无以为对也”。他认为二十师已足够的基本理由是:“夫既名之曰国防费,而其实泰半不足以供国防之用,……斯等于滥费耳。……吾以为今日理财之要义,莫急于节减行政费,综核名实,汰除冒滥,此实死中求活之唯一法门。”(30:6-7)
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梁编制此预算书的基本精神,是往裁撤冗员与节省经费的方向着手;在基本人数与额度方面,又以日本的现行状况为基准。梁的新估算结果相当惊人:“今兹所拟,以较度支部案,所裁过半;现以较资政院案,所裁亦将及半矣。”(29:72)这种所裁过半的预算,一方面反映前清预算编列之浮滥,大笔裁删固然令人痛快;但另一方面也有引人忧惧者:(1)过去根深蒂固之体系,现在虽然有新政权替代,是否能无阻碍地一铲而除?梁对各部、各地、各级行政体系的反弹力量完全未估算到。(2)新兴国家之建设,需另有大刀阔斧之处,今删裁过半,节俭有余,但是否足够开拓必要的新建设?
以上的例子与评论,是针对梁的“中央政费”一节而发。他另有长篇幅解说“各省政费”与“全国岁入”,在手法与精神上大体类似,差异点多是在项目与业务性质方面的解说,在此不拟细述。此处的要点,还是回到梁对国家预算的基本认知:“使吾此文所计算不甚谬,则虽不借一文外债,……用以维持现状,且略从事于进取建设,犹绰绰有余。夫何至举国大惊小怪,坐愁行叹,……绝望如今日耶。”(29:81)这是梁个人的自信,对错与否一试便知。可惜梁在1917年任财政总长时,因任期太短、政治环境恶劣,所以无从判断。
以今日的理解来推断,梁所编列的这份预算书,恐怕有过度乐观与简化事实的倾向。
3.4实际状况
前两节的主要内容,是梁对财政改革和预算制度的诸多批评,以及他所提出的各项改革方案。其实财政收支和预算是相关联的面向(视收入之多少才能做各项支出的预算),所以本节一方面把财政和预算这两个面向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列举清末民初的实际状况(用统计数字来表达),来和梁的改革方案相对比,以显示梁的财政方案与所试拟的预算,有哪些可议之处。
3.4.1岁入岁出
中国真正有现代形式的年度预算,始于宣统三年(1911),这项预算表有岁入与岁出两项,收录在贾士毅(1917:25-31)。这项有用的数据,但不能这么做的原因是:(1)所列举的项目名称不一,有11项岁入名称,但宣统三年的岁入预算只有9项,也无较细分的项目可知其具体内容。(2)相对地,宣统三年的岁出相当详尽。(3)宣统三年的预算表有另一项特色,就是分为“原案”和“修正案”两栏,大概是因为: 第一,此年的政治与经济情势变动甚大,所以需要大幅调整; 第二,资政院对预算有删汰权。以岁入来说,修正后的数额比原案多出400多万元;在岁出方面,修正后要减少8300多万元。若从岁入岁出相抵的角度来看,在原案内岁出超过岁入8400多万元,在修正案内则相反,岁入要比岁出多350多万元。
各国政府的预算会有估计上的误差,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事,但清末民初的情况另有特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收入,并无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划分。各地政府有相当的财政自主性,中央政府从各省所能取得的资源,端视主政者是否足够强势而异。若地方不据实上报,中央就难以掌握可运用的财源;或是上报,但不按时全额缴纳,则中央空编预算也无执行的可能。这项特质是理解诸表的重要前提。
民国元年和民国2、3、5年的岁入岁出预算数据。先看岁入的部分。民国元年时,国内税收中的(1)收益税(23.45%)和(4)消费税(23.81%)占了将近一半(47.26%)。
这两项税源内,分别以田赋和盐税为最大宗。其次是关税(19.13%)、货物税(10.43%)和杂税(9.3%),其余的税源比重较低。民国元年和其他三个年份的岁入有一项大差别:没有国债,原因是此年正值辛亥革命后,在政权交替时外国政府不肯借债是正常的;而新政府尚未底定,没能发行内债也合常理。
相对地,民国2年的国债占岁入比例甚高(40.1%),其中又以外债为主(高达内债的14倍)。原因是新政府刚成立,可借得的内债有限,只好大举外债来挹注。这项国债所占的比例,在民国3年(6.56%)和5年(4.24%)都大幅下跌;另一项特征是外债额锐减,在民国5年时甚至没有这项预算。整体而言,国债在清末民初的几年间,占政府预算的比重大幅起落,不能当作可靠的财源。最可靠的财源还是稳定的老项目:收益税内的田赋和矿税、消费税内的盐税、关税。其余项目则各年起伏甚大,例如印花税、所得税等。
也就是说,愈陈老的税项愈稳,愈新式的税项愈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