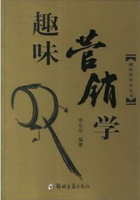(2)外资与中国资本家。梁的基本态度是采取经济民族主义的立场,他所担心的问题是“今后外资之入中国,……其必挟长江大河暴风迅雨之势,取其最新最剧之托辣斯制度,一举而布溢于此旧大陆(中国)。五十年之后,吾恐今日中国所谓资本家者一无存矣,是外资之可怖者二也”(16:89)。这是一种抗拒的心态,梁的替代方案是:“然使中国人而能结合其资本以成大资本也,则固可以抵制外资,勿使输入,……无致有喧宾夺主之患。”(16:88)百年之后读到这种见解,既同其情亦怜其悯:外资的功效不只是资金本身,更重要的随之而来的生产技术、管理方式、企业观念等非资金因素。这个道理在今日已不必费辞,对照之下梁的外资观是较封闭的。
(3)外资与中国地主之关系。外人挟其雄资,“恐将来所谓数十大都会者,当租率未涨以前,而土地所有权已强半入彼族矣。谓余不信,试观今日上海黄浦滩岸,除招商局一段地外,尚有寸土为我国人执业否也”(16:89)。梁所举的例子是事实,但代表性有多少?除了少数重要通商口岸之外,洋人对中国土地的兴趣恐怕有限。一因外资虽雄但非无限,投资于产业才是首要目的;此外尚有多少余力可用来搜括大都会土地,而得到“土地所有权已强半入彼族之手矣”的结果?列强若要占中国土地,其实不必靠外资,用政治手段割据租界既快又大,何必费钱收购?
以上是梁从劳动者、资本家、土地所有权的观点,来说明外资的威胁,我认为说服力甚低。然而梁亦非顽拒外资论者,他知道中国需要一场产业革命,将来才有可能与列强竞争。而中国既缺资金又缺科技,所以必须折中地采取一些可行的方略。梁论此事时文笔冗长,论点拉杂,要言之有下列论点。他最反对所谓的华洋合股制,这是当时通行的方法,梁认为这是掩耳盗铃的最下策:“所谓华商为总办者,不过傀儡,……此其为奸商诡名卖国产以饱私囊之伎俩,至易见也。……故有倡是议者,吾侪竟视为国民公敌焉可也。”(16:94)华洋合股制若成效不佳,恐怕是经济与政治势力强弱之表现,并非主事者所乐见,任公言重矣!
在这些冗长的论述之后,梁提出一项原则性的建议。“故吾欲为一最简单之结论,曰:毋用洋股,宁用洋债;毋用商借,宁用官借[外国社债(公司债)之性质全由商借,官不干涉,其法甚良。今吾语商借毋宁官借,似颇骇人听闻,实则以今日商人程度论之,不得不如此立论,非谓可以概将来也]。而债权与事权之所属,必厘而二之,如是则可以用外资。”落实此项原则的方法有二,一是“由政府以普通之名义,大募一次外债,其对于外国应募者,不必宣言此债之用途何属也;而政府内部自调度之,指定专为兴办某某事业之用”,“其第二法,则指定一事业以借债,而务厘债权与事权而二之。吾与某国之某公司或某私人为借款之交涉,则所交涉者借款而已,其他皆非所得过问。此各国公司借社债之通例也”(16:95)。
以上是梁析论外资在华的简史与性质,中国应如何取得外资,运用外资时应注意的原则。他在这篇长文之后有一段附言,甚可显现他理想的外资观,以及这项观点的根源:“吾意新政府若立,莫如大借一次外债,以充国有之资本而经营各业,纯采国家社会主义之方针,如今德奥诸国所萌芽者。则数十年后,不至大受劳动问题之困,而我之产业制度或驯至为万国表率,未可知耳。”(16:98)他的意思是:
新政府成立后,向外举债兴业,采国家社会主义制,资本与生产工具国有,劳动者的就业权与工资受国家保障,可免除欧美工会罢工之弊。
7.2.2外资利弊
梁另有一短文论《利用外资与消费外资之辨》(1911,27:77-80),评论清末政府在数旬之间,以利用外资为名骤借两亿之款。梁批评此事为消费外资,而非利用外资,盖政府图便利而轻借外资也。
此短文先以一半篇幅,分八点解说中国缺乏资本的原因,另一半篇幅在指责此项借款之用途:虽曰整理币制、推广铁路、振兴实业,而梁举数例质疑所悬之目标难以达成。最后一段的结论在提醒国人,外国资本家逐渐握我生计界之特权,吸我精髓以为其利赢。在此状况下,政府应思所作所为是在如何运用所借的外资,或是有无被所借的外资利用。
此文是时事评论性的短文,基本论点与前文类似,并无特出之新意。梁论外资利弊问题时,正值国力衰败,外资涌入鲸吞蚕食中国各项产业、矿业、商业、铁路之际,在这种情境下,他所列举的原则(毋用洋股宁用洋债、毋用商借宁用官借),以及落实利用外债的办法(债权与事权二分),也有其实际的考虑。这些论点是在特定的时点,从特定角度出发的,可以说是短期的特定外资观。
侯继明(Hou,1965)从较长时期、较宽广的角度,评估1840-1937年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他运用多方面的资料,佐以理论的解说,认为这段时期的外资有助于中国经济趋向现代化。原因之一是外资的投资利得,大都再转投资于中国,并未产生“利润汇出的吸血效果”;原因之二,外资带动产业发展,中国企业也因而兴起,在生产技术与管理知识上也有明显的进步。此外,在国家经济所占的比例上,传统的经济形态仍占绝对优势;外资在基本产业上所占的比例不高,出口也未呈现不均衡的发展。其中有一项重要因素:中国并非列强的殖民地,尚有相当自主权,外人的经济活动以通商口岸为主,在内地的活动须受政府限制,尤以采矿条件最为明显。若以列强入侵的观点来看外资在华的活动,而忽略外资对华经济的实质贡献,则易失之偏颇。此书广为学界所知,论点甚辩,虽非定论,但甚能对照梁从政治角度所作的民族主义外资观。
侯继明认为外资对中国的实质帮助有两项,可以用来和梁的外资观对照。(1)模拟效果:外资给中国引入了有利的投资诱因(例如开发新矿场、筑铁路),同时也传入了新技术和新观念,开阔华人的眼识。(2)连锁效果:因贸易、筑路、开矿而牵动的相关行业也随之而兴,此种连锁反应对经济、社会、文化所带来的不可见价值,远大于纯经济利润所得。
在华的外资企业有下列优势:融资易,资本足,技术强,管理能力较高,享有最惠国待遇的优惠条件,不受官方苛扰。但为何华资企业缺乏上述的优势、效率低下但却还能与外资企业并存?主要的原因有:(1)除了矿业与铁路外,外资企业大都只能在通商口岸设厂经营,限制了外资的发展空间。(2)民间排外性强,时常发起抵制外货运动,各行业的竞争者也常以此手段打击外资企业;此外,在争取劳动力时,也常运用排外心理战术。(3)外资企业产品的流通大多限于沿海,广大的内陆市场因消费习惯不同、购买力不足等因素,外资产品不易广泛地深入传统部门。
此外,较具竞争性的行业(如矿业、航业)常互订协约,划分市场以减少因竞争而产生的损失,造成外资企业与传统行业在市场区隔上有二分化的现象:外资企业以沿海地区、高级品为主,传统市场以中低级品和广大的内陆市场为主。华资企业虽然在能力上与优势上较弱,但在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文化和社会力量的支撑下,仍可和外资企业对峙。此外,本国企业也从外资企业学习到新的技术与观念,未必因受到明显的压迫或损失,反而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学习效果”。
在责备列强经济侵略之余,亦应检讨何以华籍企业不易强大。
(1)资本累积困难:国民所得低,财富阶级的储蓄多用在非生产性的土地购买等事物。所得低,储蓄少,教育不普及,生产力低,造成一系列的恶性循环。(2)传统的社会重农轻商,非农业部门(如贸易、工、矿等)的比例太轻,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无长子继承制(日本得长子继承制之利不少),政府主掌大企业,官僚腐败,宿命论与顺受的民族性强,重人文而少科学研究,对家族依赖太深,劳工低廉,以致泥习于传统生产方式。(3)清末国库困难,有心无力,政府中缺乏有力领导者,行政效率低且保守自封;林则徐、李鸿章等人虽欲振奋,但已属强弩之末。清末衰弱非一日之寒,列强入侵虽为国耻,但若无此刺激与引发,中国经济亦不易突破自闭之境。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与其他落后国家不同。外贸占国民所得的比例甚小,最高时也只占12%,显示对外依存度甚低。1867年时,鸦片和纺织品就占了进口总额的77%,1842年时茶叶占出口总额的92%。到了20世纪,中国除了茶叶外(茶叶对国内经济并不很重要),没有单项产品占出口总额的10%以上,可见项目很分散。而其他落后国家的某些单项产品,都占出口总额的50%以上,所以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国家的经济背景很不相同:没有出口集中的现象。在华的外资只有少部分用在出口业,大部分都投资在铁路、矿业方面,很少投入在丝、农等传统产品上。因为对外依存度低,国际行情的波动并不会明显影响中国经济。总而言之,侯继明认为外资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可以从下列的角度重新思考:
(1)中国尚有完整自主权,外商仅在通商口岸及租界有自由经营权,内陆矿业、航业仍受严格限制,传统部门和广大的内陆市场并未受到外资破坏,反而受利不少。
(2)以每人分得的外资额计算,在1936年时少于8美元,比率太小,对国民所得影响不大,这和其他落后国家完全不同。
(3)列强真正的投资额并不高,主要都是由盈余再转投资,也没有因为把投资利润汇回本国,而造成中国经济枯竭的现象,这和其他落后国家不同。此外,中国可耕地区的人口稠密,文化社会根深蒂固,并不是列强有兴趣大量投资的新殖民区。虽然各国贷给中国政府的款额不少,但多用为军费和赔款,直接用来投资经济部门的比例有限。
(4)根深的文化、社会习俗、消费偏好,使得外来消费品的被接纳性低;再加上国民购买力弱,在通商口岸的各国新设制造业利润并不理想,此外也有坚强的传统部门在和外资企业竞争。再说,中国政府的管制严格,所以外资企业虽挟其雄资、技术、政治特权,但获利有限,影响中国国民经济的幅度不大。
(5)外资占国民所得的比例虽少,但触发导引中国经济现代化之功却不可没,尤其在观念、技术、经营管理上更是开启华人的眼界,也因而促使中国政府决心现代化。政府的努力虽然成效不彰,但也起了领导作用,创造了较有利的投资环境。
(6)引进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能互相提供技术、机器、原料、劳工,各占市场,相互得利,现代部门破坏传统部门之说不一定能成立。
(7)中国对外依存度甚低,自主性甚高,这和其他落后国家甚受殖民国影响的状况不同。此外,Singer-Prebisch-Myrdal的“吸光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外资对华的全盘性影响很难统计算出,单就经济层面来说,侯继明(1965)的结论认为:外资对华经济的现代化确实甚有贡献,提供了资金、技术、经营制度,不但没有摧毁传统部门反而贡献良多;虽然难免损及某些传统行业,使国人在心理上有被侵略的感受,也因而容易情绪地认为外资有害中国经济,这种观点会忽略了它们所提供的实质利益。
外资从清末开始进入中国,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冲击与影响。这些复杂的事项无法在此逐一评述,若对这些问题有兴趣深入了解,可参阅曹均伟《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1991)。
他在此书的前四章,说明如何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外资对华的影响,解说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有哪些特征、形式和性质,以及近代对利用外资有过哪些不同的见解。他列举李鸿章、刘铭传、张之洞、盛宣怀、梁启超、张謇、孙中山等人的见解,一方面提供了清末外资思潮的主要资料,另一方面也整理出这些见解在脉络上的异同。此外,雷默(Remer,1933)一本700多页的翔实调查报告,对研究各国在华的诸项投资业务与作为,至今仍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外资是清末民初经济的重要议题,学界已有许多深入的研究,在此只能就梁的论点提出对照性的解说。
7.3生计博议
梁有以下文字论及国民生计问题:《论生利分利》(1902,4:80-96)、《莅北京公民会八旗生计会联合欢迎会演辞》(1912,29:30-32)、《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1913,29:109-119)。这三篇的题材之间并无关联性,主题的重要性并不高,可以申论的空间也有限,以下综述他的论点并稍加评论。
《新民说》(1902)这本小册子是梁的名作之一,其中第14节《论生利分利》(专集4:80-96)所用的主要观念,是依亚当·斯密的说法,把中国人口分为“生利者”和“分利者”两大类。严复译的《原富》在1902年出版时,梁正在写《新民说》。他读到斯密析论生产性(productive)与非生产性(unproductive)的劳动,认为这是个有趣的说法,就尝试把这个概念用到中国的人口结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