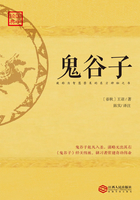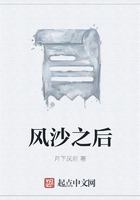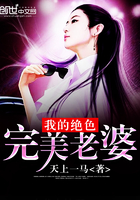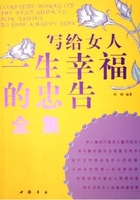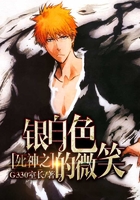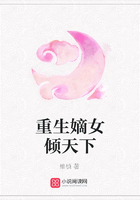关于儒家的思想,在第二讲中已讲过,不过关于儒家的哲学,很少谈及。在第二讲所讲的,只是儒家的伦理学,并不是儒家的哲学。《论语》
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在《论语》里面,谈性与天道,确实是很少的。还有关于生死的问题,鬼神的问题,《论语》上也很少提起。季路问事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关于生死鬼神,孔子都不愿发表什么议论。但是所谓性与天道的问题,生死鬼神的问题,都是哲学上的中心问题。如果把这些问题抛开,岂不是儒家本身根本没有所谓哲学么?作为维护封建统治最有力的儒家思想,如果没有哲学做它的基础,没有系统的世界观做它后面的台柱,那么,儒家思想的支配力,一定不容易维持很长久的寿命。于是《中庸》一书,在这时成为最需要的产物。《中庸》便是供给这种哲学的基础的,《中庸》便是建立这种系统的世界观的。所以《中庸》所着重的问题,是性与天道,而于鬼神的问题,也有谈及。
因此,关于《中庸》这部书,颇引起许多议论。有的说是道家的作品,因为里面所讲的体与用的关系,和道家的思想有许多相通的地方。道家想散播思想种子到儒家里面去,所以有《中庸》之作。又有的说是儒家的作品,认里面的思想虽有许多是取自道家,而其根本立场却仍是儒家。
又有的说是孟子一派的儒者所作,因为里面讲性命诚明,都像是根据孟子的学说而发挥的。我以为这几说中,以第二、第三两说为近是。不过讲到这里,就要讨论到《中庸》的出生问题。我现在先作这样一个假定,然后说明这假定的根据。便是《中庸》一书,我认为是秦、汉统一后的产物。
秦、汉统一以后,儒、道两家的思想,争取思想界的支配权。道家思想内容充实,但不为统治阶级所欢迎;儒家思想内容平泛,但统治阶级争相利用。就这两种情形说,儒家之取得最后胜利,乃是意计中事。道家思想是在战国之末才发展的,在第四讲中已有谈及。到了秦、汉统一之后,以其方兴之势,与儒家周旋,固未为不可,无如儒家有统治阶级做护符,当然不能不让儒家操最后的左券。因此《中庸》之作,可以成为有意义且有权威的作品。《中庸》里面讲体用关系颇精,不能说没有道家的影响;而其讲性命诚明诸点,也确实是从孟子学说中推衍而来的。所以我说上面的第二、第三两说,较近事实。至于《中庸》所以为秦、汉统一以后的书,更有一点为一般人所引证,便是书中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句。这在秦、汉统一以前是不能有这种现象的。
讲到这里,就要讨论到《中庸》和《孟子》先后的问题。一般人认《中庸》在《孟子》之先,因为肯定《中庸》为子思所作,已早成为思想界的定论,当然认《中庸》是在《孟子》之前了。可是自从崔东壁一声喝破以后,这两书的前后就发生问题了。关于这点,另开一段说明。
一、《中庸》和《孟子》二书的关系
崔东壁在《洙泗考信录》上说:
世传《戴记中庸》篇为子思所作。余按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于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于《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名言多矣,孟子何以独述此语?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日”,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其可疑三也。
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盖子思以后,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托之于子思,或传之久而误以为子思也……嗟夫!《中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语之文,采之《中庸》。少究心于文议,显然而易见也。
崔东壁从两书内容及文体与乎孟子平昔所称述之处,证明《中庸》在《孟子》后,并坚决地断定“《中庸》之文,采之《孟子》”,不可谓非有断有识。他并在《孟子事实录》里面叙述《孟子·居下章》为《中庸》的张本,说道:
《孟子》此章,原言诚能动人,故由获上、信友、悦亲、递近而归本于诚身,然后以至诚未有不动总结之,又以不诚之动反结之,首尾呼应,章法甚明。《中庸》采此章文,但欲归本于诚身,以开下文不思不勉、择善固执之意。意不在于动人,故删其后两句,然则是《中庸》袭《孟子》,非《孟子》袭《中庸》,明矣。
东壁认《孟子》重“诚能动人”,《中庸》“但欲归本于诚身”,“意不在于动人”,可谓独具识解。自东壁以后,《中庸》与《孟子》之传统的看法,渐渐成为问题;到现在,固群认《中庸》之后于《孟子》了。不过关于《中庸》与《孟子》的关系,都未能说得明白。东壁也只能看到《孟子》重动人,《中庸》不重动人,但何以《孟子》能动人,《中庸》不重动人,就未能说明了。关于这点,我以为应先审明《孟子》和《中庸》两书的根本不同之点。《孟子》和《中庸》同为儒家重要文献,可是《孟子》着重在伦理学,《中庸》便着重在形上学。前者以伦理观、人生观为主题,后者以世界观、宇宙观为主题。《孟子》书中虽然也有不少的形上学的思想,可是比之《中庸》,便相差远了。《孟子》书中常常提到诚身明善的道理,譬如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又如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又如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关于反己诚身的议论,在《孟子》书中随处皆是。所以孟子在《居下章》下了这么一个结论: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注重反己诚身,以为至诚可以动人,不诚便不能动人,单就个人的修养方面说话,可以知道完全是伦理学的观点。他认“人之道”为“思诚”,“思诚”即由于个人心志上的努力。如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又如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欲仁”、“志于仁”和“思诚”是一样的态度,都是着重在“心之所之”。孟子是唯心论的大师,而对于心志上的努力,比别人提倡得起劲,所以特别着重“思诚”。还有一点,也是孟子着重“思诚”的意思,便是“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的“思诚”和孔子的“欲仁”、“志于仁”,都可当作唯心论的伦理学者的动机说看,若《中庸》的态度便不同了。《中庸》是想在“诚”字上面,建立一种诚的宇宙观,它把宇宙的本质看作“诚”,因此,由这宇宙本质的发展,便看作“诚之”。一个是体,一个是用。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体能生用,即用显体,因此说: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诚之”固为人之道,但不限于人类,不过在人类当更努力尽“诚之”之道而已。“诚”与“物”是息息相关的。“诚”是“本体”,“物”是“现象”。本体发为现象,现象必依本体。所以说: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诚之为贵”,这个“诚之”和《孟子》的“思诚”不同。“诚之”关系到“物之终始”。包括人与物而言。所以《中庸》继续地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这完全是一种形上学的态度。若《孟子》的“思诚”,着重在心志上的努力,着重在动人不动人,专言人与人的关系,便完全是一种伦理学的态度了。《中庸》拿住《孟子》的“诚”,尽力发挥形上学的意义,以建立一种系统的世界观。由以上的说明,便不难了然。
《中庸》一书,着重在宇宙与人生的关系的说明。开首一段,便提出全书的纲领,都是关系到宇宙与人的。其后用诚明说明性教之不同,更申明“至诚尽性”、“至诚如神”、“至诚无息”之旨,对于宇宙与人生的关系,层层紧逼,而皆以“诚”之一字做中心,足见这书为一种有组织有主张的著作。《中庸》认“诚”充满在天地问,却全靠人生去表现出来,表现得最圆满的,就要和“诚”合而为一了,这是一种最高的境界。所以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如果“诚之”的功夫做得十分充实,那就可以联宇宙与人生而为一,更分不出哪个是宇宙,哪个是人生了。到了那种境地,就可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了。这便是《中庸》所谓“与天地参”。“与天地参”的思想,不是很显明的一种形上学的思想么?像这种形上学的思想,在《孟子》里面是很少的。《孟子》是以谈性最著名的。《孟子》谈性,只谈“人之性”,既不是“犬之性”,也不是“牛之性”,若《中庸》谈性,则并犬马牛羊,人类物类而一切赅括之,所以日:“天命之谓性。”我们拿《中庸》和《孟子》相比较,处处可以见到《中庸》在《孟子》之后,而是以形上学的建立为其主题的。
二、《中庸》的基础理论
《中庸》的基础理论,我们可以分作两项说明:第一,论诚,即是论道。第二,论中与和。但第一与第二却是一贯的。先说明第一项。
《中庸》开宗明义第一章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这是全书的主旨。把体用的道理、天人的思想,都包括净尽。什么叫“天命”?我以为“天命”即自然所命,与《老子》中“莫之命而常自然”的意思相仿佛。所谓“天命之谓性”,即无异于说出于自然所命即谓之性。
性和教是不同的。教是人力加于自然的,性是自然施于人身的。要说明性和教的不同,必须考察下面的话: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诚”是“诚”,“明”是“诚之”。“诚”是“天之道”,“明”是“人之道”。“自诚明”即是由天而人,由自然而施及于人事,故谓之“性”,亦即所谓“天命之谓性”。“自明诚”,乃由人而天,由人力加于自然,故谓之“教”,亦即所谓“修道之谓教”。以上是说明“性”和“教”的两方面。至讲到“道”,“道”是介乎二者之间的。属于“性”的方面的,为“天之道”;属于“教”的方面的,为“人之道”。“道”有轨道、法则、过程的意思。天有天的法则,人有人的法则,宇宙有宇宙的法则,人生有人生的法则。法则是随自然界而建立的,“道”是因“诚”而建立的。没有自然界也就没有法则,没有“诚”也就没有“道”。所以说“率性之谓道”。这又与《老子》中“道法自然”的思想相仿佛。“诚”与“道”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有“诚”便有“道”。不过“诚”为“天之道”,“诚之”为“人之道”而已。《老子》把“自然”看作本体,把“道”看作法则;《中庸》便把“诚”看作本体,把“道”看作法则。一个拿“自然”做中心,一个拿“诚”做中心,这是两家的分界线。
“诚”与“道”虽是二而一的,却又是一而二的。“诚”是自己具有“诚”的本质的,不假借于他物,而为一切物的基体。“道”是自己具有一种法则的,无论物的大小长短,都有各种大小长短的法则。所以《中庸》说:
诚者自诚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不过“诚”与“道”毕竟是二而一的。“诚”无论其“成己”“成物”,总是一种“合内外之道”。我们将“诚”与“道”的关系及“诚”与“诚之”的关系列为一表说明,则如次式:
诚——自诚明——性——天之道
诚之——自明诚——教——人之道
《中庸》所谓“诚者自诚,而道自道”,已显明地告诉我们“诚”与“道”是有密切联系的,我们由上表的说明,更可以了然于“诚”与“道”之是二而实一。既已把“诚”与“道”,和“诚”与“诚之”的关系说明了,现在可以提出两个要点来说。
第一、至诚
《中庸》一书,是拿住“诚”做中心观念的。它认为人的本性是“诚”,万物的本性亦是“诚”,推而至于宇宙全体,亦无往而非“诚”。
所谓“至诚”,乃尽力表现所本有的“诚”,如果尽力表现所本有的“诚”,便没有不能推动其他事物之理。所以孟子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表现所本有的“诚”,是谓“尽性”。因为这是“自诚明”的道理。孟子说:“尧、舜性之也。汤、武反之也。”尧、舜性之,即是尽性;汤、武反之,即是反身而诚。前者是表现所本有的“诚”,后者是用了一番工夫才达到“诚”。表现自己所本有的“诚”,也能表现其他事物所本有的“诚”,因为“诚”是一体的。所以能尽己之性,亦能尽人之性,亦能尽物之性。《中庸》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孟子所谓“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单就“动人”说,若《中庸》贝4推扩到物,推扩到宇宙全体。所以认表现一己所本有的“诚”,结果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以上是说明至诚尽性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