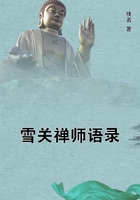一、百灵场
那次谋害案发生时,马吕斯曾把沙威引向现场,并且目睹了那案件的出人意料的结局。当时,马吕斯趁沙威把那些被捕者押上三辆马车的工夫,也悄悄离开了那里。马吕斯去了古费拉克的住处,对古费拉克说:“我在你这儿过夜。”
第二天一大早,7点钟,马吕斯就回到了他的住处。他向布贡妈付清了房租,并叫人搬走了所有的家当。当沙威早晨再次到破房子来找马吕斯时,他已经无影无踪。布贡妈只向沙威说了声:“搬走了。”马吕斯没有给布贡妈留下新的地址。
马吕斯匆忙搬走,有两个原因:其一,他在那所房子里目睹了社会上的一种丑恶现象,他对那里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其二,他不愿意牵涉进这桩案子,否则,跟着来的必然是在控诉揭发唐纳德的材料上签名画押。
对马吕斯的失踪,沙威做了这样的推断:这个年轻人由于害怕躲起来了。他曾多方查找,但终无所获。
马吕斯从一个经常在法院接待室工作的实习律师那里打听到,唐纳德入了监狱。这样,每星期一,他总是送5个法郎到监狱管理处,托人把钱转给唐纳德。
马吕斯没有钱。他向古费拉克借了五个法郎。这是马吕斯第一次向人借钱。古费拉克常想:“这钱是给谁的呢?”唐纳德也常在问自己:“这钱是哪里来的呢?”马吕斯心中苦闷异常。他始终抱有再次与他心爱的人相见的希望,与此同时,又被断定无望的绝望所折磨。
最为不幸的是,贫困再次向他袭来。在那些苦恼的、不短的日子里,他已经中断了原来的工作,而工作的中断正是危险不过的事。
现在,马吕斯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自认她是爱他的。他认定,她的眼睛已经表达了她的心事。他认定,她不认识他,却了解他的心。他想,现在,她无论在什么神秘的地方,她仍在爱着他。谁能说不是这样呢?兴许是那样,她在想念他,正如他在想念她。
在那令人煎熬的漫漫长夜,他时断时续,把对她的思念一股脑地写在一叠白纸上。那是爱情的倾注,是最纯洁、最空泛、最超绝的心动的史册。他把它称之为“和她的通信”。
总之,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始终没有发现实现希望的任何新的线索。他只有一种感觉剩了下来。
“怎么,”他常这样想,“难道在这之前,我就不能再见她一面了?”
有一次,马吕斯一个人闲逛,无意中走到了这地方的一个小池边。这一天,十分难得,正巧有一个过路人。马吕斯便问那过路人:“这地方叫什么名字?”
过路人回答:“百灵场。”马吕斯对“百灵”感兴趣。他正处于神魂颠倒的状态之中。现时的他,“玉絮儿”已经被“百灵鸟”所替代。这“百灵”二字一入耳,便不顾一切了。顿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荒唐的推理,既然这里是“百灵鸟之场”,那么,他的百灵鸟一定会在这里出现了。
从此之后,他便天天去这百灵场。
二、狱中的罪恶
那个时候,爱潘妮在路边大树下把风,巴纳斯山碰见她之后,将她带走。他宁愿去跟姑娘调情,也不愿向老头儿这里来找油水。如此,他逃脱法网。沙威派人把爱潘妮“钉”住了,巴纳斯山逃了,但抓住了爱潘妮。爱潘妮和阿兹玛一道,都进了玛德栾内特监狱。
在从戈尔博老屋押往拉弗尔斯监狱的路上,那主犯中的一个,铁牙,不见了。谁都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警察们感到莫名其妙。到达监狱时,发现马车开裂,无疑,他从缝隙中溜掉了。铁牙渺无影踪了。对此,沙威焦急胜于惊讶。
至于那个“傻小子、怕事的律师”马吕斯,沙威并不在意,甚至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了。
审讯开始。裁判官觉得,在猫老板这伙匪帮中,放一个人不坐牢,是有好处的,那就是希望能从他那里打探到一点口风。这人便是普吕戎,也就是小银行家街上那个留长头发的家伙。他们把他安置在了查理大帝院内。不用说,狱卒们的眼睛时刻都在注视着他。
普吕戎这个名字,对拉弗尔斯监狱来说并不是陌生的。这座监狱里有一个丑恶不堪的叫“新大楼”的院落,行政上称它为“圣贝尔纳院”,罪犯们则称它为“狮子沟”。这院子有一道被锈蚀了的铁门,通向原拉弗尔斯公爵府的礼拜堂。院子的左边有一堵石墙。这石墙是由鳞片状和扁平的条石砌成的,从地面到屋顶,布满了苔藓。12年前,这墙上还有一种堡垒的图形,是用铁钉胡乱划成的。在这图形的下方,签有这样几个字:
普吕戎,1811年。
1811年的普吕戎,就是1832年的这小普吕戎的父亲。
这小普吕戎,我们在戈尔博老屋谋害案里只是随便望了一眼。他表面上憨气十足、愁眉苦脸,但异常狡猾、异常能干。身子也壮。正由于看到了他这种憨劲,裁判官才放了他;认为把他安置在查理大帝院内比关进隔离牢房里会更有用些。
不管牢里的管制如何严厉,囚犯们总有办法相互联系,继续策划犯罪活动。也真是,因犯罪坐牢却不因坐牢而不犯罪。
从外表看,普吕戎已被监牢关傻了。
但是,到了1832年2月的下旬,人们忽然发现普吕戎这瞌睡虫活了起来。他串通了狱里的几个杂工,而以3个伙伴的名义,一连办了三件不同的事,总共花了50个苏。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自然引起了监狱警务班长的警觉。
一件事是在先贤祠办的,花费10个苏;另一件事是在军医学院办的,花费15个苏;第三件事是在格勒内尔便门办的,花费25个苏。计费表上标明,最末一件事,花费的数额最高。同时查明,这三个地方——先贤祠、军医学院和格勒内尔又正是三个相当凶恶的便门贼的窝点,他们分别是克吕伊丹涅——别名皮查罗,另一个叫光荣,一个获释的苦役犯,还有一个叫拦车汉。普吕戎向他们发了信,但信不是按地址送达的,而是交给某个在街上等候的人。警察认为,这里面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于是,凭这些蛛丝马迹,将三人逮捕,企图以此挫败普吕戎的阴谋。
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狱卒发现普吕戎正在床上蜷曲着身子借着微弱的烛光写着什么。普吕戎被“隔离”起来,但他写的东西却没有找到。这样,警方便没有掌握别的情况。
但有一事确切无疑:次日,一个“邮车夫”飞过查理大帝院子,越过六层大楼,落在了大楼另一面的狮子沟。
这“邮车夫”,是囚犯们的行话:一个用艺术手法制成、送到“爱尔兰”的面包团。所谓送到爱尔兰,是指越过牢房的房顶,从一个院子抛到另一个院子。拾起这面包团的人,剖开它,便可以找到一张写给那院子里某囚犯的字条。捡到这字条的,假使是个囚犯,便会把它转给收件人;假使是个守卫,或者是个被狱官收买的囚犯——监狱称之为绵羊的,苦役牢中称之为狐狸的——那字条便会交给管理处,然后到达警察之手。此次,那“邮车夫”被送达了目的地,尽管收件人当时正被“隔离”。那收件人正是猫老板四巨头之一的巴伯。
那“邮车夫”的纸条上只有两行字:“巴伯,卜吕梅街有笔生意好做。一道铁栏门,面对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