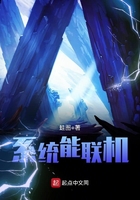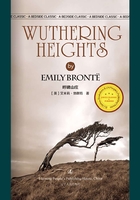这时,有几位先生在两排牲口中慢慢走着,细细观察每头牲畜,然后低声交谈。其中一位看上去更受人尊敬,边走边在小本本上记录。他就是评审团主席德洛泽莱先生,潘维尔人。他看见罗多尔夫就疾步上前,带着友善的微笑对他说:
“布朗瑞先生,您怎么把我们丢下不管呢?”罗多尔夫说他立刻就过去。可是主席一走远,他就说:
“老实说,我才不会去呢,只愿意陪着您。”罗多尔夫虽说对农促会不感兴趣,他还是向纠察亮出了他的蓝牌牌,以便放行,有时停留在一件漂亮的展品前,包法利夫人也兴趣索然。他发现后就拿永镇的女人们来开玩笑,讥笑她们的梳扮。然后他赶快又对自己的装束随便表示歉意。他的衣着既土气又讲究,颇不协调,摆出一副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派头。例如,他的袖口打褶的细麻布衬衣,在马甲开口的地方被风吹得鼓了起来,马甲是人字斜纹布做的;而他的宽条纹长裤在脚踝部露出米黄色南京土布靴,上面镶着几块漆皮。靴子擦得油光锃亮。他穿着靴子踩在马粪上,一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头上草帽歪戴着。“其实,”他加了一句,“人如果住在乡下……”
“衣着上再讲究也没用。”爱玛说。“对极了!”罗多尔夫加以肯定,“不说别的,这些乡下人恐怕都不清楚大礼服的款式!”随后他们谈起外省的落后、生活的窒息和理想的泯灭。
“所以,”罗多尔夫说,“我感到极端苦闷。”
“您!”她诧异地说,“我还以为您过得很快乐呢,是不?”
“啊!那是表象,因为我在世人面前戴着副笑傲人生的假面。望着月光下那一片墓地,我在想跟那些人一起长眠地下是不是更好一些……”
“哦!您还有朋友,”她说,“您为什么不想想他们?”
“我有朋友?谁是我的朋友?我有称得上朋友的人吗?谁关心我的死活?”后面走来一个人,扛着一大堆似脚手架般的椅子,把他们挤到了两边。他扛得实在是太多了,多得只露出一双木屐头,一双笔直张开的手臂只能看到那点手指尖。他是莱斯梯布多瓦,他把教堂里的椅子大批大批地往外搬。他挖空心思挣钱,又想出了这种利用农促会赚钱的办法。的确,镇民们热了,就争椅子坐,椅垫子里的干草带着香烛气息,他们靠着鼓鼓的椅子背,上面还沾着蜡烛油,坐在这样的椅子上,不免产生虔诚之心。包法利夫人重新挽起罗多尔夫的胳膊,他继续往下说,像是自言自语:“是啊!我曾错过那么多机会!到现在还是单身!唉!如果我的生活能找到一个目标,找到一个我所钟爱的女人……啊!我会竭尽我的全力,克服万难,突破一切障碍去赢得幸福!”
“我认为,”爱玛说,“您没必要顾影自怜。”
“啊!您真的这么认为?”罗多尔夫问道。“因为,您……”她又说,“您毕竟是自由的。”她迟疑了一下,接着说:
“而且富有。”
“您别挖苦我。”他答道。
于是,爱玛发誓说她绝非挖苦他,这时突然听到大炮轰鸣,人群立刻乱纷纷地朝镇里涌去。
可是这一炮是虚放的,省长先生还没有到;评审团的成员们颇为尴尬,不知该马上开会,还是再等下去。终于,广场边上出现了一辆双篷四轮出租马车,戴白帽的马夫正猛地抽打两匹瘦马。比奈急忙高喊:“持枪!”自卫队队长跟着也叫了一声。队员们急忙跑去抓枪支,有的人竟忘了戴上假领。然而,省长似乎有意为他们留出时间整队,并驾两匹驽马晃动着马辔小链,姗姗来到镇政府列柱前,这时,国民自卫军和消防队刚好击鼓踏步,在那里摆开阵势。“原地踏步!”比奈喊道。“立定!”自卫队长喊道,“向右看齐!”接着是持枪,响起了一阵就像小铜锅滚下楼梯的声音。这时,他们看到马车上走下来一位先生,身穿银绣短礼服,光头,只有后脑勺上还有一小绺头发,脸色灰白,相貌慈祥。他那双眼睛很大,厚厚的上眼皮往下垂,眯起双眼扫视四下的人们,同时扬起他那尖鼻子,瘪嘴上挂着微笑。他从三角肩带上认出了镇长,就告诉他省长不能来了。他本人是省议员,说着表示了一番歉意。蒂伐什则客客气气地应答着,议员也很谦虚。他俩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两颗脑瓜都快碰到一起了,身边围满了评审团的成员们,以及镇议会显要人物,国民自卫军和群众。议员先生把他黑色的小三角帽紧紧抱在胸前,频频致意,蒂伐什则点头哈腰,也堆满笑容,他结结巴巴寻找措词,口口声声效忠王室,感谢诸位给永镇赏脸。
客栈伙计希波利特上前从车夫手里接过两匹马的马缰,跛着脚把它们牵到金狮客栈的门廊下,许多乡下人围观那辆四轮马车。鼓声擂动,礼炮轰鸣,先生们鱼贯登台就座,坐在向蒂伐什太太借来的大红绒布软椅上。这些人好像都是同一个模样。金黄色松软的脸,被太阳晒得稍稍有点黝黑,像甜苹果酒的颜色,蓬蓬松松的颊髯压在又大又硬的领子上,都系着白色的领带,打一朵大领花;马甲全都是丝绒的,交叉式的;怀表上都有一条长丝带,丝带坠着一个椭圆形的光玉图章;两只手都放在双腿上,裤子的呢料还是新的,磨得闪闪发光。
上流社会的夫人们坐在后面列柱间的前厅里,老百姓则对着主席台,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椅子上。莱斯梯布多瓦真的把椅子从草场上全都搬来了,他还在奔忙,不时在教堂里寻找,他这笔生意经几乎导致会场水泄不通,想走到主席台边的小台阶都不容易。
“依我看,”乐乐先生对正经过身边上去就座的药房老板说,“真该在那里竖两根威尼斯旗杆,挂上既大方又华丽的饰物,那才吸引人呢。”
“没错,”郝梅答道,“可你有什么办法呀!一切都由镇长作主。这可怜的蒂伐什没情调,他根本就没有半点艺术鉴赏力。”
这时,罗多尔夫和包法利夫人已经来到镇政府二楼的会议室。里面空无一人,他说在这里能舒舒服服地观看整个会场的情况。他从国王的半身像下、椭圆形会议桌边搬来三张凳子,放在窗户边,他们并排坐下。
主席台上一阵骚动,经好一会儿低语协商,最后参议先生站起身来。大家现在知道了他叫柳文,这个一阵风似地在群众中传开去。他拿起几页讲稿,检查一下页码,凑到眼前,开始发表讲话:
先生们:
在这次盛会的开始,请允许我向最高政府、内阁、君主,我们这位敬爱的国王表示,我相信也是我们共有的敬意。我们的君王,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国家的繁荣。他英明果断地引导着国家这条航船航行在汹涌的大海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他同骁勇善战一样,善知利用和平,重视工业、商业、农业和艺术。
“我得往后挪一点。”罗多尔夫说。“为什么?”爱玛问道。这时,参议提高了嗓门,语调夸张地说:
先生们:
那种内战频繁,妖言邪说,人民担惊受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下面的人可能会看见我,到那时我花上半个月时间也解释不清楚了,因为我的名声很不好……”
“哦!您何苦糟蹋自己。”爱玛说。“不,不,是真的,我这个人太坏啦。”省参议接着说:
放眼于当今祖国的美好形象吧。我们看到了什么?到处是商业昌盛、艺术繁华;到处是新辟的交通线,像是在国家机体里新增的血管,在那里建起新的联系。我们的制造业大中心一个个恢复了活力。宗教信仰更加坚定,我们的微笑发自内心的深处。我们的港口樯桅如林。我们又有了信心,法兰西终于得到了新生!……“而且,”罗多尔夫补充道,“从世俗观点来看,也许,人们是对的。”
“怎么会是这样呢?”爱玛问。“还能怎样!”他说,“您难道不知道有些人的心灵时时在痛苦中挣扎吗?他们时而需要梦想,时而又需要行动,时而渴望最纯洁的感情,时而又追求最疯狂的享受,这种人总是沉溺在白日梦和荒唐中。”
爱玛不禁望了他一眼,像看到了外星人一样,她说:“我们这些可怜的女人,就连这种消遣也得不到啊!”
“可怜巴巴的消遣,是没有幸福可言的。”“可幸福能找得到吗?”她问道。“找得到,您总会遇上它。”他答道。省参议在说:
平的开拓者!你们,人类进步和道德的卫士!我知道,你们已经明白,政治风暴的确比自然风暴更加可怕……“您总会遇上它的,”罗多尔夫又说了一遍,“有一天,就在您陷入绝望的时候,突然,天边绽放光明,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幸福在这里!’您感到需要向这个人倾诉衷肠,把一切都献给他!两人一见如故,即使不交谈,也能心领神会(说着,他凝望着她)。他终于来到面前,这梦寐以求的幸福,他在这儿,在您面前,光芒四射,竟让您心存疑虑,一时不敢相信。您像刚从黑暗中走向阳光,感到眼花缭乱。”
说这话时,他用手挡住眼睛,仿佛一个头昏眼花的人,然后把手放下来,落到爱玛的手上。爱玛把手抽出来,而省参议则仍在念讲稿:
那么,先生们,谁会对此感到奇怪呢?只有瞎子,总也摆脱不了那个时代(我坦白地说),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偏见,才会继续否认农民的聪明才智。的确,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比农村里更多的爱国精神,对公众事业的耿耿忠心,以及更多的智慧呢?先生们,我所说的,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智慧,无所用心的头脑的无所用处的装饰,而是那种更加深邃和稳重的智慧,它首先致力于追求有用的目标,从而有助于增进每个人的利益,改善大众的生活,支持各级政体,这是尊重法律和尽义务的结果……“哈!又是这话,”罗多尔夫说,“老是义务,这种词让我都听腻了。这群穿法兰绒马甲的老朽,带着脚炉念珠的虔公,不停地在我们耳边念叨‘义务!义务!’可见鬼!什么是义务!义务是向往伟大、美好事物的自觉行动,而不是接受社会的旧习俗强加给我们的耻辱。”
“可是……可是……”包法利夫人想反驳。“不对!为什么要说自己反对爱情?难道它不是人世间惟一美好的东西?它不正是勇气、热情、诗歌、音乐、艺术的源泉吧?”
“那也应该尊重一些社会公德,”爱玛道。“啊!道德还有两种呢,”罗多尔夫辩驳,“一种是约定俗成的,众生相的道德,它不断地改变,对世事乱加指责。另一种是永恒不朽的道德,它就像蓝天、大地一样包容着我们。”
柳文先生掏出手绢擦了擦嘴,又讲下去:
先生们,农业的用处还需要我来说明吗?请问谁为我们解决了衣食住行之所需呢?谁为我们提供了物质保障?还不是农业吗?是农民,先生们,用勤劳的手在肥沃的土地上播下种子,长成了麦子,用巧妙的机械研磨成粉,然后把它送进城里,很快由面包房制成食品,分给富人,也分给贫民。不也是农民,放牧大量的牛羊,为我们提供衣服吗!没有农民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先生们,这些明摆的事实还用得着费劲去想吗?我们不是经常想到这种普普通通的小动物,家禽场里的那些鸡呀鸭的重要意义吗?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柔软的枕头,鲜美的肉和蛋。我不再把精心耕作的土地的不同出产一一枚举,因为那是说不完的,土地对于我们,就像母亲对子女一样的慷慨。这里有葡萄,那里有苹果,那地方是油菜,再那边有奶酪,有亚麻。先生们,可别把亚麻忘记了!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近几年来,亚麻的发展巨大。
听众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一个个大张着嘴,好像要把他的话全部吞下去。坐在他边上的蒂伐什睁大眼在听,德洛泽莱先生则不时地微闭着双眼。稍远一些,药房老板把拿破仑夹在两腿之间,捧着耳朵,不让漏掉一个字。评审团的其他成员边听边点着下巴表示首肯。主席台下的消防队员,依在他们的刺刀上歇息,比奈手肘朝外,刀尖朝上举着指挥刀,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知他是否听得见,反正他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的头盔帽檐一直压到了鼻子上。他的副手是蒂伐什先生的小儿子,他戴的那顶头超大,在他头上晃晃悠悠,还露出一段垫在里面的花布头巾。他在头盔下傻笑着,苍白的小脸上满是汗珠,显得开心又疲惫,带着睡意。整个广场挤满了人,还有不少人趴在自家的窗户上或者站在门口。于斯丹站在药房门口,出神地听着,虽然人们尽量保持安静,可是离柳文先生越远,声音也就越小,不是椅子挪动的声音打断,就是被不时传来的一声牛鸣或羊叫所淹没。
罗多尔夫又往爱玛身边挨近了些,低声说:“难道你不厌恶社会上的这种阴谋?有哪种感情不受到世人的责难?高尚的本能和纯洁的激情无不遭到迫害和诬蔑,如果一对可怜的人相爱了,有人就会想尽办法拆散他们。可他们会相互激励拼死抗争。啊!时间迟早没有关系,6个月,10年,它们终将结合和相爱,因为命运注定他们是天生的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