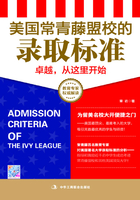他走的那一天清晨,铁门突然咣啷大响,把我从睡梦里惊醒。几支白炽强光灯照射过来,使我什么也看不清。好容易躲开了强光的直射,我看见小脑袋又被来人推到一旁,看来今天还是不关他的事。他的胡须又一次白刮了,新衬衣也是白换了,早早起床也是白费工夫了。
几个武警士兵知道自己的目标,一进门就径直奔向大嘴巴,没等他洗脸和刷牙,就把他连人带枷抬起来,缓缓向门外移去。
大嘴巴转动颈根,朝我斜斜地看一眼,算是最后告别。
“兄弟,兄弟,你慢慢地走呵。”我鼻子一酸,轻轻地说,也不知道他听到了没有。当时仓里太乱,脚步声和吆喝声响成一片。因为牢门窄,脚枷长,士兵们无法把他平抬着出门,就将枷举起来倾斜了一个角度。这使他的最后出门是一种杂技动作,四肢舒展,在空中慢慢翻旋,有一种太空人遨游天宇的姿态。他叫了一声“唉哟——”大概是脚踝被脚重枷别痛了。我事后回想起来,这一声轻得像蚊子叫,却是一个人留给9号仓最后的声音,真真切切地扎在我心里。
“你们手脚轻一点。”我忍不住请求那几个兵哥。
“听见没有?手脚轻一点!”有人却在我身后大吼。
仓里一片寂静。兵哥们回过头来,几支白炽灯到处照,寻找着叫声的来源,最后照在斜视眼的脸上。他抄着手靠在墙边,对白炽光既不退让也不躲避。
“你凶什么?想造反吗?”一个当官模样的人冲上去,手枪狠狠对准了他的前额。这等于给出一个信号。室外突然发出一片哗啦啦子弹上膛的声音。我到这一刻才发现,高高的监视窗外,全是武警士兵们警惕的眼睛,还有黑洞洞的枪口。放风室那边也是一片应声而起的子弹上膛声。原来那里的天窗盖早已掀开,监仓像一口竖井暴露在旷野,井口周围布满岗哨,只是我们刚才并不知道。一见这边有反常事态,那边开始紧急增援,井口上整整一圈射灯全部打开,白炽光铺天盖地倾泻而下,刺得我们睁不开眼睛,照得连任何一只蚂蚁也无处藏身。井上的兵哥们纷纷大吼:不准动!不准动!两手抱头!全部蹲下去!都蹲下去!……
我们都吓得抱头蹲下去了,只有黎头还是横着一只眼,额头紧紧顶住手枪,甚至顶得军官退了一步:“我要你们手脚轻一点!这是抬人,不是抬猪!”
“反了你?对抗执法,格杀勿论!”
“你杀呀!杀呀!孙子!”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老子今天就是想死!你不在我脑袋上打十个洞,我同你没完!”
黎头今天已经疯了。
他断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的心已跳到了喉头,怕军官一气之下,稳不住指头,黎头的脑袋就真要穿个洞,透透风,一注鲜血喷上墙。如果再加几个当兵的稳不住指头,我们大家今天也会一阵狂舞乱跳,落下全身的筛眼。幸好此时有一警察插上来。“强仔你疯什么疯?找死吗?你有几颗脑袋?今天要不是没时间了,非整你个出屎不可!”他哗啦一声把黎头双手铐住,算是搅了局,然后招招手让兵哥们离开。
一道道白炽电光也渐次熄灭,门外和屋顶的嘈杂脚步声陆续远去。但我们都没说话,也没话可说,一直等到天放亮,等到一块方形霞光从监视窗斜斜地照进来,然后在砖墙上移动,拉长,变形,变成不规则的长锥形,最后变成一束稀薄而涣散的斜线。高墙外有远远的一声牛叫,吓了我一跳:是大嘴巴报来什么消息吗?大墙外又有远远的几声打桩机轰响,又吓了我一跳:是大嘴巴咚咚的心跳吗?还有一个声音,初听像小孩叫声,细听像小孩叫声,听来听去,发现它确是小孩的叫声。
我发现,原来任何一种熟悉声音都会变得陌生。
送餐人员来吆喝了,但没有人打门要餐,也没有人拿自己的东西来吃。我们只是呆呆地坐着,说不清自己为什么难受。
这一天我做了个梦。我梦见自己把一支粉笔当香烟,把粉笔的一端蘸上红墨水,就成了点燃了的烟头。我叼着这支假烟,很像一个便衣警察,大摇大摆地往门外走去。警察们没看出我嘴上的假烟,没看出我狡猾地隐藏在一支假烟之后,一个个都向我微笑,点头,打招呼,傻乎乎地纷纷让路,听任我迈着八字步走出了第一道大门,走出了第二道大门,一直走到了大街上的人海里,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
我醒来以后,不知这个梦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