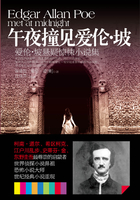那时候没有室外放风制度,只是每个监仓配一间放风室,两室之间有门相通,像个左右套间。遇到天气好的时候,警察揭开放风室的天窗盖,差不多是掀掉整个屋顶,让阳光穿过粗大的钢筋栅栏投射下来,散一散室内的潮气和臭气,就算是放风了。这比室外放风要安全得多,简便得多。警察们肯定是这么想的。
一般来说,水池与厕所也在放风室里,不过看守所超员羁押,每个放风室总是躺着密集人肉,相当于客厅和厕所都成了卧室。
除了去接见室或者谈话室,我们被六面墙团团包围,从不能越牢门半步,眼里既没有草木和泥土,更没有以前生活中的人面。接见室里墙上的一个圆家伙,是叫挂钟吧,很像一个挂钟吧,经常能陌生得让我吓一跳。我发现自己差一点忘记了挂钟,于是紧张地试着回忆以前一切熟悉的人名、地名、物名,试着想象那些东西的形状、颜色以及气味等等,担心这一切会变得模糊涣散,在这个六面墙的洞穴里逐步消失,漏到地底下去。
放风室里那一块方形天空,如果能够向我们开放,就是我们平时唯一能看到的世界了。那里可能有一只麻雀停栖,一只蝴蝶停栖,或者是蓝天里有一丝白云悠悠飘过,让你忍不住要东想一下,西想一下,其实什么也没想。我总是试图抓住这块天空中的任何一丝变化,努力推想外面的季节、环境以及可能的生活情景,确证这个洞穴还在世界上,还没有被世界抛弃,没有坠向太空中越来越远的深处。
别看有些人嘴硬,其实没有人不怕坐牢,没有人不怕自己落在这一块方形天空之下。一到了这里,眼光有极度的饥渴,灰色的日子漫长得让人发疯。哪怕是最硬的汉子,从接见室里回来,在半夜里醒来,都可能忍不住两行泪水。哪怕是最文雅的书生,为了半碗剩饭,或者一个烟头,都可能在这里勃然大怒大打出手,越活越像头野兽。
打架在这里是常事。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是光头们为什么而打,甚至不知道是什么人打什么人,只知道仓里一眨眼就地动山摇昏天黑地,像夯地机一通电就开始抽疯抓狂。有时候你甚至觉得每个人都在向其他人开战,每个人都是见人就打,没有什么营垒和阵线,打来打去也没有目的。一场恶战下来,有人少了几撮头发,有人的手腕换了个角度。但完成这一切以后,大家一哄而散,该睡觉的睡觉,该搓脚的搓脚,如同什么也没发生。
警察们对这些差不多司空见惯,有时候抓两个打手到院子里教训一番,也管不了下一回。他们甚至问不出什么结果。不光是打赢了的不会说,挨打的也绝对嘴紧,总是露出一脸茫然,与囚友们面面相觑,好像这里一片祥和太平,没有什么事值得政府操心。至于他们嘴边的血污,肯定都是自己“摔伤的”或者“碰伤的”,不值一提。
世界上有很多动物园。但这里是人的动物园,是人们恢复利爪、尖牙、尾巴以及将要浑身长毛的地方,是人们把拳头和牙齿当作真理的地方。你不服气吗?还想来点喷上了香水的什么人格呀、尊严呀、民主呀、法制吗?还打算像抹了胭脂口红的少先队员那样来呼唤爱心与和平吗?拉倒吧。我在一本书上读过:猴子有猴王,蜜蜂有蜂王,鱼群里也有头鱼,没有平等可言。特别有意思的是,头鱼大多数是残疾,不是身经百战伤痕累累,就是有点神经分裂症或者更年期综合征,因此特别顽强和凶猛。养鱼人知道这一点。他们通常会故意把某条鱼搞残疾,这样它就可能成为头鱼了,就能使鱼群得到秩序和安定了。没有头鱼的鱼群,只是苟活一时的零食。
我们的头鱼也是残废。我看过他接到的起诉书,给他写过上诉材料,知道他刚满二十岁,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头,照理说只合适在街上卖卖报纸,擦擦皮鞋,扛一桶矿泉水爬上高楼,是赚点小钱的那种人。但他居然当过大街上的菜刀队队长,在南门口到新新商厦一带颇有名气,断过两根肋骨,背上有三四条刀伤,可说已身经百战。这一次入狱的事端,就是一刀捅进人家的胸脯,只因为刀子被骨头卡住了,实在拔不出来,才没有再捅一刀,留下了对方一条性命。
不过,从我认识他起,我倒没见他动过手,大概他人小威大,一般用不着自己亲力亲为。我曾经好奇他的威从何来,老少犯人们也说不大清楚,甚至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这样说吧,他敢于在枪口之前与警察叫板,言人之不敢言,为人之不敢为,就是一种大威。他可以把图钉尖朝上,然后一巴掌把图钉拍进自己的手心,也是一种血淋淋的威。他还可以与人打赌,一口气吃下两袋味精,吃得嘴唇都乌了,两眼发直,全身有一种触电后的痉孪,脑袋不由自主地朝两边甩,那当然更是一种疯狂的威。
他还吃过一斤生猪肉。据说他喂养过大狼狗,给大狼狗喂生肉,发现吃生肉的狗最勇猛,最凶悍,自己也就跟着吃。
凭着这一切,小斜眼享有至尊的地位和无边的权利,在监仓里咳嗽一声,就有全仓的鸦雀无声。不仅早上有人替他打水和挤牙膏,不仅晚上有人替他铺床,他喊一声“电扇”,就有人给他大摇蒲扇,他喊一声“收音机”,我就得放下手里的事情,赶紧给他开机和选台——虽然少了一颗门牙,但得播放出各种男声和女声,高声和低声,再加上前奏和过门的各种音乐。包括沙锤、钢鼓、长号以及萨克斯,全都行云流水上天入地并且闪耀着伟大艺术的光辉。我捏住一只鼻孔大摇手掌,摇出的二胡颤音,自己也觉得十分动听。
“我也见过苏什么,苏芮吧?”他淡淡一笑,“那次我在广州同几个弟兄扯扑克,咣咣咣,把他们打得两眼黑,一个个滚到桌子下面。听说有苏芮的演唱会,我召了一部的士直奔越秀公园。我到那里发现没有票了,咔嚓,老子给门卫一个眼色,唰,两张纸往他口袋里一塞,……”
我发现他描述往事时,一高兴起来,最喜欢用象声词,就像话语里夹进一些打击乐。比如递眼色是“咔嚓”一声的,塞钱是“叭”的一声的,还有灯光亮了是“咣当”一声的。他的开心事都是铁罐子木桶子,在脑子里碰撞出一路的声响。我相信,他的偶像一定更热闹无比。刘欢是大胖子,出场想必是轰隆一下。程琳是瘦小精灵,出场想必是吱溜一下。费翔英俊潇洒,目光肯定锐利得唰唰唰。邓丽君小甜妹的脚步呢,必是咿呀咿呀在心窝子里揉。
“你怎么一嘴的打击乐?”
“什么打击乐?”他睁大眼。
“也就是递个眼色,咔嚓一下做什么?”
“我咔嚓了么?”
“你刚说的,自己就忘了?”
“你胡说。”
“我怎么胡说?要是有个录音机,叭叭叭,全给你录下来!”
事后一惊,我也学会了象声词“叭叭叭”。这真是没办法,同他一起混久了,我脑子里也多了些莫明其妙的动静。
他虚心地向我学唱音阶,学识简谱,还记下了很多歌词,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笔记本花花绿绿,一些歌星头像的剪贴,来自破报纸旧杂志。一些用彩笔描出来的山水、花朵、青松翠柏什么的,装点着各种歌词。其中大部分是流行歌,无非是爱情呵泪水呵小雨呵花朵呵昨天呵黄昏呵孤独呵,粉红得厉害。他的错别字太多,总是让人连读带猜,硬着头皮看甲骨文。
但他的五音不全一次次让我失望,糟践艺术的恶习更让我经常气愤。《恰似你的温柔》在他嘴里恶声恶气,成了掐死你的温柔。《酒干徜卖无》开头两句本来是:“多么熟悉的声音,伴我走过了多少风和雨……”但他心里一邪,常常唱成“多么恐怖的声音,陪我多少次抽脚筋……”还有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里面有两句:“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他一高兴就唱成“我们坐在高高的骨灰缸边,听妈妈讲那锅里的烧饼……”
他有时还强迫大家一起来糟践艺术。有一个福建籍的老光头,把任何歌曲都当安眠曲,谷堆旁也好骨灰缸也好,他一听就呼呼入睡,放出尖锐的鼾声,使歌手觉得大煞风景。
黎头对他从来没有好脸色,看他上厕所就脚下使绊子,有一次还借口那家伙把“馒头”发音为“慢猴”,对闽南方言勃然大怒,说这老货进仓两个月了还不会普通话,简直不是个人,命手下人扇他两耳光。
“到底是馒头还慢猴?你说!”小斜眼揪住对方的耳朵。
“馒头,馒头!”
“再说一遍。”
“馒头!”
黎头这才松手。
说实话,这里不是播音室,普通话就那么重要?何况黎头自己的京腔也是狗屎团子。但大家敢怒不敢言,身处牢头的淫威之下,折磨着自己的口腔舌头,还是尽力挤压出一句句中国外语,反而让人没法懂。
同样道理,监仓也不是军营,把口杯放成一条线,毛巾挂成一条线,棉毯折得四方四正有棱有角,这些黎头立下的规矩也十分可笑。他一时心血来潮,是不是要把我们统统培养成纪律严明的特种部队?是不是要争创模范卫生单位?我后来也蹲过别的仓,当劳动仔时还到过其它仓干过活。我发现很多监仓一点组织纪律也没有,犯人们吃饭时分成三国四方的这一“锅”那一“锅”,有了纠纷时找不到联合国,找不到维和部队,一口饭都吃不安稳。那些监仓更没有卫生执法和语音学执法,文化档次太低了,经常乱得像狗窝猪圈。这样一比,9号仓虽然也是奴隶社会,但至少是个比较整洁有序的奴隶社会。我对此似乎不应有什么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