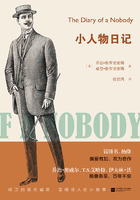煤油灯的捻子炸了一下,焰光突然就亮了。纸面的小字长大了几分,能看清它们的模样了。我的心也亮了一下,不再疲倦,想再看一会儿书。
灯捻炸裂的声音把父母惊醒了。母亲从被窝里探出身子,不耐烦地说:“别看了,省着点儿眼吧。”
父亲摁下她的身子,“孩子愿意看会儿,就由着他,别添乱。”
母亲很不服气,“这年坎儿,念了书有什么用?再把眼睛觑乎坏了,下地的时候,庄稼和草都分不清,就成废人了。”
“嘁,你是怕费油。”
“是又怎么着?”母亲的语气有些亢奋,“就你这个支书当的,一个日工才三分钱,只够买个油饼,年底结算,还欠着队里的,买个油盐酱醋都没钱,还得抠鸡屁股用鸡蛋换。”
母亲的话戳中了父亲最薄弱的部分,他的腿在被窝里重重地摔了一下,“真是妇道人家,夹缠得很,你也不想想,灯油它长着腿呢,省着不用,也会搁干了。”
父亲是指煤油的挥发。
母亲就不吱声了。
我就接着看书。其实我那时看书也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朦胧地觉得,父母的锄杆的确捋不出什么来,正被批判的孔老二的一句话——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或许是有些道理的。
书虽然继续读下去了,但躺在被窝里的父母总是不时地弄出一声叹息,让人心不安。“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瞎眯着。”晚饭我们喝的是稀粥,靠睡眠把肚腹欺哄过去。所以,贫穷的日子承受不了多余的灯光。
我只好装作已经困倦了,悻悻地把油灯吹灭了。
在土炕上辗转反侧地期待了很久,终于等来了一头疲脸子的瘦驴,径直朝我走来。地点是村口大柳树下,那里有一盘石碾子,村里人收工之后,多是聚集在那里乘凉。蹴着那么多人,驴子唯独走向我,我兴奋极了。驴子对我说,你跟我走一趟,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驴子让我骑在它的背上,抬腿就飞了起来。飞到大平原的上空,盘旋了一阵,发现了一处烟囱林立、有围墙的地方。驴子咴咴地叫了几声,直直地落了下去。落在一个院子里,有一群穿蓝工装的人,正围着一个大笸箩吃馒头。他们从笸箩里拿馒头,可拿来拿去,那笸箩里的馒头总也不见少。我吃惊不已。驴子朝我点点头,问我,吃馒头的日子好不好?我说,当然好。我说的是真话,在我们那里,“啃咸菜就窝头,一天两顿稀面粥”,生活得跟口诀一样,有谁不稀罕馒头?驴子说,那好,念你读了那么多的书,就留在这里当技术员吧。这天降的喜事把我弄懵了,我愣在那里。驴子啃了我膀子一下,你已经是这儿的人了,还不赶紧去吃馒头。我朝着那个笸箩扑了过去。
当当,当当……发抖的手就要触到馒头的时候,刺耳的声音把我弄醒了。当当,当当……我分辨得出,这讨厌的声音,来自村口大柳树上的那口锈钟。“睡觉都不老实,净踹被子,被子里那几两棉花,哪经得住你这样踹?”在远的钟声中,母亲在近处埋怨道。
我睁开眼睛,很懊恼,“敲钟的,是不是我爸?”
“不是他还能是谁?”
“敲得再响,能敲得出馒头?”
母亲摇摇头,觉得我既莫名其妙,又十分刻薄。
别看父亲赞许我晚上读书,但每到星期日和寒暑假,他就绝对不允许了。他把我赶到庄稼地里去,参加劳动。我跟他说,我不稀罕那几个工分。他说,你以为我稀罕?你是支书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地里劳动,你不能搞特殊。那时,一个伟人撂下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不仅要学工、学农,还要学军。父亲牢牢地记在心里。
春天社员们在堰田里翻地,用瘦长的铁镐。山西人用的是镢头,刃子很宽。因此人家翻出了个大寨,而我们什么名堂也没翻出来,虽然地处北京,被燕山的大脊梁遮盖的这个京西小山村,却始终籍籍无名。社员们翻地的时候,懒洋洋的,与其是为了种粮食,不如说是翻给他这个支书看。
依山起伏的堰田,看着是一方美丽的风景,镐子翻下去,薄薄的土层下,净是石头。翻出的声音透着穷气,旱出的烟尘,很呛人。人心恓惶,种子撒下去,出得了苗吗?
一个叫扁儿的社员,总是直起腰来,愣愣地戳在那儿。父亲走过去,朝他的腰眼上踹上一脚,“卖点儿力气好不好?”
“卖个鸡巴!”
父亲又踹了一脚,扁儿回应的还是那句粗口。
“扣你的工分儿。”父亲威胁道。
扁儿反而嘻嘻笑起来,“不扣,你是丫头养的。”
扁儿的个子很矮,瘦刀螂一样的脸上,净是被抓过的伤疤,谁都不把他当人看。家里总是亏粮,媳妇就总拿他出气。媳妇叫小金花,却长着个大身坯,他只要一顶嘴,小金花就抓他。他忍着,忍着,心里怕她。但临出门的时候,却趁其不备,在女人娇气的腰眼儿上狠狠地踹上一脚,女人来不及叫上一声,就趴在地上了,十天半月出不了门。他像对自己也像对别人说,怎么忍来忍去就忍不住了呢?你说他不怕媳妇,在媳妇面前萎萎缩缩地任打任骂;你说怕媳妇吧,出手又那么狠。人们不理解他——即便是伤痕常挂在脸上,谁也不关心他。
没人给他做饭,中午的干粮只是两只柿子。
到了中午,人们要在草窠子里睡上一晌。肚子喂不盈,睡就盈了。父亲惜时,跑到山梁上去打烧柴。一大捆烧柴打回来了,人们还横七竖八地挺着尸首。父亲挨个地踢他们,“起,该干活儿了。”
扁儿从眼缝里乜了一下父亲的那捆烧柴,“看来,就属你是盏人灯哩。”这是一种极端的反感——于公于私,你都占了先先,我们还做不做人?
收工的时候,扁儿蹴到父亲跟前,阴郁地笑笑。父亲一边回应地笑笑,一边往背篓上装柴捆子。父亲刚要背起来,扁儿伸手就把柴捆掀下来。因为没有宣言,父亲愣了一下,“你要干吗?”“不干吗。”扁儿嘻嘻笑着。
“你真是没事闲的。”父亲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只是摇了摇头,重新装他的柴捆子。
扁儿又给他掀了下来。
父亲急了,喊了一声,“你再掀一个试试?”
社员们都围拢过来,他们觉得,这下该有好戏看了。
父亲阴沉着脸子,索性把柴捆子直接扛上了肩头。扁儿的脸色也庄严起来,“今天你肯定背不成!”他跳了起来,越过了高大的父亲,把柴捆及父亲全扑倒了。
周围一片欢笑。
父亲爬起来,高大的身躯直直地朝扁儿的小身材逼过去。
我看到,扁儿的脸色苍白,整个身子都在颤抖。我兴奋极了,一个壮观的场面就要诞生了。
“横竖就是一捆烧柴,不背就不背。”在父亲居高临下的时候,居然说了这么一句泄气的话。
没有故事发生,人群便无声地散了。人们走在阔大的山脉上,像羊拉下的粪便,很渺小,看不到表情。
扁儿走在我们的身后,走得无声无息。
父亲几次搭讪着要跟我说话,我懒得理他。这个支书当的,一点儿尊严都没有。
进了家门,我把事情的原委跟母亲讲了,母亲一下子就火了,“我去找他,干吗欺负老实人!”
父亲一把没拦住,母亲转眼之间就没影了。
但很快母亲就回来了。我问:“出气了?”
母亲白了父亲一眼,“出气?憋气!”
母亲说,小金花死人似的躺在炕上,扁儿死人似的圪蹴在炕洞前,炕洞里连一粒火星都没有。
父亲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吃饭。”
扁儿确实让父亲跌了威信。上工的钟都敲了两袋烟的工夫,居然不见人出来。父亲很纳闷,对我说,你去挨家挨户问问,他们还出不出工,如果不出工的话,就扣他们的工分。我说,你还是自己去吧。我还在对他昨天的表现耿耿于怀。父亲很柔情地摸了摸我的头发,说:“我一个堂堂的支部书记,哪能这么干?”
我挨家挨户问过,对兀立在大柳树下、满脸渴盼的父亲说:“他们都铁了心不出工了,且让我捎信给你,工分太少,他们不稀罕,你愿意扣就扣鸡巴的吧。”
父亲跌坐在碾盘上,嘴里大叫:“完了完了!”
我说:“你还是去公社吧,让他们派工作组来。”
“你净出馊主意,你当他们是谁?他们都是老街坊哩。”父亲瞪了我一眼。
那个时候,讲政治挂帅,破坏生产的人,往往是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
父亲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独自上山了。
在堰田里,山风凄切,他权当是社员们的窃窃私语,镐子翻下去,也一丝不苟。他对自己说,狗日的都看着咱哩,绝不能偷一点儿懒。翻着翻着,脸上挂满了眼泪。他也不明白,这么没地力的薄土,打下的粮食还吃不盈一季,干吗还一年接一年地死死地摽着?干吗不让搞点副业,肥肥嘴儿呢?
他怀着满腔的幽怨,复仇一般使着狠力气。天气不体恤他,还是初春,就已经是干热干热的了。他闪了棉袄,只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破秋衣。汗水洇湿了后背,继而变成碱。日光游移,汗碱的图案不停地变换:一会儿是张羊脸,一会儿是只牛头……总之,都是山里的畜牲。累了,他只想笑。就笑。呵呵地,似哭,似犯了神经。“这个支书当的。”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嘲笑自己。
呵呵,呵呵……
终于干满了点儿,他披着稀薄的夜色,踽踽地走回村口。大柳树下,蹲满了一色的青壮劳力,他们端着青瓷大碗,一边哧溜哧溜啜着稀粥,一边用筷子敲着碗沿。他们是做给他看的。他低着头,径直走过去,愤愤地撂下一句话:“真是一群贱人!”
第二天,该敲钟的时候,他手里的钟槌举起来又放下,最后,还是敲了。“兴许他们只是装个样子呢?”
两袋烟工夫的钟声,终于没有唤来一个人,他彻底失望了,头也不回地上山了。
第三天,柳树上的钟他只是看了一眼。第四天,他头都懒得抬一下,急匆匆地从柳树下走过。
或许是过了一个星期的光景,父亲正在没滋没味地吃早饭,钟声竟恶作剧般急急地响了。父亲手里的粥碗跌落在地上,碎了。母亲说:“瞧,又没了八分钱。”
父亲推门而出,跑到了大柳树下。见队里的青壮劳力都簇在那里,手里都攥着翻地的家伙。
“敲钟干吗?”父亲问。
“出工。”众人回答。
父亲摇摇头,“是怕扣工分吧?”
“放屁,我们是怕错过了节气。”
父亲心头一热,到底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种地的本分,让他们呆得恓惶。他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兀自朝前走去。人群尾着他走,谁也不说话。他心头突然难受起来,喉头哽咽着。“你们且记住,我会对得起你们的。”他对自己说。之后,又有些不甘心,恨恨地骂了一句:“这帮狗日的!”
玉米勉强地拔节了,荒草却茁壮。这是旱地特有的景象。因此,社员们不得消闲,还得锄耪。玉米的叶子像一把把有暗刃的刀,在人们的臂膀和腿子上割出一道道的伤痕。人们怨恨不已,却异常勤劳。他们有一个朴素的道理:糊弄庄稼,就等于糊弄自己。
还不到蝗虫发作的时候,蝗虫的青虫就很肥大了。这是对庄稼人的嘲讽,他们心里很受刺激。因而也就爆发了一种野性——
他们把锄头撇在一边,在田埂地垄上,蹿来蹿去地捉青虫。他们用草梗子把青虫穿起来,燃起地火烧烤。他们有大本事,青虫烤熟了,草梗子却不断。他们大量地吞嚼这些虫子,咬肌暴突,真不像人。
父亲捉虫子的数量最多,吞咽的数量也就最多。他的嘴唇和舌头都黑了。捉到兴头上,他觉得汗碱浆过的衣裤很是碍事,索性就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内裤的成色实在糟糕,关键的部位破破烂烂的,开了天窗,蛋卵子时隐时现。在场的社员有不少婆娘和小姑,她们偷偷地笑,男人们则嗷嗷地叫。但父亲却很忘我,翻转腾挪,如入无人之境。父亲身长,动作的姿势很像什么。扁儿突然说:“简直是条大狗。”众人大笑,齐声呼应:“对,大狗!”
“大狗!”
“大狗!”
……
传到父亲耳朵里,他居然知道人们是在叫他,不恼就是了,还索性叫上几声,汪汪,汪汪……
众人笑得前仰后合。“好日子!”他们说。
起初我还为父亲羞惭,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之后,也不觉得那么严重了,便偷偷地笑。
扁儿看了我一眼,“小狗。”
我嘿嘿一笑,“我要是小狗,现在就把你裆里的东西咬下来。”
扁儿做了个捂裆的动作,好像真的被咬到了,眉头紧锁。
随后,我们往一块儿笑,都不觉得对方可恨。
玉米终于顺利地吐穗了,小雨也极节俭地来了几次,人们紧悬着的心落得妥帖了些。在常识里,只要不是连天的大旱,即便是雨水稀少得像泪珠子,也不会闹蝗灾。山地的玉米长得忒慢,平原的中茬玉米都收获了,它仅仅是抽穗而已。锅里的粥越来越稀了,社员们便且闲且恓惶。
父亲对众人说:“狗日的们,我让你们开开荤。”
扁儿撇一撇嘴:“你糊弄谁?”
“我让你们吃鱼。”父亲毫不犹豫地说。
扁儿翻了翻白眼,像明白了什么,嘴角刚要绽出笑来,却猛地拍了一下大腿,“操,你真是馋晕了!”
村里的确是有条河,但连年干旱,河脉浅,有的地方,索性就断了。没有大水,哪里有大鱼?一些小鱼罢了。
山里人没有打鱼习惯,不置备网罾。那么,用什么捞?所以,扁儿认为父亲在起哄他们。
父亲坐在河边的鹅卵石上,想了半天主意。
“药它。”父亲突然说。
“用什么药呢?”扁儿问。
“苦杨。”父亲给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
“行吗?你真会想歪主意。”扁儿带头反对。
“支书是我还是你?”
父亲便带着众人到山上去打苦杨。并称,不管理解不理解,打就是了,给你们记工分。
苦杨,并不是一种杨树,它是山上的一种灌木,枝条柔曼,有细长的叶子。苦杨的皮剥下来,捣碎后放到碗里,倒上水便呈浑黄色,喝上一口,苦极了。但去火治淤病,是一种药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