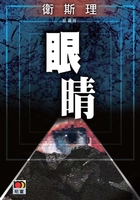“现在进行时”里的真实进入尤凤伟的小说世界是一件相对轻松、甚至是适宜的事情。平和的语言、不紧不慢的叙述,让你感觉仿佛是坐在一个和蔼的说书人面前,他有一麻袋一麻袋的故事,慢慢地抖开去——悲欢离合的演绎中弥漫出让人窒息的真实的迷雾。你身不由己地被裹缠了进去,惊愕、绝望、挣扎中,蓦地发觉,说书人已杳无踪迹……
这便是读《泥鳅》的最直接的感受。尤凤伟是很会讲故事的,即便是对那些极其挑剔的读者,苛刻的评论者,他也来者不拒地先用故事的磁场把你牢牢罩住——毕竟,人的本性不会拒绝故事,小说的基本面亦是由故事构成——然后变魔术般地兜出一道道真实的细节,一幕幕惟妙惟肖的风景。你几乎忍不住要由衷地赞叹:久违了故事,久违了真实。
精彩纷呈的故事与逼人的真实结合,这是尤凤伟在现实主义的山径上匍匐、攀援数载后的宝贵心得。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予人以真实之感(细节刻画得翔实牢靠)是一部小说至高无上的品质——它就是令所有别的优点都无可奈何地、俯首帖耳地依存于它的那个优点。如果没有这个优点,别的优点就会都变成枉然。”真实的细节是故事的脊梁,它将故事推入遍布可能性的巨大发展的惯性空间。而尤凤伟做得更绝,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义无反顾地向着真实的渊薮坠落。
在《泥鳅》里,真实具象为一群游移、飘零于城市的打工仔的生活原生态。尤凤伟像一个穷追不舍的摄影师,将镜头对准这灰色的人群,且不断推近距离,于是我们看到了他们疲惫的笑容,他们额上的汗珠,乃至眼泪与激情,连同那忽明忽暗地燃于心底的卑微的希望与憧憬……
对于这种真实,尤凤伟从不犹疑。就他而言,这些就像鲁滨孙刻在树枝上的日期那样深刻、鲜明。他看到了,感触到了,思索过了。真实不再是哲学上那个纠缠不清、摇曳不定的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不再神秘莫测,不再要通过什么精致的感官冒险才能捕得它的一鳞半爪。它清晰地呈示在你的面前,生活的严酷和冷漠使得原本大而化之的“感同身受”的方式成了衡量真实的权威尺度。如何让读者和自己一样“感同身受”呢?尤凤伟使出了自己的绝活——抖开了故事的包袱。
尤凤伟对故事相当有信心,他认为作家有责任、也有义务把一个故事向读者交代清楚,叙述故事之于作家,就像素描之于画家,是一种基本功。精妙的情节在尤凤伟这里似乎是源源不绝的,以致他来不及精挑细拣,细致描画,一概兜出便是了。于是,有头有尾成了尤凤伟故事最大的特点。不到最后一个情节的涟漪彻底消失,尤凤伟是绝不肯轻易罢手的。虽然写得有些膨胀、不透气,但无可否认地,故事却是立体地凸现了。比较起来,张炜就没这么走运了,他与故事之间似乎总是隔着一层雾。张炜围绕着故事转,不知该如何切入,仿佛是担心一动,便会破坏故事的完整性。于是他只好对着故事冥想,从空气的脉搏里把握出感觉,在谨小慎微里艰难行进。他时常被语言绊住,陷在句子里拔不出来,励精图治般地要在每个句子里“雕”出感觉。而尤凤伟则不同,单看他的每个句子似乎没什么诗意,但这种局部的粗糙却换来了故事的圆融,一气呵成,以整体取胜。尤凤伟仿佛是在跳着踢踏舞在故事中行进着,如沐春风,欢畅流动,由此带来的阅读的亲和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那外表低调、不事花哨的叙述里却凝聚了尤凤伟全部的激情与智慧,既是他的欢乐,也是他的绝望;既是他的苦痛,也是他的报酬。
为了使情节不致散漫、游弋,尤凤伟在《泥鳅》里创造了“泥鳅”这一意象。泥鳅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动物,它作为主题的变奏不时在故事中闪烁、回响。小说中写到泥鳅豆腐汤,泥鳅遇热往豆腐里钻,这完全是一种在求生欲望支使下的本能反应。作者以此来暗示、渲染打工仔在城市里被命运之手任意牵着鼻子走时的无奈与挣扎。如果泥鳅暗指国瑞的话,那豆腐即是喻指国瑞身边的一群女性,她们温柔的庇护最终没能挽回国瑞悲惨的结局。由泥鳅,让人想到荀子《劝学》中的一句话,“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这里,“蟺”通“鳝”,黄鳝与泥鳅很像,且都善于钻洞,然而最终却只是被蟹利用,成了个棋子,就像国瑞被宫超白白牺牲一样。泥鳅并非如一些评论者所指出的,是性的象征,与世无争的泥鳅背后掩藏的是对命运的黯然神伤。
故事将真实与虚构密不可分地扭在一处。值得一提的是,《泥鳅》里孜孜以求的真实是从“现在进行时”的生活流里捕捉的,小说和现实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甚至近得让人有些屏息。民工在城市里不可不谓司空见惯,这一流动的群体离开了农村,却无法洗去农民身份的烙印;进入了城市,却只能做个局外人,在都市的边缘和角落里喘息、做梦。关于他们的报道虽不时出现,却难得跳出一张个性的脸庞,至于他们的心灵世界,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更是一团黑暗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泥鳅》是及时的,它是以往的农村题材在特定的当代条件下的发展与变体。与欧洲流浪汉小说的猎奇迥然不同,《泥鳅》写的是当下的农民,尤凤伟的出发点是严肃而真诚的。
“当下”或者“现在进行时”是让不少作家神经紧张、望而生畏的词儿,它是遏制想像的“紧箍咒”,对象明明近在眼前,却幻变不清,无从把握,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作为结构的具体的现在——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行星;我们既不知道如何把它存于我们的记忆中,也不知道如何以想像力来重建它。”“现在进行时”抹杀了空间的距离,吞没了“时间差”,而这些恰恰是灵感、想像在凌空腾跃前必要的助跑。还是回到“过去完成时”吧,不用再殚精竭虑、胆战心惊,“我爱你,所以我要远离你”。隔着时空往回眺望,活动活动僵硬、迟钝的想像之翼,一股脑地杀进“过去”。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沈从文的湘西情结,对阎连科为什么钻到耙楼山脉里不肯出来的苦衷也有所了悟。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纷纷攘攘的现实只是抽空了美感汁液的干瘪的葡萄,它与文学审美之间不仅永远是不等号,而且针锋相对,背道而驰。这迫着他们从现实中抽身逃遁,在一个遥远、封闭但“安全”的空间里栖放自己的心灵。而尤凤伟却有一种独特的本领:他不仅在“现在进行时”的生活流里站稳了脚跟,而且能随时从其中撷取事件,放进灵感的熔炉,炼出诸如《泥鳅》之类的金丹来。这在弥漫着一派回忆与梦呓的当代文学中实属难能可贵。
真实的搁浅:尤凤伟与时间的“契约”
尤凤伟以他的激情连同说书人的机智为我们缝制了一个精巧、严密的真实的荷包,荷包上布满了他亲手捻制的情节之线。故事将真实凝固、定格,但问题在于,当我们被吊着胃口,从头读到尾——故事结束了,感觉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真实将告一段落,连同真实中的人物——国瑞,也随着故事飘然远去。我们看到他凄然的笑容,却无法挽留他那渐远渐去的身形。“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曾让人心醉神迷、信以为真的故事如今却断然将国瑞与我们隔开,故事那边,是另一个世界了。
何以会造成这种隔离之感?这似乎还得从故事本身说起。爱·摩·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给故事下了个定义:“故事就是对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述——早餐后是午餐,星期一后是星期二,死亡以后便腐烂等等。就故事而言,它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使读者想知道以后将发生什么。反过来说,它也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弄到读者不想知道以后将发生什么。”福斯特显然对故事评价不高,甚至将其喻为“冗长无比、蠕动不休的时间绦虫”,主张用“镊子”将其从小说的肌体里剔除出去。
很明显,福斯特意识到了故事对小说家的束缚。然而,这束缚究竟意味着什么,福斯特却没有说透。诚然,故事里充满了时间感,正如生活在时间里流淌一样。在日常生活里,你和我都可以轻描淡写地否认时间的存在,而潇洒地按各自的意志行事。但小说家在小说中完全不谈时间是不可能的,他必须顺着时间的链条摸索下去,以免被读者视为不可理喻。这似乎成了小说家的宿命,正如生活中的你和我无法阻止眼角皱纹的出现,无力面对死亡女神轻松地展颜一笑,说一声:“来吧,我们共饮一杯生命之酒。”
时间吞噬了永恒,这便是福斯特的真正恐惧所在。它意味着故事变成了一次性针头,在注射给人短暂的幻觉后,便被扔进了历史的废品箱。那曾经活蹦乱跳的生命(人物),那苦心经营的真实,就这样被时间之手轻易、干脆地抹杀,犹如风过水面,了无痕迹。
由此可见,福斯特力主小说挣脱时间的桎梏,正是为了保住真实,求得永恒。他甚至以天才的直感告诉我们,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像《战争与和平》,“主宰它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空间”是一个很感性的词,福斯特把它作为一个和时间对立的概念提了出来,他说,“空间”不同于“地域”,“空间”能给人以伟大乐章般的恢弘、永恒之感。时间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对“空间”不再适用,“空间”的永恒即是对时间的遗忘与超越。
尤凤伟在他的小说叙述里,显然和时间达成了某种妥协。他从来没想过要挣脱时间的锁链,像爱米莉·勃朗特那样在《呼啸山庄》里试图将时钟藏起来,在尤凤伟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有点故弄玄虚。既然在生活里都无法消灭时间,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家又为何要在小说中鄙弃时间呢?这无异于意味着对现实主义的背叛。鉴于此,尤凤伟几乎是心甘情愿地将故事的小船划进了时间的流水。《中国一九五七》一开头,便是身陷囹圄的周文祥对时间的追溯,他绞尽脑汁和遗忘做着搏斗,“五月十四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八日这三天都干了些什么?”一句冰冷的问讯让人想起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其中也有对遗忘痛苦的描述,那干净彻底、撕心裂肺的遗忘化为生活的本真状态,从而具有了形而上的悲剧意义。而周文祥的遗忘只是尤凤伟的一种叙述策略,遗忘不是记忆的反面,而恰恰是记忆的一种形式。无论如何,周文祥的遗忘将回到现实。让事件与时间重新勾连,才是尤凤伟的真正目的。这一点,在中篇小说《合欢》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公元一九四三年秋,夏庄财主夏世杰一鸣惊人,从龙泉汤集上讨回个小女子做了偏房。
是个便于记忆的日子,公元一九四七年元旦,夏世杰的婚姻组合在这一天解体。
同样是个便于记忆的日子:一九四八年正月十五。夏世杰与吕月在夏发子的东炕上双双死去。
这是《合欢》里三个关键的承上启下的句子。可以看出,作家的构思顺着时间游动。所有的事件,只有在时间的坐标轴上定位后才能予以表述;所有的意义,只有在时间背景的衬托、支撑下才能凸现。所谓的永恒,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也只能在时间的磁场里才能驻足、停留。
这便是尤凤伟与时间达成的妥协。在他所有的故事背后,都矗立着一座威严的大钟,时时刻刻都能听到那不紧不慢的、清晰的滴答声。它制约着故事的节奏,甚至牵制着作家的想像。仍旧以《合欢》为例,夏世杰在土改里被流氓夏发子分走了情投意合的小老婆吕月,自此便丢了魂魄一般,朝思暮想,痛不欲生。后来夏发子应征入伍,废了腿。当他确信自家已面临断炊之危同时又确信不会很快再有第二次土改给他送来“果实”时,便允许夏世杰和吕月相会,条件是每次来,夏世杰都必须背一升粮食。于是小说进入了最扣人心弦的部分:
真实的情况和嫖妓差不多,进门后首先交割嫖资,他(夏世杰)将粮食背进夏发子的住屋,放在炕上,让他验看。夏发子是极其苛刻的,每回都挑剔不止,不是嫌粮食成色不足,就是嫌粮食晒得不干。他验证般将一粒粮食投进口中咀嚼,一边咀嚼一边骂骂唧唧……过秤的过程同样也不消停……夏发子不急不慢,眼珠子在秤杆上来来回回地滑动,如同在看着一本大书。他不说行了,夏世杰就得永久地提着。这个漫长的过程对夏世杰无疑是一种折磨,可他仍然默默地忍受着。吃苦在先享乐在后,这是中国人信奉的一句真理,而夏世杰明白此时此刻他也正在为此身体力行。过完了秤,将粮食倒进屋角的缸中,苦就算吃到头了……于是夏世杰松口气,拖着业已疲惫的身子去到对面屋与等在那儿的吕月相会。相会的情景自不言而喻,俩人搂抱一起,边哭泣边诉说边干那桩事,可谓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似乎只在一瞬,便到了夏世杰该走的时辰,依依分手时夏世杰总说:等着我,明天我还来。吕月也总是含泪点头。当初嫁他时她将他视为俊杰,现在看俊杰倒未必是,而说他是情种倒是受之无愧的。
这是一幕惊心动魄的人间悲剧。尤凤伟对夏发子的动作描述不可不谓之活灵活现,可笔触一到夏世杰、吕月,情况便发生了逆转。原本预计会有一场精彩、揪心的心理描写,可尤凤伟突然变得惜墨如金,仅用“默默地忍受”、“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便将那千折百转、千头万绪、犹如地下奔突的炽热岩浆般的痛苦一笔带过。在尤凤伟的叙述里,痛苦居然变得如此透明,如此清晰,如此简单,如此流畅。尤凤伟作为小说家的激情哪里去了?为什么他在小说里总是竭力回避心理描写?为什么他的想像可以编出如此多彩的故事,可以游刃有余地添加情节,而一旦面临心灵的深渊,就望而却步了呢?这似乎只能从故事背后的钟声里寻找答案。
“滴滴答答”的钟声提醒尤凤伟,故事要向前推进了。绝不能让时间陷进心灵的沼泽,像普鲁斯特做的那样——明明几秒钟的念头,却能洋洋洒洒写上几十页。结果心灵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磁铁,将万劫不复的时针凝固在小说家所期望的某一点上。于是,一秒钟被无限地放大,时间那坚硬的秩序也悄然解体,它就像一个冷美人,最终受到普鲁斯特那敏感、丰富的心灵的诱惑,在普鲁斯特念头的拥抱、亲吻下,昏昏睡去。与此同时,心灵的空间弥漫、荡漾开来,在普鲁斯特那看似杂乱的叙述中,一个混沌、永恒的世界浮现了……
让时间接受心灵的摆布,这无疑是小说家最勇敢、也最具刺激的冒险,但弄不好的话,小说和人都变得神经兮兮的,文本也极易失去控制。尤凤伟是一个稳重的作家,很有大局观。他和时间的约定里,头一条便清晰地指明了时间对于心灵的权威性。在《泥鳅》里,时间告诉尤凤伟,该让国瑞回来取冥币了。尤凤伟便安排国瑞拦下一辆出租车,没怎么犹豫,也没费什么大的周折便赶回公司。接下来,是国瑞被捕……情节一环扣一环,时间已经给故事定好了节奏,甚至连故事的结局也设置好了。
于是,尤凤伟以和时间的妥协换来了故事的紧凑、圆融,绝不会出现因大段的心理描写而造成的故事的支离破碎,情节的旁逸斜出,整个故事脉络清晰,一贯到底。结局就站在看得见的远方,信心十足地静候着与所有情节汇合的那一刻。与时间妥协还给尤凤伟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在结构上省了心(这在他的中短篇里体现得尤为充分)。他无须绞尽脑汁地在结构上追新求异,时间的链形结构已潜在地撑起了故事的主干,尽管老套了些,但实在、稳妥。尤凤伟只需在上面添加情节的枝叶,故事便丰满、鲜活、摇曳多姿了。
对此,尤凤伟亦付出了代价:他的小说丧失了“空间”的永恒。国瑞永远不能走出故事的森林,来到我们中间;他只是做了一个悲凉的手势,却永远无法将手伸向我们。而我们刚想和他握手,时间之流已无情地把他卷向了远方。
现实主义的“黑洞”——泯灭个性的真实
《泥鳅》无疑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真实是现实主义的要求,就欣赏而言,与读者是一拍即合的,而对于评论却是一种压迫。在真实的沙滩上,评论者那一向自信、坚定的步伐变得踌躇了。面对《泥鳅》,人物的鲜活、主题的深刻是无可否认的——这已经将现实主义的最高褒奖稳操于手了——但直觉却从反面提出了一个问题:尤凤伟没有写出来的是什么?
这仿佛是一个不大讲道理的、故意挑刺的问题,但事实的感觉的确如此:总觉得不“过瘾”,作品在动人的力度上还差了些。尤凤伟肯定遗漏了什么。
这似乎只能从那不容置疑的真实、从尤凤伟坚守的现实主义本身来寻找答案。
巴尔扎克是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亨利·詹姆斯在评论他时曾说:
巴尔扎克的厄运就在于缺少一扇供他秘密出入的门……简而言之,他所缺少的就是魅力。
他的放荡不羁的想像本来会深深地影响、或者说肯定会深深影响他的写作原则,但它却不断被一个完全相反的原则所打乱,这就是那个认真的探索者的原则,要查究出一个有用的结果的探究者的原则。
亨利·詹姆斯的评论有一种感性的锐利,他以“缺少一扇供他秘密出入的门”来表达对巴尔扎克那庞大得让人叹为观止的真实世界的困惑。“厄运”一词的背后掩盖着他对巴氏的仰慕与钦佩,因为只有连天才也无法克服的缺陷才配称之为“厄运”。这种“厄运”是与身俱来的,是无法抵御、无从超越的,它与其说是巴尔扎克的“白璧之瑕”,不如说是现实主义的天生不足。
从它诞生的那天起,现实主义就开始不断地攫取、吞咽真实,小至个人的行为、心理,大至人生,统统来者不拒,连浩荡的“人间喜剧”也一口吞下。它的胃口越来越大,消化能力也越来越强,让人联想起以吞噬天体来造就、延续自身的宇宙黑洞。原先作为一种朴素的创作理念的现实主义最终异化成了一种强大的势力,它所向披靡,甚至于连它的造物主——作家的灵魂也被它控制、操纵了。这便是亨利·詹姆斯所讲的巴尔扎克的“厄运”,狭隘的真实原则遏制了巴尔扎克“放荡不羁的想像”,现实主义的“黑洞”吞没了他原本更为丰富、更为立体的人格“魅力”。
对此,福克纳是这么说的:
故事叙述的是时间生活,但小说呢——如果是好小说——则同时要包含价值生活。
作者的人格——如果有的话,是由一些更高的面,如作者对生命的评价等来表达的,而故事在这个特殊方面充其量只能把我们由读者转变为听者。
就在现实主义拿着真实到处炫耀时,它忘记了真实并不等同于艺术,严谨的真实可以成为点燃艺术之火的氧气,而密不透风的真实的堆积亦能窒息艺术的灵光。呼唤“秘密出入的门”,即是对现实主义的真实肆虐的反抗。艺术不仅是呈现,还需要隐藏;不仅是攫取,还需要内敛,需要“蓝田日暖玉生烟”式的模糊。只有在模糊的滋养下,艺术才能永远地娇嫩如昔;只有在模糊的包容下,作者的人格魅力才会从真实的坚冰下探出头,我们才能在作品中听到作者的“声音”。换言之,模糊切实地为作家开启了一扇“秘密出入的门”。
显然,尤凤伟和巴尔扎克一样,没有这扇归属于自己的“自由出入的门”,他甚至不曾想过去寻找。他在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时,曾说:“写一部作品,要以理性认识它,感性去写它。”这明显有着主题先行的味道。作家创作的出发点是理性(这是现实主义的真实观所要求的),无论他的故事如何曲折圆满,如何扑朔迷离(如《石门夜话》),题材如何重大严肃(如《中国一九五七》),总感觉到有一轮理性的太阳当空照耀着,把一切条分缕析了。其间的沟沟坎坎、机巧灵犀显露无遗。真实化为了理性的选择,成了日光式的暴露。
尤凤伟太清楚自己要写些什么、表达什么了,对故事的套路也极为熟悉(中篇小说《诺言》的核心便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英雄救美的俗套)。他很注意叙述的节奏,起承转合处打磨得自然圆滑,这无疑是尤凤伟的优点和高明之处,但同时也构成了其作品的天生的致命弱点:缺少了世界经典作品所应有的模糊。
看得出,出于结构和叙述的需要,尤凤伟在《泥鳅》里创造了艾阳和小齐。艾阳是作家,他的作品每每在国瑞走投无路、故事要发生转折时出现,这在叙述上是一种巧妙的缓冲,有点类似于古代说书人在关键时刻的插科打诨。欲擒故纵的尤凤伟趁机在艾阳的作品里插进乡间故事、顺口溜之类的东西,不仅丰富了内容,在叙述层面亦增加了一种声音。而小齐作为艾阳作品中的人物,不但介入了国瑞的生活(他在临刑前还提到小齐),还在结尾处担当起替国瑞送冥币的使命。作品的前后呼应、衔接穿插,尤凤伟考虑得周到详尽,可谓精心算计了。
然而,正是这种“成竹在胸”式的明确,使得《泥鳅》显得不够大气,仿佛是一部纪实之作,少了点奇崛与率性。托尔斯泰当初写安娜,本来只是想写一个失贞的女人,而在写作中,安娜却跳出了托尔斯泰预先的构思,有了她独立的生命,让托氏欲罢不能,爱恨交加。这在尤凤伟身上是绝不会出现的,他的所有作品在动笔的刹那,主题、格调、结构、甚至人物形象都已安排停当。现实主义的求真原则遮蔽了尤凤伟身上所有的浪漫因子,仿佛他只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理性的人,在创作、思索。
阅读尤凤伟的小说,仿佛是进入了一个敞开明朗、阳气过旺的世界。逼视的深刻有余,却欠缺了月光般的柔和,少了月色朦胧的呵护。依据常理,太阳和月亮本是水乳交融、阴阳相依的,至少也不应构成矛盾,正如阳光越是灿烂、明媚之处,阴影越是浓重一样。太阳和月亮是如影随形的,忽略了任何一方,都会使文本单薄。阳光是裸露的真实,它代表了塑造与强求;而月色是敛藏自卫,它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文本的神秘。没有了阳光的文本,会沦为晦涩柔靡,自艾自怜;而缺少了月色,文本则失去了丰厚的基础,变得直露、浅白,真实成了不折不扣的虚构的表演,哪怕技巧再高超,最好的赞叹不过是:“虚构得不错,几乎像真的。”
凡此种种,不能责怪尤凤伟(所能表达的似乎只能是小小的遗憾),他所安身立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立场,他的责任感、使命感,乃至由此生发的反思与批判,都使他由不得暧昧、含糊。在《泥鳅》里,我们仿佛听到尤凤伟在动情地呼喊:“看看我们的农民兄弟吧,他们在城市里受苦受难,而他们也是人哪!”这内心深沉的爱使得尤凤伟不由自主地把国瑞写得纯真善良、懵懂无助(当然,仍是在真实的原则范围内),而对蔡毅江的恶却没有大肆渲染。在被逼无奈、人总要活下去的前提下,恶被淡化处理,网开一面。于是,人物形象的深入挖掘、立体描述就此中断了。
而到了尤凤伟的抗战题材和新历史小说,此类缺陷便荡然无存。它们开辟了一个道德评判的真空,一切都在人性的天平上重新衡量。《中国一九五七》中的“孝子”,其前后反差鲜明的行为使人很难用“好”、“坏”将他界定,似乎只能归属于特殊时代下“各为其主”式的悲哀与无奈。及至《生命通道》里的高田,杀人不眨眼的鬼子被赋予了人性的温情,而委曲求全、一腔正义的苏原,却以汉奸军医的身份记入历史。尤凤伟在变幻莫测的历史迁流里,塑造了一群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串联、勾勒出了一部人性史——以其鲜明的个性特点成为对简单历史之非个性的反动。
显然,尤凤伟力图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深刻、永恒、真实的人性,而这都是以他心目中完美的人性理念为参照的。在他创作构思的源头,那美好的人性已早早地、牢固地立在那里,虽然没有对其直接描述,但它就像哑巴格心中的图画,清晰而坚韧。它或全面、或局部、或以截然相反的形式体现在尤凤伟笔下的人物身上,给人感觉似乎每个人物的背后都闪烁着作者睿智的眸子,他在挖掘、比较、甄别于他的完美人性之间。这使得我们在过足了一番入木三分的“人性瘾”后,在大开眼界、始料未及的惊愕之后,蓦地有种怅然若失之感。其间的缺憾与《泥鳅》的不足是一样的——依旧是少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感。
我的阅读经验与阅读兴趣使我非常在意作品背后作者的“声音”。美国的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曾说:
小说给予作家在虚构话语和历史的边缘地带创造声音的机遇。这些边缘叙述声音既能遮蔽又能促成最咄咄逼人的虚构叙事的权威。
任何叙述者都是一个潜在的发声的“我(I)”。这一发现导致了“异故事”这个更准确的词的产生。
苏珊的“声音”一词大多局限于叙事学的文本形式范围,但在论述中又和具体的人格牵扯在一起,难分难解。无论怎样,苏珊显然认识到了作者的声音对于作品的重要性。[她启用作者型声音(authorial voice)这个术语来表示“异故事”的、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便是证明。]作者的“声音”在虚构的世界之外,但却又使文本得以存在。它是构成作品个性的重要因素,和虚构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关联。如果作者的“声音”过于外露,那么他被信赖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作品的真实度亦大打折扣,成了一厢情愿的倾吐;反之,如果作者的“声音”过于式微,作品会不知所云,真实的意义和深度将遭受最严厉的质疑。事实上,任何作品都隐含着作者的“声音”,即便是再内向、隐晦的作者,其“声音”总是在文本中趋于“到场”的。
纵观中外的经典作品,无不饱蘸着作者复杂人格的汁液。其“声音”里裹着激情,但又往往矛盾重重、含混暧昧,苦恼不知所宗,欢乐不知何为。“声音”里藏着欲罢不能、欲说还休、强颜欢笑,它与书中人物的“声音”一道,合成了一曲震撼人心的交响。正如我们在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时时感受到的那样,字里行间呼之欲出的是陀氏那歇斯底里、人格分裂、狞厉的呼喊,它构成了其作品特有的风格。相对说来,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的“声音”是极为克制的,这造成了“薛宝钗形象是美还是不美”在后世的争论。但当你看到《芙蓉女儿诔》时,你分明地听到了曹雪芹的“声音”——那优雅背后难言的酸楚与痛心。在《芙蓉女儿诔》中运用那样的溢美之辞,这在曹雪芹而言,似乎有点失控,有点踉跄,然而正是这失控、这踉跄使你怦然心动,潸然泪下。曹雪芹的“声音”显然非清醒、锐利但狭隘的理性所能涵盖,它在《红楼梦》里保留了一方永远也读不懂、猜不透,永远都既清晰、又模糊的神秘空间,使得《红楼梦》带上了曹雪芹无与伦比的个性色彩。
而在《泥鳅》里,尤凤伟的“声音”要单纯、明朗得多。我注意到,吴义勤先生在评价《泥鳅》时用了“亲历”一词,即尤凤伟的抒写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作为这些卑贱者中的一员,在‘亲历’”。你毫无理由去怀疑尤凤伟的真诚,但这种“亲历”意味着作者与书中人物立场的完全一致与贴合。于是,原本应该丰富的、充满张力和对峙的声音的“交响”变成了一咏三叹的合唱,响亮、明晰的背后却是艺术、深度上相对的底气不足。身为作家的尤凤伟丢弃了自己独立的、理应更为生动、更为复杂的人格魅力,而一味去迎合真实,强化理性,这使得《泥鳅》成了一部实在但缺乏个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