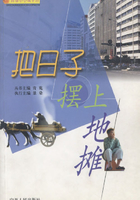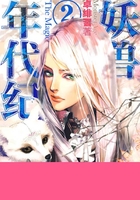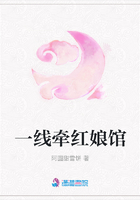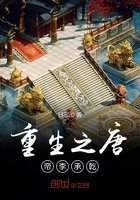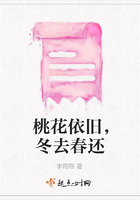他乡故人
一切都仿佛在重演。如今以难民的身份离开香港的张爱玲,一如当初从上海落魄地来到香港。
时过境迁,三年弹指便过去了。三年的时光并没有使张爱玲的境况更好一些,只是徒增年岁,皱纹乘虚而入罢了。大洋彼岸的生活并不比国内更好一些。漂泊无依几乎是张爱玲永恒的状态。
在美国,张爱玲几乎是举目无亲,唯一值得慰藉的,便是炎樱。这个也几乎是永恒的伙伴,恰巧也从日本移民到美国纽约。开始的日子,自然也还是两个人一起。然而如果生活光只是友人之间的把酒言欢,那么这样的生活是不完整的。张爱玲必须要工作,必须要创作。
为此,张爱玲与炎樱一道,去拜访了胡适先生。生活终于还是给她安排了契机的。那个素来很欣赏张爱玲的胡适先生,恰巧也在美国。事实上,他早在1949年便已只身一人前来纽约。一年后,其夫人江秀冬也来到美国,陪伴胡适。胡适与张爱玲素有交集。最早可追溯到两人的祖上。
张爱玲的爷爷张佩纶早年仕途顺利,考中进士后成为皇家教师。此时胡适的父亲胡传则还只是一介书生,因此请求张佩伦为他推荐。此后胡传仕途也是跌宕起伏。在后来的低谷时期,张佩伦仍念旧情,于危难之中伸出援手,雪中送炭。这使得胡传颇为感激。之后张佩纶落难之际,胡传也曾给他写信,并附银两作为回报之举。
此后也多有交流,甚而登门拜访。这在张佩纶的一生中并不是怎样的大事,因此也少有对后人提及。若不是张佩纶在他的《涧于日记》里记载了两人的交往,而胡传也在他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一段经过,也许胡适同张爱玲永远都只是“相逢不相识”了。而张爱玲对胡适的印象也从幼年时期就开始了。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买过《胡适文存》,后来又去买了《海上花》。张爱玲大约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坐在其父的书桌前看了《胡适文存》,后来又“破例要了四块钱”买了多卷本的《醒世姻缘传》来看。
对于《醒世姻缘转》的痴迷,从张爱玲的自述里可见一斑:“驻扎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有一部《醒世姻缘传》,马上得其所哉,一连几天看得抬不起头来。房顶上装着高射炮,成为轰炸目标,一颗颗炸弹轰然落下来,越落越近。我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
张家一家似乎都与胡适结缘。除了张爱玲与其父亲之外,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姑姑张茂渊也都爱看胡适的书。张茂渊与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早年还曾与胡适在同一个桌上打过牌。而张佩纶的侄子、张爱玲的堂伯父张志潭与胡适也有短暂的往来。
有一回,张茂渊看到报纸上登的一张胡适的照片,不记得是下飞机还是下船,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张茂渊看着笑了起来说:“胡适之这样年轻!”
1944年的她对胡适的看法是:“中国的新诗,经过胡适,经过刘半农、徐志摩,就连后来的朱湘,走的都像是绝路,用唐朝人的方式来说我们的心事,仿佛好的都已经给人说完了,用自己的话呢,不知怎么总说得不像话,真是急人的事。”
张爱玲正式与胡适有了交集,是在1954年。那年张爱玲刚写成《秧歌》,去信请胡适写书评。恰巧胡适有写日记的习惯,将此信附于其中,得以留存:适之先生:
请原谅我这样冒昧的写信来。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Scribuers出版,大概还有几个月,等印出了我再寄来请您指正。
而胡适对待学问极其认真。当时张爱玲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后辈,学问上的建树自不及他,况且那时胡适并不知道她就是张佩纶的后人,但也是认认真真地将《秧歌》看了的,回信也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巧合的是,尽管这封信在胡适的日记里已被定义为“没有留存稿”的,张爱玲也还是将此信抄录保存下来了:
张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
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
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页写的那条棉被,如175、189 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189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 ,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
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书中160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205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76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的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两人自此后多有书信上的往来。两人的书信往往都很认真、真诚。也许正因为这样,再加上文学、学术上的互相欣赏,两个差了一辈的才子才女,成就了一段“忘年交“。而那个时期,也正是胡适一生中最为暗淡的岁月。而两人的正式见面,则是这次在美国的相见。
不久之后,胡适便做了回访。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两人才知道了彼此祖辈的相识。于是关系也更亲近了一层。除了纳什之外,其实胡适的人生与张爱玲也颇多相类似之处。
两人同属吴越一带的人,一生中辗转经历上海、香港、台湾,终至美国。两人都是在上海时功成名就,也因为政治风向标的多变而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且两人的思想都是融会中西,晚年生活也都颇为凄凉,一生中都经历过多段恋情与婚姻。这样重叠了人生的两个人,碰到一起,怎能不心生感慨、惺惺相惜!然而这样的日子并不长久。从来都是这样,花无百日红的。
这年冬天,他们见了最后一面。临走时,“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三年后,胡适回国。回国后四年便去世了。那果然是他们俩最后一次的相见。而在回国后的日子里,胡适对两家人的交往也还是多有感念。1960年,胡适还曾写了一篇《张佩纶的涧于日记》,回顾了张佩纶和胡家的因缘。
而胡适对张爱玲的学术研究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张爱玲为她一生最为钟情的两部古典小说——《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所作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胡适研究白话小说工作的延续——“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
两人真正的交往就在美国这短短一段时间中,而这段交往的前世因缘,以及留给两人的回忆,却是永生不尽的。
这也是张爱玲在来到美国之后与还未遇见赖雅之前那一段空白期里,感情上唯一的慰藉吧。
异国相遇
这一团孤篷在时代的大风里被刮得晕头转向,失去方向,失去希望,只剩下苦苦的挣扎与迷茫。阳光是早已没有的了,往昔明晃晃的光只能向记忆中寻,而今只剩了漫天的大风夹起的沙尘,将整个清明的世界遮天蔽日住了,描画出了一个阴惨惨的世界。
不知不觉,来美国已是4个多月。同样是来美国不久的炎樱已是过得风生水起,而张爱玲却仍在徘徊,生活不知向何处去。连一个人生存于世上最起码的立锥之地尚且没有,更何况发展呢?作为是更加没有的了。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生活给了你场景,却给不了唯一,爱与不爱,平凡或伟大,酸苦或甜蜜,一切自在人心。与胡兰成刻苦铭心纠葛牵扯后,桑弧又如云烟般消散眼前,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张爱玲觉得自己的心在孤独中慢慢苍老,只是命运注定,爱是她的一场摆脱不掉的劫,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
早在香港时,张爱玲便已是深居简出,生活极为简单素朴,连一张写作的书桌都没有,都是坐在床上伏在一张小案子上写。大概是养成了习惯——当然,是生活的压力使然也未可知——来美国之后,张爱玲仍旧很少使用书桌,这一习惯一直维持到她晚年。
新的一年已经到来,而她原先的女子职业宿舍已不是长久之计,不能再住。张爱玲唯有另想办法以谋出路。
恰巧此时张爱玲打听到有个麦克道威尔文艺营,专门为没有能力担负起自己的生活却又有着旺盛的创作力与创作天分的文人作家提供住宿。于是张爱玲写信去取得申请,并且为她的居住期限请求延长。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建于1907年,是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道伟的遗孀玛琳·麦道伟创立的。它坐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群山之中,占地420英亩,是由40多栋大小房舍、工作室、图书馆等构成的建筑群,可谓世外桃源。文艺营的设想是,赞助有才华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暂时摆脱世俗的干扰,在一种宁静的环境下专门从事创作。
那时的她怎能想到,自己这一去,刚和胡适先生别离,却戏剧性地遇到和胡适先生同庚的赖雅,并且不到两个月就在一起了呢?
张爱玲的爱情,向来都是这样。不要去计算年龄,不要去计算时间,不要去计算值不值得,她就是义无反顾地飞蛾扑火了,没有人能拦得住。假使我们计算了那些东西,得出的结果只会更令我们困惑。
赖雅,六十五岁的绅士老人,他白衣白裤,飘逸潇洒,他高谈阔论,风趣幽默,他是未泯的孩童,他是温厚的长者,在举手投足间,一言一行中,他深深打动着这个被寂寞侵蚀行将枯萎的女子,她笑了,畅然开怀,她笑了,如飞花般灿烂。
她说:“爱情使人忘记时间,时间也使人忘记爱情。”爱情是什么,撕心裂肺,轰轰烈烈,一颦一笑只因他,爱情是什么,指尖相携,温暖相依,平淡中相濡以沫……
他们的爱情,一开始是不顾一切,然而在这“欲火燃烧”的背后,是生活烙下的印记。生活的困顿穷窘令两个无依无靠的人紧紧贴靠在一起。
生活就像是大气。平时似乎无色无味,无知无觉,但在不知不觉中,却改变了很多人的很多东西。气压太强了,那么无论是怎样的两样东西,无论他们是命中注定还是后天的外部环境使然,无论他们是否相配,无论他们是否彼此欢喜或者欢喜得有多长久,都只有仅仅依靠在一起了。并且依靠得严丝合缝,外界的力量再也无法将这两者分开。除非他们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亦或者,原先的大气压强已经减弱,减弱到她们俩可以彼此分开,再也没有必要待在一起。
除此以外,张爱玲的恋父情结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似乎天生爱与比她年长的人待在一起,这样会令她有安全感。正像《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一样:“他的母亲碧落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碧落嫁到聂家来,之后生下聂传庆,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 聂传庆明白,那就是爱——-二十多年前的,绝望的爱。二十多年后,刀子生锈了,然而还是刀。在他母亲心里的一把刀,又在他心里绞动了。”
张爱玲对于她的父亲,也正是那样。一种绝望的爱。尽管过了二十多年,刀子生锈了,却随时随地都能在心里重新绞动。更何况,即使不再绞动,心里的伤口是再也不会愈合的。
亦像是《心经》里的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恋父,但在找寻恋人的标准里,似乎总带着父亲的影子——“我一向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
当张爱玲来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时,赖雅也来到了这里。
赖雅原是德国移民后裔,年轻时就显露了耀眼的文学才华,他个性丰富多彩,知识包罗万象,处事豪放洒脱。但是由于他的社会理念和好动的个性使然,再加上生活压力造成的注意力分散,并未将自己文学的才华施展到登峰造极,并没有写出不朽的作品。
赖雅在30多岁时,衣着入时,风度翩翩,一副帅哥才子的派头。然而,到了40多岁时,人们一看他,就像一个资产阶级的对头,因为那时的他,变成了一个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赖雅本来就疾恶如仇,对被压迫的人们总怀着一种出于自然的同情心,总替美国的劳工和普通民众考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一切,当然会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不谋而合。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常常都是以社会小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为主。
而过了花甲之年的赖雅,境况却令人唏嘘。在各方面甚至包括身体都走了下坡路,文学无大建树、经济状况拮据、摔断了腿并数度中风。为了重振文学雄风,他来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
他此前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女儿。但生性奔放自由的他,很不适应婚姻的束缚,便与女权主义者的前妻解除了婚约。在这以后的岁月里,他也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友,但她们中没有一个愿意也没有本事与这个男人共结连理,直到他遇到张爱玲。
三月,一个美丽而又带有神秘气息的月份。在美丽的文学作品里,这是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万物复苏,世界正是要由单一走向五彩缤纷,由冷清渐至热闹。大地上正是要万紫千红,莺啼婉转的。这本应该是多么好的一个节日!
可是眼下,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所处的新罕布什尔州正是严寒的雪天,这与文学里的三月不仅是意向上的差别了,更是精神上的无所适从。
张爱玲此时孤身一人在这样肃杀的环境里写作。她在此之前所经历过的冬天,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寒冷。上海,香港,最冷也只是在零度左右。而这一回,冷不防便到了零下30多度了。然而在这样的时刻,她依然是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文字。
此时她正在写作的是《粉红的眼泪》,并不是什么新的作品,只不过是翻译旧作,稍加改编罢了。自从于香港写作了《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至今尚未有任何新作发表。
张爱玲的才气,已是被人世的风尘消磨殆尽了,现在的她只有靠了陈年旧作以及多年的英文与古典文学的功底来书写新的篇章。这篇章她写得吃力,我们看着也心酸。
《粉红的眼泪》正是根据她早年在上海时写就的佳作《金锁记》改编的。虽说改编时也是费尽了心力,但总还是不讨好,并没有引起怎样的反响。
其实张爱玲是有计划的。她早年还是在学堂的时候,就有过要超越林语堂的梦想。林语堂一直是她心里的“偶像”。而今,她来到美国,也正是要仿效林语堂,用英文写就佳作,想在美国的文坛有一席之地,也好赚取生活费用,使自己不至于总如此困顿。
但现实总是与理想背道而驰。她风头正盛的时候已经过了,能够超越林语堂的时候已经过了,现在的她,心中也许还怀有当年的梦想,但是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不可一世的其实已经荡然无存了。为了生计,人总要低头,尽管孤傲如张爱玲,仍不能例外。
而今的她,不但超越林语堂是毫无希望的了,就连超越当年的自己都似乎是“痴人说梦”。美国没有她的市场,英文写不出她的毕生沧桑,异国他乡唤不醒她的天才梦。
而最后与她相依为命的,除了并不怎样可靠的文字,还有并不怎样可靠的爱情——赖雅。然而无论如何,他们陪伴这张爱玲走过了人生的下半辈子,使她漂泊的一生不至于太过孤独。
她与赖雅初相识,是在3月13日。这一日两人只不过是见了一面,并无进一步的交谈。而第二日,两人只交谈了几分钟,却已是相谈甚欢的了。也许是因为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里孤独的写作生活,使久未开口说话的她在遇见赖雅时能够侃侃而谈;也许是因为生活境况同样不顺的赖雅使她没有寄人篱下的自卑,两人相顾相惜相怜,彼此明白一些东西。
说到底,是孤独将两个人牵到了一起。孤独就仿佛是一个无形的媒人,将两个人的手交叠在一起,并嘱咐彼此要互相珍惜。因为错过了这一个,双方都将无所依傍。
赖雅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且先前已有过几次中风,但并不像国内的老者已是垂垂老矣之态,相反地,他生得高大,早年的威猛随着年岁的增长演变成了和蔼,使得张爱玲较易亲近。而赖雅对于张爱玲的印象也相当不错,觉得她庄重大方。
两人在这一次谈话之后对对方都建立起了信赖与亲近之感,之后便多有接触,再之后的事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到了三月下旬,两人已开始互访工作室,开始进行亲近的走动了。4月1日那天,他们在坐在一起享受复活节。两个人不再是单个孤独的个体,而渐渐成为一个整体了。不久之后,她将《秧歌》拿给他看,他亦是不吝溢美之词的。
张爱玲同赖雅关系的进展,一如当年与胡兰成。
同样是不经意的相逢,同样是大得多的年龄,同样是以相谈甚欢为基础的进一步发展,同样是神速得令人咂舌的发展,同样是走向了婚姻的结局。
避风港湾
张爱玲与赖雅在严寒的三月相遇,他们的爱情也正像是严寒的结晶。肃杀的冬季不容许姹紫嫣红,那么,就让冰晶依偎在一起抱成团变成冬季最美的风景吧——雪时一定要下的了。不,不仅仅是要下,还要下得纷纷扬扬,翩然起舞,好叫这冬天晓得,它的肃杀压迫不了所有人。总有人会反抗,总有人会拥抱,孤独的,是这个主宰者。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走得近一些,再近一些。
他们也在走着程序。
他们不经意地相逢了。然后相识,然后相谈,然后相知——自然,彼此知道得并不彻底,然后互相试探,试探对方是止步于此,还是想有进一步的发展。然后互相依偎,互相取暖,互相依靠。最后,终于在一起了。
那时,距离他们相遇,不过才两个月。
佛说:前生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两个人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已是不易。巧合的是,命运又安排他们相遇的时候都已是经历了过半的人生,遍尝世间酸甜苦辣,遍看人间百态,都正在无边的苦海中挣扎。
在这样的时候相遇,除了紧紧地靠在一起,还能作何想呢?只有紧紧地靠在一起,才能克服人生的一切艰难险阻;只有紧紧地依靠在一起,才能在面对克服不了的艰难险阻时,还有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这时候的张爱玲与赖雅,都需要另一半的支撑,都需要给自己找寻一种继续面对人生、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念与力量。
然而当时的两人,并未为以后的地久天长做打算。两人只不过是在一起时互相取暖,共同燃烧。至于燃烧之后的灰烬,会被风刮到哪里,谁都无法可知。因此,两人都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并没有想到今后真会“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当时只是“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谁还会瞻前顾后,顾及其他呢?
宿命的是生命之谜,无人可测。
张爱玲亲自送他到车站,彼此倾诉了感情。他们具体说了什么,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是两人已经是从两个月前的素不相识到现在的互相扶持了——张爱玲尽管那时也是手头拮据、囊中羞涩,生活并不宽裕,但是临别时她还是送给赖雅一些钱,这使得赖雅深受感动。
随性之人,只求顺其自然,一个西方绅士,一个东方女子,一个流荡四方,意气风发,一个独辟一隅,沉默寡言,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一个共产党的批判者,他们不同,却又相同,他们同是文学的才子才女,拥有十足的默契,这份默契使他们能够融洽愉悦的交谈,能够在文艺营的日子里谈天说地,温柔相持。
只求同行,不求结果,她珍惜这个男人给她的平淡幸福,他亦为孤傲多才的独具韵味的东方女子所倾倒,只是她不再是为爱痴狂的少女,他仍是放荡不羁的浪子,他们仍旧默契,绝口不提婚姻,不提白头到老的誓言。
当赖雅在文艺营的期限到了,在这里的日子走向了尽头,他要离开,去纽约州北部的耶多文艺营去,爱玲没有挽留,亦不会哭泣,她仍是清冷的女子,不会再为一个男人低至尘埃里,他没有诺言,不会承诺,一次失败的婚姻和三十年的孑然放荡,他给不起,更何况江郎才尽,他自身难保。
5月14日,赖雅离开,她坚持送他,在离别的车站,他们收敛起内心的伤感,若无其事的谈论着不着边际的话题,她知赖雅的拮据,赖雅也知她的经济问题,但她仍然拿出一些钱接济,她是良善的女子,有一颗赤诚之心,为此,他感动,他惊讶,他酸涩,她是值得一生珍爱的女子,只是他已苍老至此。
火车的汽笛声轰鸣响起,他在车内,她在窗外,他望着她清冷瘦削的身体,不禁百感交集,车轮碾过,粉碎一切,轰隆隆向前开去,牵挂和不舍竟萦绕在他的心头,多少次踏上火车,多少次远去,可他第一次觉得沉重的想要哭泣。
夕阳的余晖下,她拉长的影子晃过眼前,他默默而语:“再见,别忘了来信!”
再见,他们并不曾想到会再次相见,只是上帝听到了他的呼声,命运要再次将他们连在一起,用一个生命将他们紧紧系在了一起。
离别之后,在耶多文艺营的赖雅还是会经常给张爱玲写信。信中除了互诉衷肠,也跟张爱玲说了他的打算——他盼望着10月份能重新回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
6月30日,张爱玲在文艺营也到期了,由于名额已满,她的延期申请没有通过,只得收拾行李,搬进叫做罗丝·安德逊的一个朋友纽约的家中。
纽约,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城市,那里有光鲜的浮华外表,那里有繁华的街市,有喧闹的熙来人往,有宽敞肃穆的教堂,有飞过的群群白鸽,那里也有阴暗的角落,有罪恶,有堕落,有贫穷,有饥饿,那里,是天堂,也是地狱。
那里,不是张爱玲的天堂,她站在摩天大厦之间,面无表情地听着英语的腔调,看着来来往往的白色皮肤和金色头发,恍然间,不知身在何处。她生活拮据,没有工作,亦没有钱,她缺少独立的空间,没有安静的归所,引以为傲的才情无处挥洒,寂寞和孤独,清高和冷傲,抵不过怀才不遇的心伤和繁华后的饥饿与贫穷,物资和精神,都拉扯着她的灵魂。
只是,在那里,她发现自己怀了孕,那是她与赖雅爱情的结晶,是她与赖雅曾经欢乐相伴的证据,只是她是凉薄的女子,一个孩子的力量并没有唤出潜藏的母性,惊讶过后,她恢复惯有的平静表情,写信告知了已经分离两个月之久的赖雅,没有过多言语,没有指责,也没有高兴,只是告知,她认为他有知晓的权利,仅此而已。
7月5日,赖雅收到了她的信件,那时他已经离开耶多文艺营,搬到了萨拉托卡泉镇的罗素旅馆,他坐在桌边,迫不及待地撕开查看,当看到怀孕的言语,他的心脏怦怦直跳,他激动,却又踌躇,那个可爱美好的女子,他爱她,而她有了自己的孩子,这是劫,还是幸,但这一定是命。
他坐着,忘记午后明媚的阳光,忘记咖啡浓郁的芬香,任思绪在回忆里纷飞,他的前妻吕蓓卡,他的女儿霏丝,他失败的婚姻……
1917年7月,他与吕蓓卡步入婚姻的殿堂,并很快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那时他们相亲相爱,其乐融融,都以为会快乐地携手到白头,只是生活没有想象容易,吕蓓卡是著名的女权运动家,为女权运动奔波忙碌,无暇顾及家庭温情,他是天生的浪子,不喜被婚姻束缚,在世间穿梭不停,交友看风景,终于,那些白头皓首的誓言被灰尘湮没,无人提及,他们于1926年和平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