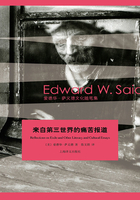文/孙仁歌
日常生活中的确拥有许多“巧合”,只是往往可遇而不可求。生活的本身,有时似乎就是活生生的“导演”。2008,在大洋彼岸,我与台湾著名诗人痖弦的相见,显然就是一个颇富于戏剧性的“巧合”。不过导演出这一巧合的“导演”,并非来自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出自生活本身的“造化”与“撮合”使然。
2008年5月,笔者应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邀请,前往温哥华出席一个涉及平民教育问题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在启程之前,意外得知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先生退休之后,就在温哥华定居。获得这一信息,于我无疑是一个惊喜,显然更加激发了我积极前往温哥华之精神系统的优势兴奋中心。
我与痖弦先生的交往,说来话长。那是十七年前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坐在收音机前的我、在一种视文学如生命的氛围中听完了安徽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一个“文学剪影”节目——《彼岸的歌——介绍台湾诗人痖弦》。不曾想,节目播完了,我的心情却像潮水一般沸腾起来,久久难以平静。痖弦其人其诗,让我受到深深的震憾!作为“逃亡的一代”诗人群体中的一个杰出代表,痖弦正是借助诗歌这种艺术形式直面现实、将自己内心深处的离愁别绪乃至某种人性的要求与灵魂的愿望传达给海峡两岸的你我他。正如《台湾新诗十家论》作者陶保玺在他的那篇《进入痖弦诗歌中的黄钟世界》中所说:“他演奏的恰恰是黄钟大吕般的乐章……读痖弦的诗作,让人深深感到在他的血管里,流动着汉魏乐府、盛唐诗韵及其意脉……”都说诗人创作是自己对自己的独白,而在痖弦的诗歌里,那种啼血般传达出来的情感已远远超越个人的狭隘性,无可置疑地进入了普遍领域,的的确确“把一个人的情绪升华为一代人的情绪,把一代人的思考浓缩在一个人的思考之中”(吴亮语)。
一曲难忘,余韵扰怀。于是,我便鸿雁传书,把这一听觉体验抑或经历及其所感所思写信告诉了痖弦先生。不料,当时还在台湾《联合报》主持文艺副刊工作的痖弦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并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他也想听一听诗在大陆的声音。这便是我与痖弦开始十七年之久神交的缘由。后来,安徽人民广播电台“文学剪影”节目制作人史辉女士应我的请求便将《彼岸的歌——介绍台湾诗人痖弦》拷入一盒磁带,以便打包寄给痖弦。然而那时两岸还没有实现三通,邮寄包裹一事由于种种不便而被迫搁浅了。数年之后,我应邀赴京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七届“海峡情”征文颁奖活动,有幸与来自台北市的女作家丘秀芷女士相识,最后委托她将一盒饱经岁月“厮磨”的磁带捎到台北交给痖弦,笔者才算了却一桩心愿。还深深记得磁带捎到台北不久,痖弦先生收到磁带并再三聆听分享了磁带之后,还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致谢,并称赞大陆播音员朗诵得太好了,他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此后,尽管我与痖弦经常保持书信往来,但始终难得一见。在他退休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们一度中断了联系。对于退休之后的痖弦先生的踪迹,一无所知。直到前往温哥华之前,才从邀请方加拿大文更中心《文化中国》华文杂志主编子夜那里得到确切消息:痖弦就住在温哥华三角洲一栋别墅里,他们还在一些文化活动中见过几次面。
于是,去温哥华见痖弦先生,便成了笔者此行的一个重要活动内容之一。从大陆看台湾,是彼岸;从东方看大洋那一边,也是彼岸,如今生活在大洋彼岸的痖弦先生,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他还有当年那种动辄激情四射的诗人情怀吗?这或许正是我急于飞往大洋彼岸希望能如期见到望痖弦先生的诱惑之所在吧。
到了温哥华之后,我就在第一时间把这一专访计划告诉了东道主子夜兄。子夜非常善解人意并相当爽快,答应一定满足我这一心愿。在应付日常事务乃至种种文字工作的间隙,一天下午,子夜兄果然兑现承诺,亲自驾车带上我以及同行的杂文家鄢烈山君一道直奔温哥华三角洲而去。
倘若没有子夜兄的亲临与导向,我们即便踅摸到三角洲,也很难很快找到痖弦先生所栖居的这栋别墅的位置及其门号。毕竟已移居温哥华多年,子夜兄对这里的人理地理乃至天南地北方方面面已相当熟悉。而且他还非常心细,把我们下午要前来造访的消息提前电话告知了痖弦先生,以免造成突然登门失礼于老人。不曾想,痖弦先生已在家中正襟恭候多时,本人亲自开门迎出并热情把我们带入客厅。经子夜兄介绍,老人与我握手时很是激动。他也不曾想到,一个与他神交多年并已经深深烙在他情感世界中的一个大陆知音,居然在度过了漫长的17年之后,在大洋彼岸与他相逢。对于17年前,我为老人鸿雁传书以及跑磁带录音并邮寄遇阻的那段往事,老人还记忆犹新。无庸讳言,对于我的到来抑或造访,老人由衷地流露出来一种欣慰与感动,而且显而易见,老人也丝毫不加以掩饰,嘴上一再说:“你来温哥华如提前告诉我,我就把你接到家里来住了。下次再来温哥华,一定住在我家里。家里有车,出入也方便。”对于老人的这般盛情,也同样在我的心里激起了层层波澜。尽管老人因“有朋自远方来”而喜上眉梢,但这突来的喜悦并不能覆盖滞留在老人眉宇之间乃至畅言笑容背后的一种苍凉与孤独,甚至是一种失落。这种直觉果然没有传递错误信号,在交谈中我们得知,两年前老人的爱妻张桥桥因肺病久养不治而撒手西去,从此老人便陷入一种深深的哀思与缅怀之中不能自拔。直到今天,一提到爱妻桥,老人的眉宇间仍然掠过一道忧伤与愁绪,语气以及神态顿时也变得不那么开怀了。是的,人生难得一知己,张桥桥对于诗人痖弦来说,具有双重意义,既是他人生长河中的忠贞伴侣,又是他诗世界乃至精神世界中的知音。无疑,在这个世界上,最懂痖弦其人其诗者,莫过于张桥桥了。可以说,张桥桥不仅熟知痖弦之弦,更能理解痖弦之弦。何谓“痖弦”?“痖弦”到底“痖”在何处?或许只有张桥桥生前深谙其道。今天研究痖弦其人其诗者固然大有人在,但比起张桥桥,可能都只能成为“猜想者”而已。然而知音一去不复还,这怎不让老人因生命中失去一份重要的支撑独怆然而泣下?
言及张桥桥的话题,使客厅里的气氛一度有些凝重。边谈边举目观望客厅,我发现墙壁一角悬挂一幅极为醒目的书法作品,内容仅有“桥园”二字。“桥园”二字让所有过目者不禁为之动容。这不单因为张桥桥生前好友董阳孜女士的书法功力不凡,造艺不俗,更重要的还是“桥园”二字的寓意让人倍感痖弦对于爱妻桥桥(痖弦称生前爱妻为桥桥)的一种依恋乃至召唤。桥桥虽然已去彼岸世界,但这里仍然还是她的家。或许在老人的情感世界里,桥桥并没有走远,还一如既往与他朝夕相处,相濡以沫,心与心依然还粘合在一起。在墙壁的另外一角,还供奉着基督教主耶稣受难图。原来,桥桥生前与夫君痖弦双双都是基督教信徒。就此而言,死对于死者和生者来说,都是一种永恒。在基督教那里,此岸世界是有限的,彼岸世界才是无限的。人一旦到了彼岸世界,一种永恒的幸福就属于他或她了。难怪,痖弦以“桥园”告慰彼岸的桥桥:爱妻生前我们是一家,爱妻死去我们还是一家。死既然是一种幸福的永恒,生者对于死者的哀思又何以久久不能解脱呢?可见。基督教精神只能是一种劝慰,而于精神也不是一种万能,即便深信不疑,但其中的局限性——死毕竟不等于生的现实、即便深信基督者也难以收到生死同一的现实效果。否则,人还依依恋生作甚?尤为让人望而难言的是放在“桥园”下端的一架沉默着的旧式钢琴,想必那是桥桥生前生命的表达者,也是痖弦生命的表达者,那就是钢琴音乐的优美旋律。人去物犹在,更平添了几分凄凉与悲哀的景象。
诗人告诉我们,桥桥19岁就得上了肺病,几经疗救都无法还她一个健康的肺功能。后来只剩下了半个肺。最后10多年都是靠吸氧气维持生命,直到64岁去世。老人说,在我的印象里,她生了一辈子的病,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选择定居温哥华,因为这里的空气质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这对于一个患有肺病的人来说,是最好最好的归宿了。桥桥来温哥华比我早几年,这栋房子也正是为了她而硬撑下来的。诗人收入毕竟比不上商人或那些明星们,我本人是退休之后才过来的,或许正因为移居温哥华,才延长了她10多年的生命,要不然,还滞留在台北,她可能还熬不到64岁。诗人说,我常常对人说,我不写作不可惜,而桥桥不写作实在是太可惜。她有写作的天赋和才情才智,23岁那年应《幼狮文学》编者之约写的那篇散文诗《花非花》,就成为《幼狮文学》同仁诸君的意外发现,他们一致认为她这篇文章与应约包括名家在内的一组文章相比,是最美最纯的一篇,是属于真正吃专业作家这碗饭的人才有可能侍弄出来的精品。然而,由于长期遭遇肺病的折磨与煎熬,她写作的天赋与才情才智终为病魔所吞噬。
也许由桥桥生与死的话题切入那天下午的“茶聊”,使那天下午的聊天话域受到了语境制约,种种开怀话题不便无限展开。那天下午聊天的关键词似乎就没有跑出“桥园”这一语境,尽管《文化中国》执行主编子夜兄和杂文家鄢烈山君也时有插话,话题涉及面倒也很广,诸如《南方都市报》李怀宇采写的《每个文人都应该是“广义的左派”》(此选题就出自痖弦之口)、痖弦作为台湾的“十大诗人”、痖弦的传奇人生、《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以及关于复兴繁体汉字的讨论等等,虽然如此,但开题与收尾的话题还是形散而神不散,还是神凝于“桥园”。言及于此,笔者以为还有必要对痖弦的生平作一点简短的交代:痖弦,本名王庆麟,1932年生于河南南阳,青年时代于大动乱中入伍并随军辗转入台,之后先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创作中心、威斯康辛大学创作与读书,并获得硕士学位。曾与洛夫等人创办并主编《创世纪》、《诗学》、《幼狮文艺》等杂志,任《联合报》副刊主编20余载。无论是写诗著书的痖弦,还是编诗编文的痖弦,都是那个时代的典范。他的诗歌创作及其审美价值前面已略作交代,而作为编辑家的痖弦,也同样美名远扬,佳话多多,他每稿必复的高尚职业行为,一起持续到他退休的那一天。至此,在他几十年的编辑生涯里,总共给岛内岛外的各方读者、作者回了多少封亲笔信,连他自己也无从计算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主持《联合报》文艺副刊期间,格外看重、青睐大陆作家乃至普通作者的稿件,由他扶持刊登的大陆作者稿件数量十分可观,甚至挤掉了许多岛内作者长期厮守的“阵地”。因为这,痖弦还吃了不少“亲共”的骂名。
那天下午的“茶聊”不仅给老人带来了些许安慰,而且也让老人借茶浇了一把心中积郁已久的块垒。知他懂他并深深爱着他的桥桥终究已离他远去,留给他的时光漫长而又孤单。如今的他,已很少写诗了,很多时间都用在了读读闲书、写写随笔、翻翻《圣经》,有时也出去应付一些实在推卸不掉的文化活动或各种讲座、报告等。在温哥华,老人还有两个女儿,并与其中一个女儿生活在一起。那天下午我们造访之时,很不凑巧,女儿等等亲属都不在身边,也没有见到佣工之类的身影,所以,沏茶、上果点都由痖弦自己亲自操持,且不厌其烦。好在老人身板还算硬朗、行动也还自如,来来往往几个回合,还显得挺开心。尤其对所上的一盘温哥华草莓格外热心,再三请我们每人都尝一尝。果然,温哥华草莓看上去跟淮南等地的国产草莓无甚差异,但吃在嘴里感觉很不一般,这是没有遭遇任何人为污染的草莓,单从清洁卫生的角度而言,堪称无价果点!
夕阳西下,暮色迫近。我们的造访也该告一段落。然而老人却盛情挽留,要留下我们晚上一块吃水饺。我们不得不以婉言而拒之。老人似乎很不过意,转身去里屋拿出来一本台湾文学经典《痖弦诗集》走到我面前,说:“你老远而来,我很感激,没有什么东西好送你,这本诗集是新出的,已剩下不多,送你一本,留个纪念吧。”接过书,感到沉甸甸的。殊不知,在我的心里,能得到这本书,比吃上10斤水饺要美得多矣!常言道:君子之交淡如水。与其说淡如水,还不如说血浓于水、书重于酒,无酒胜有酒,以书代酒亦醉人呐!
走出“桥园”,似乎才发现“桥园”。仔细观摩一番,又收获眼福。在我看来,这座房子酷似一个被无限放大乃至变形了的国际象棋子儿,被上帝随意摆在了温哥华三角洲一角,怎么看都怎么觉得自然而然,简直看不到一点人工雕琢的痕迹,它与周围的各色建筑体系园林花木乃至远山近水融为一体,彼此互不可分割。距它不远处,还有一座极富有现代气象的大桥作为烘托,同时也为它平添了几分生机。真乃“桥园”之园,园内有“人桥”,园外有“天桥”,里外相通,内外合一,天造地设者也。
我们终于离开了“桥园”。回首“桥园”,发现痖弦老人的孤影还久久滞留在那里凝望着我等已经离去的背影。这情景,没让我想起他写给桥桥的那首《给桥》,却倒让我想起了他写于民国46年1月9日的那首《秋歌——给暖暖》:
“落叶完成了最后的颤抖
荻花在湖沼的蓝眼里消失
七月的砧声远了
暖暖
雁子们也不在辽远的秋空
写她们美丽的十四行了
暖暖
马蹄留下踏残的落花
在南国小小的山径
歌人留下破碎的琴韵
在北方幽幽的寺院
秋天,秋天甚么也没留下
只留下一个暖暖
只留下一个暖暖
一切便都留下……”
俗话说,千里有缘一线牵。而我时隔十七年之后与痖弦先生在大洋彼岸相逢,也算是一种缘分吧。只是牵起这一缘分的“一线”不是生活中的凡夫俗子,而是文学,也可以说就是永远魅人的缪斯女神。
此文尾声之际,敏锐的读者或许会把这一美妙的“巧合”归功于缪斯女神,是啊,我之所以能在大洋彼岸见到神交多年的痖弦其人及其生命中最后的栖居,原来是缪斯引路、文学搭桥,生活的馈赠有时来得就是如此出乎预料呵。
作者简介:
孙仁歌,男,汉族,安徽寿县人,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系淮南师范学院中文与传媒系文艺学教授,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淮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先后发表各类文学作品130多万字,出版小说集1部、散文集各2部,在海内外获锝省级以上专业奖项20余项。近10年来在国内外各种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逾百篇,出版学术著述1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