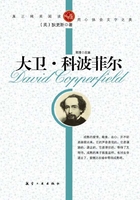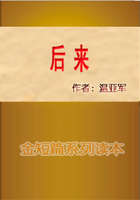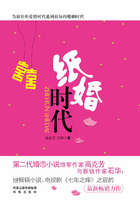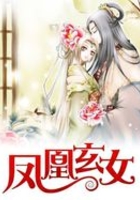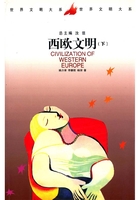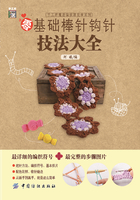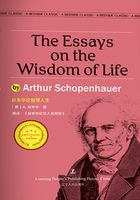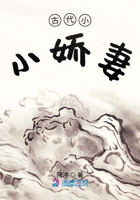第一部
Chapter 01
1
在这座城中,两层的楼房[1]仅有十来栋:除了我们家住的那栋和国防军的两座营房之外,还有几幢公共建筑。稍后修建的武装部队司令部官邸也是两层,楼里安装了吊式电梯。我们家住的那栋楼位于中央大街的马路边,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都市建筑,地地道道的公寓楼,外墙高大,门道幽深,台阶宽敞(楼道里刮着穿堂风,上午总有一些赶集者在楼梯上歇脚,他们穿着绣有图案的毛呢外套,头戴绵羊皮帽,聚在那里吃腊肉、抽烟斗、随地吐痰),每层楼都有十二扇窗户一字排开,朝向街道。我们家住一层。每套公寓都有一个狭小的阳台,夏季未至,邻居们就在阳台的铁栏杆上悬挂填满花土、种有天竺葵的长方木匣。(“让你的城市更美丽!”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人们为了普及这个高尚的理念还成立了协会,即“城市美化联合会”。)那栋楼设计得漂亮、气派,是这座城中第一幢名副其实的“摩登”建筑,墙体是用粗糙的红砖垒砌而成,建筑师在窗框外贴满了花里胡哨的石膏装饰。朝新建的公寓楼上贴所能贴的一切,这是世纪末[2]建筑师们的共同心愿。
这座城里所有的房子都被称为“家宅”,哪怕楼里住有许多户人家和付租金的房客。真正的城市几乎可以说是“隐形的”,建在隐秘的深处,藏在街头巷尾的房屋外墙背后。假若哪位旅人透过拱券式大门洞朝里面张望,会看到庭院里建有四五幢房子,孙子和玄孙们都在院里盖房,把院子挤得逼仄不堪;如果一个男孩结婚了,家人就会为他在老楼的一侧新盖一座翼楼。城市隐匿在那些庭院里。人们心怀忌妒,带着荒唐的谨慎封闭地活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户家庭都在城中某个犄角旮旯为自己搭盖了一个小小的建筑群,只有临街的外墙以一副代言人的庄重面孔应对世界。这个世纪初[3],我父母在那栋全州闻名、在当地被视为名副其实的“摩天大厦”的楼房里租下一套公寓。那是一栋高大、肃穆的公寓楼,当时这类建筑在首都[4]已盖了数百座:住满了房客,楼上悬廊环绕,中央供暖,底层有公用的洗衣间,后侧楼道上有用人专用的厕所。那个时候,这座小城的居民尚未见过这样的建筑。中央供暖系统属于现代化设施,而用人的厕所,也引发了众议。要知道许多世纪以来,尽管主人们品位高雅,但从来没人关心过用人们在哪里或去哪儿解手。设计并建造我们这栋公寓楼的“摩登”建筑师,可谓是当地的“改革先锋”。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如此泾渭分明地将主人们跟用人们共同生活的“必须之地”区分了开来。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夸口,说我家楼里有专供用人使用的厕所。事实上,出于某种羞耻感或厌恶感,用人们并不愿意光临那些被单独分隔给他们的茅厕,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去哪儿解手。估计他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去他们许多世纪以来,自创世以来常去的地方。建筑师设计时可以随心所欲,用不着为节省地皮或建材花费脑筋。楼道里,房门开向面积跟卧室差不多大的前厅,那里立着带镜子的橱柜,墙上挂着装刷子的绣花布袋和鹿角标本;门厅里很冷,冬天会冻得人浑身打颤,因为盖房时忘了在那里安装暖气;由于门厅里没有供暖设施,客人们的裘皮大衣会像冰坨一样硬邦邦地冻在衣架上。按理说,开在楼道内的房门才是从外面进屋的“正门”,可是这扇门只为贵客敞开。用人们和包括父母在内的家庭成员,平时都从开向悬廊的侧门进屋。那扇嵌有玻璃的小门开在厨房旁边,这里没装门铃,所以来人要敲厨房的窗户。家里人的朋友们大多也是从这扇小门进屋来。“正门”和挂有鹿角的前厅,一年到头也只使用两三次,在我父亲[5]的命名日,还有化装舞会的那天晚上。有一次,我央求母亲,请她允许我在一个并非周末的寻常日子里扬扬自得地独自穿过通向楼道的前厅走进家里,作为送给自己的一件生日礼物,那种感觉,简直像荣获特殊的恩赐。
庭院是矩形的,面积很大,中央竖着一个掸灰尘用的立架,看上去像一个可供多人使用的晾衣架;院子里还有一眼圆口的水井,借助电力将井水泵出,然后输送到住户家里。在当时,城里人还没见过水管子。每天拂晓和黄昏时刻,楼长的妻子都会来到井边,开动小型发电机,一直泵到安装于二楼房檐下的排水管里有一道涓细的水柱流到庭院,表明位置最高的水罐里也已经注满了饮用水。那个场面格外壮观,特别是在日落时分,楼里所有那些不会因围观而有损尊严的人都聚在一起,主要是孩子们和用人们。那时候,在城里大多数的住房里,电灯都已经相当普遍;电灯泡和奥尔牌煤气灯交替照明。但是,也有不少地方仍然点煤油灯。我奶奶直到去世那天,始终用一盏煤油吊灯照明。在我高中毕业那年,父母将我送到相邻城市的一所学校走读,寄宿在一位唱诗班的声乐教师家里,我在煤油灯昏黄的光亮下学习了一年,也玩了一年的“二十一点”[6];说老实话,那种居住环境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大合适,都会为自己迫不得已屈身在如此落后的地方而感到自尊心受伤。在童年时代,我们都为自己家装有电灯而感到自豪,但是,只要家里没有客人,我们就会在吃晚饭时点上光线柔和、奶油色泽的煤气灯。在我们家里,总是弥散着一股煤气味。后来,不知哪个聪明人发明了一种相当安全的煤气点火器,在灯丝上方装上一块铂金片。充煤气时,铂金片开始微微抖动,炽热发光,并自动点着易燃物。我父亲热衷于科学技术类的新生事物,他是我们城里第一批在煤气吊灯上安装这种安全装置的人之一。总而言之,我们虽然有了电灯,可仍旧使用煤油灯照明,特别是那些用人们,特别是在厨房里;在楼道内,楼长也点煤油灯。人们虽为电灯惊叹,但是对它并不很信赖。
中央供暖系统与其说供暖,不如说在制造稀里哗啦的噪声。我母亲不相信蒸汽的神效,以至于在孩子们的房间里砌了一个瓷砖壁炉。世纪初的所有奇迹,在彼时彼刻只是加重了人们的生活负担。发明者从我们受过的洋罪里吸取经验。几十年后,全世界都因电灯、煤气和马达而充满喧嚣,嘶嘶作响;不过,在我的童年时代,发明者仍在摸爬滚打,他们的发明还远不完善,应用起来问题很多,让勇敢的革新者和虔诚的信徒们疲惫不堪,头疼不已。电灯忽明忽暗,只能发出昏黄的光线;蒸汽暖气不是在刺骨的严冬里突然罢工,就是运转失控,房间里充满潮湿的寒气,因此我们经常生病。按理说,人们应该“赶超时代”,但我姨妈却不以为然,她不乐意“赶超时代”,继续在白色的瓷砖壁炉里添柴生火。我们则丢下现代化的蒸汽式暖气,跑到她家取暖,享受在炉膛内闷烧的榉木发出的温和、幽香的滚滚热浪。
劲风吹过宽敞的庭院,总是发出怒吼和呼啸,因为庭院的北边无遮无挡,朝向环抱城市、即使夏季也白雪皑皑的巍峨山脉。根据建筑师的设计,在庭院两侧,与二楼外墙相连的是一楼的侧翼;在庭院尽头还盖了一排相当漂亮的小平房,相当于一套“两居室住宅”,楼长一家曾在那儿住过。这一切都使得这栋楼向远处延伸,占地面积相当大。估计建筑师本人不太相信这栋楼能够住满人家,所以没在庭院里修建更高的楼层。那栋楼可以说是一份新时代的宣言,是对努力攀升、拼命建设、勤奋经营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一曲颂歌。那是城里第一栋不是为让居民们在熟悉的高墙内消磨一生而建的住房——据我所知,世纪初曾在那里居住过的老房客们,如今没有一位还住在那儿。那是一栋住满房客的公寓楼。家族史悠久的贵族人家,都不愿在这样的楼里购买住宅,甚至蔑视楼里那些刚搬进来、没有生存土壤的居民们。
2
我的父亲也这样认为,有身份的人不应该付房租,不应该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因此,他为了能让我们尽快搬进自己的家而不遗余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花了足足有十五个春秋。然而有一天,当我终于跨进“自己家”时,只是作为一位回家探亲的大学生,那栋流光溢彩、宽敞得浪费的建筑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公寓楼里度过的。我一想到“家”这个词,眼前就会浮现出中央大街路边的房子、宽阔的庭院、带铁栏杆的狭长走廊、掸灰用的高大木架,以及装有电泵的水井。在我看来,那是一栋阴郁沉闷、杂乱无章的房子。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怎么被建在那儿的。居民之间缺少友情的维系,他们甚至连邻居都算不上。住在那栋楼里的人都有自己世袭的身份,论阶层,分宗派。住在老楼里和平房内的人家,不管是仇敌还是朋友,肯定都是属于难以相容的那类人。
楼里住了两户犹太人家:一户是所谓的“改革派”或“进步派”[7],家境富裕、见过世面、已经市民化了的犹太家庭,他们租下了二层临街的整排房子,活得相当封闭、傲慢,从不跟楼里人来往;住在庭院后侧底层的是一户族亲众多、信奉“东正派”[8]的犹太家庭,他们家境困窘,并以特殊的方式迅速繁衍,总有更新的亲戚和新生儿出现,全家人挤在庭院后侧三个昏暗的房间里。有的时候,比如逢年过节,那里会挤满亲朋好友,嘈杂喧嚣,匆促忙乱,仿佛与会者准备做出什么重大的决定。那些“穷犹太人”大多是加利西亚人打扮,恪守教规。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很穷,但不管怎样,楼里信奉天主教的邻居们对这家人的好感,远远超过对那户封闭、富有的“改革派”人家的好感。有一次,住在底层的“穷犹太人”家里,有人率先剪掉了传统发型,换上普通人装束,脱下长袍,摘掉礼帽,剪短头发,刮净胡须,穿上流行时装。没过多久,大多数家庭成员纷纷效仿,摇身蜕变。孩子们改上市民学校,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报名上中学。十到十五年后,身穿长袍的犹太人不仅在我们楼里销声匿迹,就连在城里也非常少见。在我们楼里住过许多孩子,但我已经不能逐一记起。跟楼上颐指气使的“改革派”家庭相比,楼下这家“穷犹太人”跟基督徒的邻居们相处得更为融洽,更为友好。楼里人用庇护的口吻谈论他们,甚至有点夸大其辞,称他们为“我们的犹太人”,夸他们是“非常勇敢、正派的人”。我们颇为自豪地对外宣布:在我们那栋高大、摩登的公寓楼里不仅住有犹太人,而且住的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有资格住在那儿。二楼那家贵族气派的犹太人我们很少碰见,他们活得潇洒自在,经常外出旅游,他们的孩子们在天主教中学里念书,女主人是一位消瘦、忧郁、患有心脏病的女士,能弹一手好听的钢琴曲,她的衣服都是在城里找裁缝定做的。毫无疑问,楼里的市民和小市民家庭的妇人们都忌妒她。那位富婆的穿着总是很扎眼,招人嫉恨;就连我都觉得她那样打扮既不礼貌,也不检点。楼上这家邻居“不管怎么说仍旧是犹太人”,他们活得过于浮华,过于奢侈,比方说,那位富婆比我母亲打扮得更为优雅得体,弹钢琴和乘轿车也更加频繁。“什么都应该有所节制。”我在心里这样暗想。我们跟东正派的那家犹太人和孩子们可以更好地沟通和相互理解。他们也不必因为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不必因为保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着装风格、节庆风俗和古怪混杂的方言土语,不必因为将德语、意第绪语、匈牙利语的词汇大杂烩而表现出刻意的谦卑;包括他们自愿保持并且强调的外族性在内,让我们更多地感到他们只是一个具有异邦情调的部落而已。我们甚至还会同情他们,就像所有富于仁慈之心的基督徒那样,觉得自己应该庇护这种无依无靠的外乡人。我母亲有时会送一些瓶装的水果罐头给楼下那位一到秋天就坐月子的年长妇人,而在复活节时,那家犹太人则将薄饼[9]包在干干净净的白布巾里作为礼物送上楼来,我们彬彬有礼地接过来道谢,饶有兴味地打开布包观看,不过我想,家里没有谁会吃它的,就连用人们也不会吃。我们同情并且接受这一家人,但是从某种形式上讲,这种态度就像对那些经过驯服后的黑人。我母亲有时跟他们搭讪,当然只是在大扫除时,她站在楼上朝楼下喊几句友善的寒暄话;那位憔悴不堪、头戴假发、永远在喂奶的妇人则平静地应和:“是啊,是啊,尊贵的夫人。”我不认为母亲这样寒暄是想让那位可怜的犹太妇人意识到“社会差别”;而且她也完全没有必要那样做。这家人对这种差别心知肚明,住在底层的犹太人也从没想过要巴结我们;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家人对于社会差别的谨慎小心,跟天主教家庭没什么两样,的确,他们或许更加神经过敏,他们跟我们所做的一样,以自己古怪的方式高傲而矜持地回避各种可能导致大家彼此亲近的机会。总的来说,楼里的住户们都很同情这家穷犹太人。我们怀着善意的默许,关注他们的节庆和非同寻常的习俗。毫无疑问,改革派家庭已不再按犹太人的节庆旧俗在庭院里搭帐篷,他们连犹太教堂都很少去。有一次我父亲甚感吃惊、略带愤慨地讲述说,他跟楼上那家颐指气使的犹太人一起乘火车旅行,那家人居然在车厢里吃包在棉花里的鲜葡萄,要知道那是在三月底!我们整个晚上都惊诧不已、愤懑不平地谈论此事,尤其是我母亲,她为这种“不当行径”倍感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