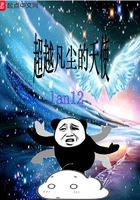一
父亲走了好久之后,母亲才和我说起她,婉西,那个叶片般的女孩儿。母亲说,你见过她的,在你父亲的葬礼上。
我父亲的葬礼上?我说,并没往心里去。
但我很快发现了母亲的异样。母亲与我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因为说话,她下意识侧着身;因为紧张或者别的什么,她坐得很虚,半边屁股挂在沙发上,另一半则悬着,胸口的事胀起来,一直撑到了嗓子眼,让她的脖子伸上去,仿佛整个人挂在半空。而她的眼睛——母亲的眼睛,曾经就像小河里的鹅卵石一样,亮晶晶晃悠悠的,如今已如两口枯井,石头还在,只是少了水分——母亲枯井般的眼睛扑闪着,似在躲避我的目光,那样子,仿佛任何一点光亮,都能将她刺破。
母亲的话已经满得憋不住,却又很难说出来。
我顿时有些在意了。
但我仍然没有任何印象。父亲的葬礼上,他的徒弟和学生确实不少,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认识的那几个,我们差不多一起长大,不用看,就是单听听他们的脚步声,闻闻他们走过来时空气震荡的气浪,我就能辨出谁是谁;不认识的,那都是我长大工作之后,父亲的工作,再没能上我的心。
母亲只好往下说。
父亲走后,母亲老是说起他,就像用这种方式,她便可以继续着他们的夫妻生活。只有说起父亲,用嗓子发出声音,用舌尖咬住父亲的名字,她才感觉父亲活了,不光她看得见,听的人也看得见。父亲还穿着那件长风衣,黑礼帽,脖子上的围巾像一场初雪,裤腿上的折痕刀锋一般。父亲瘦削的身体也像一把尖刀,插在母亲的眼前,既让她觉得安全,又让她倍感危险。
否则的话,哪怕是把他装在心里,母亲也感觉不踏实,抓不住,无声无息,随时都可能溜掉——就像那天早上,父亲看一眼她,不说话,走了。
后来母亲不光跟我说,也跟婉西说。否则那许多的事,母亲是压根儿弄不明白的;那许多晦涩而隐秘的感觉,婉西也不会讲出来。
那天,母亲说,要不是那天下午,你父亲根本就不会走。母亲的话带着已经稀释掉的怨尤。
二
那天下午,父亲照常去给婉西“念戏”。念戏是父亲所在的川剧圈子里的行话,实为“捋台词,练唱腔”,一句话,就是人坐在那里,将整个戏过一遍。在父亲工作的那个川剧团,父亲的角色有些特殊:司鼓。司鼓一职许多人未必能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在每次由剧团美工用油彩画出来的海报上,有主要演员又特别是女主角的画像,然后就是导演和司鼓的名字。司鼓一般都排在导演的后面,但作用未必就比导演小。这么说吧,如果把舞台比作战场,那导演和司鼓都是战场上的指挥官。他们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导演主外司鼓主内。导演负责表演,司鼓掌控节奏。导演着力的是观众的视觉感受而司鼓操心的是观众的听觉效果——轻重缓急、浓墨重彩或者轻描淡写,全出在司鼓手上。如果我们做个实验,把司鼓负责的那一摊子都关了,把锣鼓唢呐胡琴三弦什么的都撤下,那舞台上的戏就成哑剧了,没有人看得懂它在说什么;但如果把演员撤下把幕布关上,就让锣鼓和音乐漫天飞,你大不了闭上眼睛,照样还可以听上一会儿。
这么一说,你大体也就明白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鼓并不比导演地位低,甚至比导演更加“位高权重”。事实也确实如此。演出时,你已经看不见导演,可你只要往舞台内侧稍微看看,在舞台右侧,有一个圆桌大小的小台子,那是专为司鼓而设。就在内台与外台的临界点上,再迈出去哪怕一毫米,就是舞台了。司鼓的宝座设在如此敏感的部位,为什么?就为了高瞻远瞩统领全局。锣鼓一响,幕布一经拉开,这台上台下,台前台后,演员音乐锣鼓,就都归司鼓指挥。
但父亲的主要职责,是听觉,是节奏。因此父亲有个理论,学戏的人,唱念做打,唱排在第一,唱功是学戏人的第一功夫。他还固执地说过,你只要唱功好了,你往那儿一站,吼上那么一嗓子,立马就把人的心吊起来,把人的听觉视觉、五脏六腑都吸了去,你就像一块磁铁,而观众就是那些铁末子,他不跟着你跑都不行。
由此父亲得出结论,人的听觉比视觉重要多了,也可靠多了。眼睛就常常欺骗你,可耳朵不。眼睛可以把白看成黑把驴认成马,可耳朵不,耳朵一是一二是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最具说服力:人们都畏惧瞎子的耳朵,可没见过谁害怕哑巴的眼睛的。
父亲的话主观了,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有明显的王婆卖瓜嫌疑。但有一点却是确凿的,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给人“念戏”,主要的精力都花去帮人练唱腔了。
我从小在川剧团长大,在戏园子里跑来跑去,在咿咿呀呀的声音中睡去或者醒来。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有一个印象,父亲在给人练唱腔。那自然是一出尚未上演的新戏。剧本刚发下来,角色已经敲定,只要是父亲担任司鼓,他就有义务为新戏的主要演员练唱腔。我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熟悉那些新戏的唱腔的,我也不知道父亲怎么能拿过一出新戏来,就能当老师。我只知道父亲的声音并不好听,就像我的嗓子一样有些沙哑,而那些担任主角的男演员女演员,他们都是名角儿,台柱,他们的声音从或胖或瘦、或高大或短小的身体里发出来,都像鸟叫一样动听,都像海涛一样激越,都比父亲的声音好听多了。
有时候我便悄悄想,假如,假如父亲的声音也像他们一样好听呢,那他一定不会当司鼓,那他一定去当演员了——内心里,我是巴不得父亲当演员的,最好能当名角儿。
可令我奇怪的是,那些名角儿都听我父亲的。那些名角儿,天麻麻亮就来到我们家的院子里,敲开我们家那扇天蓝色的旧木门。父亲人还没出来,只有咳嗽声出来了,在黑洞洞的屋子里一声一声,鼓一样响。母亲先搬出椅子,然后是桌子。茶由父亲亲自泡。父亲对茶的讲究决定了他必须亲力亲为。水必须翻滚,茶叶要多,盛在一只青花瓷的盖碗里,揭开碗盖,黄稠稠的一碗茶汤,上面飘几粒零星的茉莉花屑。
父亲就坐在那碗茶旁,张大了嘴,咿咿呀呀叫起来。他唱一句,那些名角儿唱一句,那感觉,就像父亲是一只领头打鸣的大公鸡,带领着他的小鸡,要把天叫破似的;那感觉,就像父亲在清理着一条淤塞的河道,父亲沙哑的嗓子就是掘进机,在别人的嗓子眼里穿行着,将那些淤泥、杂草、乱石,通通捞起来,扔出去,小河水于是欢畅地流起来。
三
不知道是我的记忆有选择,还是事实原本就是如此,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在清晨为之“念戏”的,总是女人,女演员。或许唱腔对于男演员们,好比一只巨大而沉重的煤气罐,男人们三下两下就能把它扛上楼,而女人不同,女人扛不动,只能等男人来帮她。她们云朵一般飘进我家的小院,落座在一张张凳子上,让我的眼前恍恍惚惚。那些日子,我总是被他们的咿呀之声吵醒,然后起床,吃饭,上学。我总是找出理由在门前出出进进,既想多看她几眼,又怕多看了几眼弄伤了我的自尊心。母亲倒比我坦然多了。母亲扮演着女侍从的角色,就像在戏里,她总是演丫鬟,跑龙套。然而母亲能气定神闲地为之服务,缘于她的底气。尽管有云朵般的女人坐在对面,父亲却仿佛有眼无珠,父亲的眼里只有剧本、唱腔,然后就是盖碗茶。父亲的脸白净,严厉,小眼睛要么眯缝着,要么圆睁。他眯缝着眼时,是在看戏谱,要么就像酒微醺时,摇头吟唱唱腔里最微妙的部分;他圆睁时,不用说,是对那云朵般的女人发怒,这时候,女人就如云变成了雨,泪汪汪的,还不敢随意落下。
除了“念戏”,父亲从不给女演员们任何表情,因此私下里,父亲挣下了一个印象——是个一流的司鼓,却是个死板的男人——这印象虽然欠佳却是我母亲所欢喜的。
然而父亲这般威严而尊贵的形象并没能维持多久。转眼之间,商品经济的大潮来了,这股潮水首先冲开的,竟是剧场的大门。
父亲和母亲所在的县川剧团剧场,由一座古城隍庙改就。古时候的城隍庙,看上去是拜佛之地,实际还兼做集市买卖,佛事俗事都便达。因此县城里的城隍庙,竟位于城市的最中心,好比县城人的心脏。新中国成立之后,拜佛之事废除,精神生活尚存,于是城隍庙改成剧场,由原来的旧戏班子铺底,再招进来一批年少无知的孩子,取名川剧团,旧时的戏子也就有了一个堂皇而动听的名字:文艺工作者。
我不知道戏子和文艺工作者之间,除了字面上的褒贬差异之外,究竟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父亲以为有。父亲是真心实意想当一名文艺工作者,而非戏子,为此他把一切都往这上边靠。他把工作称为事业,把他的心称为事业心,把他的司鼓行当称为艺术,把他的全部激情和心力,都用去制造舞台上的人生。但也仅限于舞台上,舞台之下,父亲就像一块燃烧殆尽的废炭一般,冷漠,刻板,了无生气。
我还记得偶尔去看父亲演出时的情景。舞台边上,那个圆桌大小的小台子,父亲称它为鼓棚子。父亲高高地坐在上面,一身便装,大冬天里,还系着厚厚的围巾。父亲苍白的脸杵在厚厚的围巾上,如一面鼓,紧绷,收缩,颤抖;而他的面前是另一面鼓,大小和颜色都与父亲的脸相似,父亲手执一根竹签样的指挥棒,挥舞,旋转,敲打,那感觉,仿佛父亲没了,他化成了鼓,鼓化成了他。
每每,父亲从鼓棚子上下来,母亲会为他端上一盆热气腾腾的水,父亲称为洗脸。可父亲洗的不是脸,是背。父亲一件一件地脱衣服,再转过身去,让母亲为他擦背。一场戏打下来,父亲的背上成了河,而河床却像被火烧过的土地,贫瘠,稀薄,流失了所有养分,母亲手里的毛巾在那贫瘠的河床上,像船那样航行着。
洗好后,父亲换上干净的衣服,坐下来。只有在这时候,父亲的脸上才有了温度,那感觉,仿佛炭燃烧之后还泛着余热。
四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父亲打定了主意要为之献身的艺术,也没能带给他任何的顺畅和安慰。父亲8岁时被家里人送进剧团,又迷迷瞪瞪爬上了鼓棚子,从那一刻起,他所见所学就是才子佳人,忠孝大义。为此他得出了一个错误的认知,以为才子佳人就是艺术,忠孝大义就是价值。没承想,转眼间,才子佳人成了牛鬼蛇神,忠孝大义让位给了阶级斗争,他也不由分说被扣上了“白钻”的帽子。演出被迫停止,一脚踏进了黑暗无边的街头。
那段疯狂的岁月,我也正在疯狂地长大,所有的心力都被懵懂和成长占据了。我并不真清楚父亲的生活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父亲又在怎样地活着。后来剧团也演戏,父亲也坐鼓棚子,但都是些革命戏样板戏,都是些不结婚的男女。父亲结了婚,因此他对那些不结婚的男女不感兴趣。有一个夜晚,父亲和母亲演出归来,我躺在床上佯装睡着,居然听见父亲又在“念戏”了——他在给母亲“念戏”。以前他从不给母亲“念戏”的。
那是父亲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听见川剧名剧——《秋江》。懵懵懂懂中,我听出了剧情的大概:一位名叫妙常的道姑,从道观里跑出来,去追赶一位书生,来到江边,书生已乘船离去。道姑心急如焚,只好恳求赶船的老艄公渡她过江。可老艄公俏皮幽默,一面帮她过江,一面故设阻力逗着她玩,最终,阻力是假,助力是真,老艄公帮道姑追上了书生,成全了两人的爱。
父亲和母亲像每一次演出归来那样,并排坐在客厅的两只单人沙发上。
昏黄的灯光下,夜深人静之时,父亲不可能像早晨在院子里“念戏”那样,四平八稳坐着,有板有眼面对戏谱,照本宣科,但父亲的“戏”都在脑子里,信手拈来就是。没有桌子隔着,没能面对着对方,父亲似乎更易于发挥,感觉中,父亲已不是在“念戏”,而是在演讲。父亲说,这才是戏剧,这才是艺术。《秋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川剧名家周企何和陈书舫演出以来,几十年经久不衰,为什么?就因为一个字,情!一个“情”字,剧情人情情趣,都有了,再加上它的舞台表演,音响效果,堪称戏曲美的经典。
父亲又放低了声音,像怕惊飞了什么似的,说:你看,就说音响和演员的表演,道姑上船的那一瞬,道姑踏上虚拟的船头,沙啦啦一阵响,敲锣边,波浪的声音,然后道姑往下一蹲,身子把船头压低了,老艄公却往上一踮,船尾翘起来了。两人这一蹲一踮,船头船尾的,沙啦啦沙啦啦的效果,把人们上船的回忆,都搅动起来了……
末了父亲还说,戏好与不好,重在一个“情”字,而不是花哨的表演。这出戏,父亲说,它的重点是表现真挚的爱情。当道姑赶到江边,见大水横阻,情人已去,难以追及,这时候道姑的内心,那种怅惘,那种牵挂和焦急,怎么才能表现出来呢?因此,表演上,重点就在这里,难度也在这里。而道姑对于船身颠簸的惊骇表演,虽属必要,却不是主要的一面……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听见母亲说过成形的话,只听见她像应声虫一般,嗯嗯啊啊;那天晚上,虽说我看不见,但我始终相信那天乃至后来的许多晚上,父亲不光在家里“念戏”,还比画;父亲不光自己比画,还拉着母亲一起比画。事实也确实如此,那段疯狂的岁月结束之后,古装戏重新上演了,母亲一改以前沉默的面目,竟像变戏法般,演起了经典传统剧目:《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