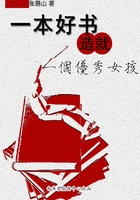6544
「哈囉!」
那一年的春天早晨,我獨自一個人坐在西雅圖中央社區學院的長廊上發呆。因為想事情想得太入神,以至於那個人叫我的時候,一開始我並沒有聽見。
「哈囉!」叫我的人很有耐性地再次叫了一聲。「Excuse me,請問……」
我的思緒在那一瞬間回到地球上來,這才有點狼狽地回過神來。
說話的是一個個頭高高的東方女孩,頭髮挺短,白淨清秀的小小臉蛋,漂亮的大眼睛在金邊眼鏡背後閃著沈靜的光采。
「哈囉!」我有點楞楞地這樣說道,因為在這個學校裏雖然東方女孩不能算少,可是真正像眼前這個這麼亮麗的倒是從來沒見過,而見到美女就手足失措的想來我不會是第一個,也絕對不是最後一個。「有……有什麼可以效勞的?」
當時,我才剛到美國不到幾個月,說的是一口制式的彆腳英文。而會坐在學校的長廊上發呆是因為學校在農曆的春節有個「中國節慶」的活動,校方安排了一個幫美國同學取中國名字的攤位讓我看著。
漂亮女孩笑了。可怕的是,連笑容也有著一口白牙式的完美。那是一種會讓男生溶化的笑容吧!首先,眼角像水紋一樣先瞇起來,抿起嘴角,再燦爛地露出潔白的牙齒微笑。
「你是臺灣來的吧?」她改口用標準的中文這樣說道。在這之前,她說的也是一口流利正確的英文。「我早上上第一節課經過就看到你了,所以過來看看。」
她開朗地把滿手的課本挪到左手,伸出右手。
「很高興認識你,我的名字叫做……」她說了一個在春天的微風裏很容易就遺忘的學名。我也伸出手,和她握了握。「可是,我比較喜歡我的朋友叫我蚊子。」
那就是我第一次見到蚊子的情景。那一年,我們都相當的年輕,就好像當年新出廠的白色本田波利露V6跑車引擎一般的年輕。也因為如此,在命名攤位後面坐了一個下午,兩個人就已經變成彷彿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蚊子是來自臺灣的小留學生,11歲到美國,在美國唸中學、高中,現在在社區學院拿大二課程,準備夏天轉進華盛頓大學。
「你怎麼會在這裏擺這樣的攤位呢?」她很好奇的這樣問我。「幫美國人取中國名字,怎麼取?」
通常,是這樣子的。我有一搭沒一搭的告訴她。來取中國名字的每個人只收象徵性的25分錢,只要告訴我他們的英文名字,我照發音給一個中文名,用毛筆寫在紅紙上。再用一張白紙寫上每一個中文字的涵義。就是這樣簡單的生意,取名字的過程、看美國人煞有介事地唸自己的中文名字、抓著紅紙頭問東問西也非常有趣,更棒的是一天下來還會有上百元美金的進賬,通常學校也會把這樣的收入全數給學生。可是,這樣簡單輕鬆的東西聽說前幾年還有人作弄美國人,取了「肚子痛」、「神經病」等不雅名字,過後還自鳴得意地在人前人後誇耀,當成是一個笑話來講。
「就是這樣,」我一邊幫一個叫「Linda Sharpe」的小老太太取了林夏葡的名字,小老太太可愛地瞇著眼說回家要把紅紙貼在玻璃窗上。「真不懂得那些人在想些什麼,如果有一天被作弄的人知道了,不會很生氣嗎?不會從此就很討厭中國人嗎?」
蚊子用她冷靜充滿智慧的眼睛看我。
「你剛來還不曉得。這種聰明的中國人你以後還會遇到更多,看久了,也就會習慣了。」
而日後幾年的實際狀況印證下,蚊子的話果然沒有錯,而且,連一次例外也沒有。
不過,那一年我們真的都非常的年輕,這種黏膩不快的話題永遠不會持續太久。前面不是說過我們就像是當年新出廠的跑車引擎一樣的年輕嗎?時光隨著話題的轉變而流逝,後來,我們還發現我們並不只是同年出廠的新車引擎那麼簡單,事實上,我們還是一雙非常巧合的雙子引擎。
「喂!所以,」蚊子在言談中偶然問起,因為一開始自我介紹時就知道我們兩個人同年。「你是哪一個月生的呢?我得知道我是姊姊還是妹妹呀!」
我笑笑,對她說了月份。
「不會吧?」她睜著大眼說道。「怎麼可能這麼巧呢?」
我想,那大概就是說,我們乃是同一年,又同一個月出生的意思。
「然後,」蚊子露出很詭異的調皮表情。「請不要告訴我你是24號的生日。」
只可惜,天底下最不可能發生的事十有八九就發生在這樣的場面。我在八七年的秋天從六千哩外的臺灣來到異國的西雅圖,離家近萬里,生命的軌跡幾劃過四分之一的地球,卻在這樣一個春天午後遇見一個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孩。
確定了雙方都不是在鬼扯打屁之後,蚊子還拿了我的駕駛執照以茲查證。於是乎,那一個中國年我們就在某種類似驚艷的心情下聊了一整個下午。收攤後拎著一大袋25分硬幣跑到學校附近一家近似中古時代教堂、滿室裝滿彩色玻璃的肯德基炸雞去痛痛快快大吃了一頓。
那以後,我們有時候會通通電話,有時在學校擦肩而過,蚊子會在青翠的校園裏大叫我一聲。
「喂!」她的口氣總是愉悅開朗。「同學。」
為什麼要叫同學呢?有一次,我就這樣問過她。
「因為我已經擅自組了一個同學會,」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外表正經八百的美女露出調皮神情過?當時,蚊子的神情就是如此。「我把它叫做同年同月同日同學會。」
而根據蚊子的說法指出,這個同學會開放給所有和我們兩個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加入,不過,日後我們似乎也都沒再遇見過這樣的新會員。所以,這個同學會一直就只有我和蚊子兩個人。
接下來的日子裏,瑣瑣碎碎的事情隨著春天夏天,夏天秋天的自然流程過去。我和蚊子在學校見面的機會不多,頂多只是用電話聊聊天,現在想起來,蚊子大概也是一個很寂寞的人吧?除了我之外,彷彿也沒什麼真正知心的朋友。那其實也不能叫做聊天,因為蚊子說起電話來就像是接觸不良的電熱器一般,剛開始的時候語氣疲倦、精神委糜,可是等到進入狀況的時候又吱吱喳喳說個不停,最後才彷彿心滿意足般地掛斷電話,一覺到天明似的。全程都是她在講話居多,我插得上口的機會大概不會超過百分之五。
聊天的內容基本上什麼題材都有,聊她打工的Seven Eleven,聊她那宗教走火入魔的老媽,也聊她在臺灣的男朋友。有時候真的聽得煩了,我會把電話筒擱在一旁,過一陣子再回來「嗯哼」一陣,倒也從來沒被她發現。
基本上,我對蚊子把我當成聽話機器的做法是沒什麼意見。但是,人的情緒總是會有起伏,有時就會在沒有預期的情況下,演出不在預定劇本之內的可怕情節。
基本上,那一天晚上的電話交談中,發生的就是這樣的可怕情節。當時,我一不小心在前一年冬季讓一個女孩的身影跑進心裏,卻在夏天的六月出現覺得承受不了的結果。心情正呈現著五級沮喪的末期症狀。
「所以,當時我和他就在臺北工專附近的一家咖啡館,」不知情的蚊子在那一晚上的電話裏這樣沈醉地說道。「夜深了,咖啡館在每一個桌上點了蠟燭,關上燈……」
蚊子和她的男朋友在她有一年回臺灣參加自強活動時認識,這個燭光故事她早就說過了。而我因為心情太壞,連「嗯哼」都懶得說一聲。
「喂?」蚊子在電話中這樣說道。「喂!你還在那兒嗎?」
「嗯!」我沒好氣的說。
「哦!那就好,反正,我們就坐在那兒,他的手握住我的,燭光很美,他說……」
突然間,我想我大概是瘋了吧!因為我清晰地聽見以下的言詞流暢地從我的口中出現。
「為什麼我還要再聽一遍他說什麼呢?為什麼我要在這裏聽妳說這些廢話呢?妳有苦悶,難道我就沒有嗎?」
電話那一端的蚊子彷彿被嚇呆了,一句話也答不出來。
「為什麼妳一定要人聽妳那些說了一遍又一遍的事呢?我又不認識他,你們分開不能在一起難道是我害你們的嗎?為什麼我心情不好的時候還得聽妳說這樣一大堆無聊話呢?」
說完了,我在電話筒前突地整個人發起楞來。罵人的話流暢到連自己都有點反應不過來。
「Shit!」這是罵完了那一霎那,心裏浮現的第一個字,英文。知道說了可怕的話了,可是,又不知道怎樣去彌補。
難堪的沈默在電話線上持續了一陣。
「對不起……」良久,蚊子才小聲地說道。
然後她就「克」的一聲掛了電話。
幾年後,我和蚊子曾經在紐約的時報廣場前聊起那一次可怕的失控對話。
「真是窘到腳底的感覺,」那時候,我和她坐在星鹿露天義大利咖啡攤位上,看著紐約的人群在眼前匆忙流過。「那時候,好想立刻打電話過去道歉。可是,卻怎麼樣也覺得不知道如何開口。」
蚊子諒解地笑笑。幾年後的她是個潛力無窮的年輕紐約股票分析師,一向素淨的臉上化了合宜的半濃粧。「我那時候只是想,這個傢伙怎麼了。不過後來知道你煩的原因後,也就沒關係了。」
「對不起。」我說道。
「怎麼這麼說呢?」蚊子笑道。「後來,我不是也對你做了同樣的事嗎?」
總之,我在電話裏對蚊子大吼的那一次之後,她打來的電話就少多了,幾乎到了沒有的程度。有時在校園見了面,一樣的明朗笑容,也一樣地遠遠叫我「同學」。
夏天過去,秋天到了的時候,蚊子就順利地轉到了華盛頓大學。那以後的電話更少,而且因為不在同一個學校的關係,連見面的機會也沒有了。
然而,近冬天的時候,我的生日那一天,像往常一樣冷冷清清沒人幫我過,連自己也忘了。晚上快九點的時候,電話鈴聲響起。
「Happy Birthday!」在電話中,蚊子靜靜的說。「祝我們生日快樂。」
再一次見到蚊子,已經是第二年四月的事了。我在那一年的春季班也轉進華盛頓大學,已經在學校上了快一個月的課,對於有些課教室間相隔超過兩公里依然感到讚歎不已。那天,我正走過學校的四個學院系館包住的四合院大廣場(The Quad)。
四月裏的華盛頓大學四合院廣場以櫻花最為有名。怒放的白色櫻花在櫻樹上綻開,走過廣場,彷彿走過一個有白色頂蓋的明亮天堂,地上鋪滿了飄落的白色櫻花花瓣,放眼過去,也像是走進了一頂將天地鋪滿的亮白色花帳。而就是在花帳的最中央,有人這樣叫了我一聲。
「同學。」
那是我在隔了將近九個月後第一次看見蚊子。頭髮長了,舒適地披在肩上。沒有戴眼鏡的臉更多了點令人著迷的感覺。黑色燈芯直條毛衣,白長裙,黑色亮皮鞋,高瘦瘦地襯著一地櫻花站在那兒。
「蚊子!」我高興地叫道。我的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學輕巧巧地走過來,給我一個大大的擁抱。
「好久不見。」她說。
「好久不見。」我也說。
不過,樣子變了,人可是一樣沒變。在學校遠遠見到時還是會叫我一聲「同學」,雖然課程變重了,可是偶爾打電話過來還是一樣聊個沒完沒了。而且最厲害的是,連話題也和九大行星運轉軌道一樣永恒不變。
「Seven Eleven,老媽,男朋友,」我有時候對朋友這樣說道。「除了Seven Eleven薪水調高了,老媽變老,男朋友二專畢業開始工作之外,什麼都沒有變。」
而且,蚊子已經存了三年的錢,準備在那一年夏天回臺灣看男朋友。
我在西雅圖認識的人群之中,有兩類人的屬性比較特殊,我在其它地方很少遇見這兩種人,可是在西雅圖的那幾年間,卻讓我很巧合的碰到了好多個。
兩種人中間,有一種是所謂「含金湯匙出生」的富家子弟,家中物質生活充裕到可以拿美鈔來點煙(而的確也有人幹過這種鳥事)。可是這一類的傢伙們不成材的程度卻可以是你看過所有不成材傢伙的總和。
另一類則恰好相反,通常,他們都生來就有很多傷心、不愉快的往事,但是他們很努力,外表和你我一樣明朗愉悅,對生命的認真態度則遠遠超過你我的總和。而很令人辛慰的是,蚊子和她臺灣的男朋友都是這種類型的人。
蚊子的爸爸在她五歲時就因為一次莫名其妙的火車意外過世。她的媽媽帶著五個小孩後來改嫁給現在的美國人老爸。我見過蚊子的媽媽一次,這位太太是我生平所見最消極的避世宗教狂熱者。基本上,蚊子的媽媽是那種成天建議子女和她一起「共同離開這個污濁塵世」的可怕分子。蚊子她們在西雅圖北邊的家是個沈靜又令人呼吸困難的窒悶空間,老媽,美國老爹,還有她的四個兄弟姐妹都可以大半天一家人不說一句話。但是,從蚊子的外表你絕對看不出來她的家中有這樣的傷心往事。
蚊子在臺灣的男朋友則有著比她更傷心的過去。
「他的爸爸是個很有地位的人,」蚊子在電話中說過一個的確擲地有聲的人名。「在歡場逢場作戲時和他媽媽生下他。本來父方打算讓他入籍的,但是他的外婆堅持把他留下。他媽媽後來從良嫁了個老兵,可是老兵一喝醉就會拿刀砍他們母子。他在十歲那年就離家自己打零工賺錢,靠自己唸到二專畢業。」
那時候,蚊子的聲音很興奮,我可以想像她眼睛充滿光采的模樣。
「而我現在要回去看他了,他苦了好多年,現在終於可以好好過日子了。」
初夏六月的一個中午,我幫蚊子載了兩大件行李送她到機場。初夏的塔克瑪機場空調非常的涼,可是蚊子高興得臉上泛出微汗的紅暈。
「我會帶禮物回來的。」又是一個大擁抱。「等我回來我們再一起過生日。」
夏天的西雅圖花開得非常燦爛,在綠色的大地上彷彿燃起一團團色彩繽紛的火。七月、八月過去,我沒有收到蚊子的任何消息。加上自己也在暑假玩得挺瘋,等到九月學校要開學了,才發現蚊子打從回臺灣到現在從來沒捎過來隻字片語。
應該一切還順利吧?我偶爾在心裏單純地這樣想著。也許在臺灣結婚了也說不定。
九月底十月初,學校開學,校園裏又來來去去充滿在教室間穿梭的年輕學生。蚊子一直沒消息,打電話到她的宿舍說早在六月就退租了。而我壓根兒就不曉得她工作的Seven Eleven在哪裏。也想過要去她家問問,但是非常離譜的是忘了她家在5號公路的哪一個出口。
原來,在這樣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要失去聯絡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兒。
十月,西雅圖開始進入冬天的雨季,一年九個月的綿綿細雨從天空不眠不休的飄落。
我和蚊子的生日那天,同年同月同日同學會沒有任何慶祝,因為會員只剩下一個。長夜漫漫的生日那一晚上,電話鈴一直沒有響過。
冬天到了。雨城的冬季雨在十二月的聖誕假期轉為白色的雪花,聖誕節前夕已經飄了好幾天的雪。
而蚊子終於在下雪的一個晚上打了電話過來。
「妳在哪裏?」我驚訝的問道。「還在臺灣嗎?」
不是。蚊子簡短的說。其實她早在八月就已經回到西雅圖。
「我想和你說說我男朋友的事情。」
「嗯!好啊!」我點點頭。
蚊子說,她的男朋友實在是一個命很不好的人,可是他沒怪過任何人。從他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得一個人打工養活自己。他的手臂上有一個疤,是有一次他那個老兵養父要砍他媽媽時幫媽媽擋的。
雖然這些內容我都已經聽過了,我還是在心裏嘀咕著耐心聽下去。
近午夜的時分,窗外的雪無聲地就著路燈燈光飄落。遠方的地平線上有妖艷的橙紅,隱隱看得到來自阿拉斯加映照的極光。
蚊子繼續語氣平板地說下去。
「他的親生父親也來找過他,但是他不想和他們有任何瓜葛了。外婆現在和他住在一起,老人家變得好老好老,身體也不好。他一個人兼三份工作,每天晚上回家都好晚,而外婆常逼他早點結婚,想早點抱孫子。」
「為什麼他就要這麼辛苦呢?為什麼這樣的好人卻沒有一分鐘可以好好喘口氣呢?」蚊子的口氣越來越急促。「為什麼老天爺就這麼不公平,這世界上有那麼多的人,為什麼他一個人就要吃那麼多苦?」
「蚊子……」我有點困難地想說句話。卻被她越來越急促的聲音打斷。
「為什麼好人不一定有好報?」她繼續有點狂亂地說道。「為什麼像他這麼努力的人,得到的卻只有這麼一點點,而像你們這些天生命好的公子哥兒,不用做事就可以過得舒舒服服?你為什麼要在這裏?你為什麼要在這裏聽我說話?你們為什麼不都去死!」
然後,她居然就這樣「克」一聲就把電話掛掉。
我有點難以置信地把電話筒放回去。好像在什麼時候發生過類似情形似的。我支著下巴,看著飄落的雪花發了一會兒呆。
「原來人家說雪花像鵝毛一樣是真的啊!」我在心裏很奇特地出現了九不搭八的詠歎。而的確,大片大片的鵝毛雪就在我眼前無聲無息的飄落滿地。
而就在這個時刻,電話鈴再度響起。
「對不起……」蚊子在那一頭低低地說道。
「沒關係。」我說。而且我是說真的。
話筒那一端又有了小小的沈默。
「可以過去你那裏嗎?」最後,她這樣說道。
我很認真地想了一下。
「可以。」我說。
一打開門,就看見蚊子柔亮的黑髮上都是雪花。看見我,她突地「哇」一聲哭出來,像個無依無靠的小女生般地緊緊抱著我,痛痛快快地放聲大哭。
我皺著眉,覺得非常不知所措,本來想推開她,和她好好談談。可是,腦海中突地流過許許多多的往事。蚊子依然在我懷裏抽抽答答的哭。而我只是楞楞地站在那兒,任著她扯著我的臂膀,臉埋在我胸前地哭。
也許我算是她在這世上唯一一個可以說心事的人了。我想起她的老媽,想起蚊子那幾個神色漠然的弟妹,想起我對她大吼的那一次,也想起前一年,我們的生日那天晚上。
「Happy Birthday。」她說。「祝我們生日快樂。」
那一年的暑假,蚊子本來要在臺灣陪男朋友到九月底學校開學的,可是卻在八月就回到西雅圖。
那一年在臺灣,有一個夏天的深夜裏蚊子聽見男朋友在電話裏低聲向另一個女孩說著這樣的話。
「我會和她說清楚的,好不好?」他悄悄地捂著電話說。「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她從那麼遠的美國回來,我總不能做得太絕吧?……」
那一個下雪夜裏,蚊子哭了一會兒就不哭了。通常,堅強的女孩子眼淚不會太多,縱使有時堅強的外殼有時會暫時崩垮,時間過去,眼淚也就用完。
「讓我整晚抱著你,好不好?」蚊子那天晚上不讓我開燈,坐在我的床上,臉上映著窗外的雪光有淚痕。「但是,什麼都不做,好不好?」
「好。」那一個晚上,我的話非常的少,已經到了只能說單字的地步。
而其實,蚊子芳香柔軟的身體抱著我的時間並不長。沒多久她的手臂就放鬆,很放心地在我的床上沈沈睡著。我替她蓋了棉被,坐在她的身旁,連呼吸都不敢太響。
房間裏呈現出永恆般的靜寂。隔著玻璃窗,雪還是不眠不休地飄著。而我,卻在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連一點最起碼的睡意也沒有。
也是在幾年後那一次紐約時報廣場前的見面,蚊子問過我那一晚上的事。
「為什麼你沒有對我怎樣怎樣呢?」蚊子調皮地說道。「雖然我說什麼都不想做,可是在那種狀況下,不論你做什麼其實我都不會怪你的嘛!」
我笑笑,沒有說話。
「也說不定,」蚊子又說。「我在那裏很期待很期待你來對我怎樣怎樣的,因為剛剛被男朋友甩掉的女人可以是很饑渴的喲!」
「因為妳沒有說出來嘛!」我故意繃著臉。「妳又不是不知道,那時候我們都那麼年輕,對於女孩的心事哪知道那麼多?」
「是我沒有魅力嗎?」她做出一付有點擔心的表情,有點像開玩笑,又彷彿挺認真。「對男人來說,我是不是那種沒有Sexual arousal性吸引力的女人呢?」
我們在紐約的嘈雜空間中笑得很開心。比幾年前更添成熟味道的蚊子的確是個非常的美麗的女子,在原先那種冷靜的美感中又多了點類似自信的神采。
「不過,如果是現在的話,」後來,我很誠實地說道。「妳可能就完蛋了,也許就對妳怎樣怎樣了也說不定。可是,那時候真的在腦海中有某種稱得上是堅定的信念。」
蚊子啜了一口翠綠的薄荷義大利蘇打,很專心地聽我說下去。
「因為我想,同年同月同日同學會的傳統中,並沒有上床這一條吧!」我說。「而且,好像如果真的一起睡了,就會有什麼東西「匡噹」一聲全數碎掉的感覺。不過……」
「不過……」蚊子很開朗地幫我接下去。「現在就不一定做得到了,說不定,你會像餓狼一樣的撲向我,對我怎樣怎樣,對不對?」
「對。」雖然沒看過女人講到被怎樣怎樣還興高采烈的,但是我還是點點頭。
然而,就連那次紐約的見面也是挺久以前的事了。之後我和蚊子沒再見過面,因為西雅圖和紐約雖然理論上在同一個北美大陸上,但是專程跑去見個面又彷彿找不到任何的藉口當著力點。
可能我對自己也沒有信心吧?因為蚊子還是很美,很令我著迷,而我們的聲音卻不見得能再像年少時那樣的醇淨清澈。
「如果做了什麼什麼的話,也許就會『匡噹』一聲全數碎裂掉了吧?」
至少,到目前我還是很堅定地相信這一個論點的。
每年近冬天的時刻,蚊子總是按照往例,在我們的生日那天撥個電話過來。
「Happy Birthday。」她會說。「祝我們生日快樂。」
而事實上,只做「同年同月同日同學會」的共同會員,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想,蚊子也會同意我這個想法的。
心情挾煙機
五光十色的小小空間,近似於霓虹燈的燈光不住閃耀。投下十塊錢硬幣,前進、左右三個按鈕的指示燈閃閃發亮。挾煙遊戲機軟垂的鋼爪無精打采的昇起。在電子合成的俗氣音樂聲中,我小心翼翼地調整鋼爪的方向,一走錯就不能回頭。找定目標,鋼爪下落,三隻爪子攫緊……
當然最後還是撲了個空,鋼爪收回,禮品掉落的洞口像往常一樣空空如也,向來我就不是玩這種挾煙遊戲機的高手。只是每逢天氣特別寒冷的冬天,如果在大街的走廊上看見這種看似金碧輝煌,實際上孤零零矗立在冷風中的挾煙遊戲機,我總會花上幾個十塊硬幣玩一玩。而每當遊戲機的鋼爪收回,洞口空空如也的時候,我總會想起很久很久以前那個臉圓嘟嘟的小男生。
算起來,那應該是我高中三年級的事了。我在高三的時候因為準備聯考,曾經在臺中市的學校附近住過一段時間。學生口袋裏的錢就好像熱帶雨林中掉落的一瓶蜂蜜似的,吸引了附近許許多多的商家,紛紛在學校附近開了許多吃喝玩樂的好玩店面,而且為了把學生的口袋再掏深一點,很多店鋪的門口也放了挾禮品香煙的遊戲機。它們總是閃閃發亮的立在走廊上,玻璃箱內的禮品向路過的人露出魅惑的笑容。
我們常去的一家麵攤口就有這樣一部挾洋煙的遊戲機,有時候吃完晚飯,也會忍不住花上幾個銅板碰碰運氣,當然,真正抓中的機會微乎其微,在我自己的記憶中,好像從來沒有過挾中洋煙的紀錄。
「這騙人的嘛!」我的同學彭呆有一次再度落敗於機器手下之後,這樣氣急敗壞的說道,還踢了機器一腳。「要不怎麼沒看過有人挾到過?」
那時候是個陰冷的冬天的星期六下午,我們幾個住宿舍的沒回家,約好到麵攤吃碗麵暖暖身子。等麵煮好的空檔中,我們幾個大漢圍在遊戲機的旁邊,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聊著。彭呆還想再在機器上踢上一腳。突然間,一個稚嫩的小孩聲音在我們後面響起。
「不是這樣玩的,我玩給你看。」那個小男孩這樣說道,一邊從彭呆手上拿過來一枚十塊錢硬幣。
小男孩熟稔地把硬幣投進機器,專注的神情,右手像是武學高手似實若虛地掌控著前進,左右轉的按鈕。挾煙遊戲機裏的鋼爪不尋常地只動了一個短距離,準確地下探,拎起一包莫爾涼煙。鋼爪拎得不是頂緊,它顫危危地挾著香煙,在領禮品的洞口頂端就掉下來,可是這樣便已經足夠,「咚」的一聲,那包綠色表層的莫爾洋煙就乖乖地躺在洞口的底部。
「你看看,最重要的是不可以抓香煙最多的地方,」小男孩像個大宗師似的對幾個目瞪口呆的大男生侃侃而談。「因為香煙越多,出問題的機會也越多。」
過後,我們大夥出錢請他吃了一碗麵,大夥就這樣認識了。小男孩當時大約十歲上下,讀國小三年級,玩挾煙遊戲機對大部分人來說只是可有可無的消遣嗜好,可是,對小男孩來說卻是種謀生的工具。
原來,小男孩來自一個破碎的家庭,父母親在幾年前就離異了。母親從他八歲起就沒再見過面,父親已經再婚,住在臺北,後母不願意收留他,所以小男孩就自己一個人住在附近的一棟小套房裏,每個月做父親的出現一次,除了付房租外再給他一些錢做該月的生活費。小男孩非常的聰明伶俐,很討人歡心,可是因為自己一個人住,又沒有人管,花起錢來就沒有節制。他的年紀還太小,抽煙喝酒那些不正經的事還學不會,但是常花錢去買玩具。
小男孩父親給的錢總是在月中前後就花光,於是,玩挾煙遊戲機就成了他謀生的技能之一。如我前面所說的,小男孩的技術非常的高超,有百分之六十的機率會挾中洋煙,贏到的洋煙就找相熟的商店老闆用二三十塊錢買回去。可是有時還是會遇到手氣不好的時候,遇到這種狀況就只好喝白開水過日子,真正餓到受不了的時候就只能找像我們這樣的萍水相逢之交借一點錢,而且每次他的父親知道了就會狠狠打他一頓,帶著他去把錢還清,卻也不肯多留一些錢給他。
有一回,我們又請小男孩吃飯,吃飯的時候小男孩說要借錢,我們幾個人東湊西湊集成幾百塊錢,我的同學彭呆脾氣很大,心卻最軟,他把錢遞給小男孩,告訴他不用擔心還錢的事,但是要省著點花知不知道?小男孩高興極了,紅撲撲的臉蛋笑顏逐開,興奮地點點頭。
「我帶你們去我家玩,好不好?」吃完飯後,小男孩這樣討好地說道。我們互相對望了一下,紛紛點頭說好。也許對這種年紀的小孩來說,這算是最高層級的道謝方式了吧?當時我的想法是這樣的,而且我想我的同學們的感覺也差不多。然而,再怎麼說那也不能算是個家。座落在一棟四樓建築的加蓋頂樓,一打開門只有一個房間,裏面一張傢俱也沒有,只在地上鋪滿報紙,房間正中央放個紙箱做桌子,地上散落著玩具、衣服、書包和嶄新的課本。
小男孩很熱絡地要我們和他一起玩他的玩具,可是沒有人有這種心情。走出他的家,每個人的心情都像是那天的天氣一樣,陰陰的,感覺非常的沈重。
幾天後,我們還是在同一家麵館吃晚飯,看見沒人玩的挾煙遊戲機,正納悶怎麼好些天沒看見小男孩的時候,有個胖胖的男人領著他來到我們的面前。
「是他們是不是?」他粗魯地把小男孩拎過來。「你給我過來!」
「他欠你們多少錢?」小男孩的父親瞪了我們一眼,開始從口袋裏掏錢。小男孩瑟縮地站在一旁,臉上有明顯的巴掌印子,眼淚在眼眶子裏轉來轉去。
沒人回答。
「欠人家多少錢?」小男孩的父親轉過頭去,重重地堆了他一把。小男孩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
「砰!」的一聲,我的同學彭呆雙手一拍桌子,把桌上的碗盤震得匡匡作響。站地身來,鐵青著臉轉頭走了。
「沒有啦!」我開口說。「那是給他買東西的。」
他的父親又瞪了我們一眼,把錢收回口袋,也掉頭走掉,小男孩抽抽答答地,也跟在他的身後一起離去。
過了沒多久,我們看見彭呆再次出現,有個同學叫了他一聲,他理也沒理,逕自往小男孩和父親離去的方向快步走過去。
後來我才知道,彭呆當天晚上追過去,不由分說就往小男孩的父親臉上揮了一拳。小男孩的父親一狀告到學校,還因此記了彭呆兩次大過。
那以後幾天,小男孩臉上的指痕一直沒消,看見我們也躲得遠遠沒過來。有人要過去和他說話他拔腿就跑。聽附近雜貨店的老闆說,因為他的父親警告過他,如果再和我們這幾個混在一起就連生活費也不給他了。
時光匆匆的過去,當然沒多久之後我們就從高中畢業了。那個小男孩我們沒有人再見過,只是有時候總覺得會在什麼少年重大刑案的新聞轉播上看到他,因為在這樣一個充滿誘惑的社會環境中,他要全身而退的機會也實在是太渺茫了。
這些年來,我的生命足跡飄忽不定,從臺灣盪來了美國西北區的西雅圖,不論在哪裏,挾煙遊戲機依然在我們這個悲愁的人間處處可見。看似單純的機器後頭卻隱藏著這樣一段令人心頭沈重不快的故事。而我也常在街頭看見同樣年紀的小孩子與我擦身而過。有時也會很想知道那個小男孩現在過得好不好。
「如果不能好好的養育人家的話,帶他來這個世界上做什麼?」
說老實話,我想,當年我是該和彭呆去揍小男孩的父親一頓什麼的。
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