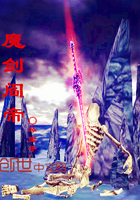“阿烈!”未等慕容烈下马,郝贝已拖着一身邋遢至极的衣服跑了上去。郝南见李穆然目露询问,忙道:“阿贝自小在慕容都尉家中长大,和慕容家的人关系更近些。阿烈和她也算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武功也是一起学的,算得上是同门。”
“这么说,阿烈一早便应认识郝南。那么他当时去拦那个刺客他怎会看不出刺客是谁?”李穆然心中隐隐不快,亏自己还好心好意介绍郝南认识慕容烈,想着这能让他尽快在众百将之中脱颖而出,原来是多此一举。他早知郝南是个城府深沉的人,却没想到慕容烈也能将自己骗得懵然不知。
他心知这必然又是大将军暗中授意,不觉深吸口气。自己眼前仿佛还能看到慕容垂谈论刺客时的声色俱厉,现在想想,那些多半也是假的了。不知道大将军从什么时候起知道了慕容山在背后动的手脚,更猜不透的是,大将军究竟将自己当做什么人。可是这几个月来大将军的默默提携,也是如此真诚他缓缓压下心中的不平与愤慨,问道:“阿烈,你也来了?”
慕容烈下了马,对郝贝摇了摇头,随后走到李穆然身前,道:“李兄,我去郝兄营中找他,才知你们一起出来了。既然如此,想必有些事情你已经知道了。大将军也是刚问过慕容都尉才明白的。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了!大将军叫我速来,便是希望你能和郝百将依旧如昔,不仅人前,更是人后。”
见李穆然颔首,但脸上神情僵硬,似乎仍不肯释然,慕容烈拍了拍他肩膀,道:“李兄,大将军是看重你的,很多事情该忘就忘,你是个聪明人,该明白怎样对自己最好。”
李穆然明白他是要自己不再去追究薛平以及常武的死,毕竟那两个人只是普通士卒,不仅家里无权无势,而且自己也没有什么过人才能,自然比不上郝南和他的家族势力。他看向郝贝,道:“后军慕容都尉呢?”
慕容烈道:“慕容都尉针对你,是因为怕你挡了郝百将的路。可是再过三日,郝百将就要升为千将,他自然不会再在意。”
“千将?”李穆然只觉震惊,与郝南异口同声地问了出来。
慕容烈对郝南道:“圣上很赏识你,所以决定破格提拔。三日后,新兵营和良家子弟合在一处,你手下将有两个新兵营的百人队和八个良家子弟百人队。大将军希望你好好表现,不要再让他帮你为很多事情善后。”
郝南道:“我明白,请让大将军放心。”旋即,他又看向郝贝,皱眉道:“阿贝,你待会儿跟阿烈一起回去吧。”
郝贝白他一眼,道:“你撵我回去?怕我被他杀了吗?”她下巴一抬,指向李穆然。郝南只觉头皮发炸,他虽然能做到百花丛中风流倜傥,可偏偏对自己这个妹妹没法子。他无奈地看了慕容烈一眼,道:“阿烈,你来劝她吧。”
慕容烈也觉得头皮发麻,他与郝贝算得上是从小打到大,对她了解透彻,深知郝贝除了慕容山夫妇的话以外,谁的话也听不进去,自己这时贸然开口,岂不是触霉头么。然而他毕竟不能让郝贝僵在此地,便清了一声嗓子,道:“小师姐,这是军务正事,你就”
“呸!”郝贝一吐舌头,冷哼一声,“阿烈,我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管?”
慕容烈被她一句话训得不敢再张口,倒是李穆然冷笑一声:“阿烈,恕我见识浅薄,从没见过这么蛮横不讲理的女孩子。”
“你!”郝贝横了他一眼,怒道,“你说我蛮不讲理?”
李穆然笑笑:“以往我不懂这四个字的意思。今日见了姑娘,算是上了一课。”
郝南脸色一白,忙道:“阿贝,阿贝,李兄是和你说笑的。你今天已经杀了人,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你再不走,等一会儿回去,我一定让你义父拿家法出来好好教训你!”
“没你的事!”郝贝俏脸气得发青,一挽袖子,道,“姓李的,我知道你在新兵演练场上输给我后,一直不服气。今天我就给你比试的机会,你若赢了我,我就再也不插手你的事情。否则加官进爵,哼哼,你就别痴心妄想了!有我郝贝在,保你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小师姐,你这话若被大将军听了,小心罚你禁闭!”慕容烈有些着急,张口喝止道。
李穆然却对慕容烈一挥手,道:“阿烈,你不用担心我,我就与她比试比试。”语罢,一立承天剑,道:“你有什么手段,都用出来!”
郝贝“咯咯”笑道:“爽快!我这次不用毒,让你输得心服口服!”随即,柳腰一折,竟以迅雷之势从慕容烈腰畔抽出佩刀来。
“阿烈,斩风刀借我用用!”她声音未落,整个人带着刀风,卷着满地黄尘,已攻向李穆然。
她的身法很灵巧,身材也很瘦弱,但是一旦手中握刀,竟整个人变成了一把刀,凌厉异常。李穆然手中的承天剑一晃,与斩风刀接了三四招。斩风刀锋锐不在承天剑之下,两者碰撞火光四溅,却并无损伤。
接过几招之后,李穆然心中一定:郝贝的武功虽高,但毕竟是个女子,手中力气并不算大,因此斩风刀的优势并不能完全展现。但毫无疑问,郝贝是他出谷后,遇到的武功最强的对手。
她比石涛更厉害。她每一招都能化成四五招,从不同的地方攻来,纵然自己全力格挡,仍觉吃力。
不过他仍是占着上风,因为郝贝的“刀法”他曾不止一次地见过:平日他与郝南一同练兵,与慕容烈偶有比试,对他们的武功再了解不过。郝贝的刀法中夹杂着郝南的刀法,也夹杂着慕容烈的刀法,沉重而快猛,远胜纪忠国的纪氏雪花刀。可是她不常上战场,不过夹在后军乌桓仲的队伍里,接过一两次战势,因此她的刀法还是多了许多本不需要的虚招,花哨华丽,并不实用。
很难想象慕容山和他的义女,竟然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李穆然本以为郝贝的武功应是直截了当,故而出口挑战时,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但与郝贝交手后,他却自信了起来:自己一定能赢!
他想起在桐柏山上初见慕容山出手,那般的凌厉直接,让自己不寒而栗。当时他自信凭招式完全能胜慕容山,可是两人一旦对敌,不出三招,自己便是身首异处。因为上战场没有那么多时间由着人用出花招虚招,每一招的目的都是为了你死我活,不必漂亮,也不必完美无懈,故而这半年时间,他一直在练如何最直接的出剑,最迅速的伤敌,最不费力气的结束一场战斗。今日的比试,正如昔日的慕容山对上昔日的他,只是他的身份已有转变,虽然对方武功在自己之上,但他相信这些日子苦练的结果能够扳回这种劣势。
在又闪过三四招刀劈刀砍后,趁着郝贝的招式用老,李穆然终于出了手。
他这一剑刺得极是凶猛,甚至郝南与慕容烈在旁看了,都不由失声惊呼。
那一剑刺得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待得郝贝要躲闪时,剑已刺到面前。
她从没有输过,一时间整个人呆在了当场,连躲也忘记。李穆然没料到她在这时忽地失态,剑来不及收,只来得及向旁边侧了侧。
然而承天剑是如此锐利,虽然剑锋勉强侧开,可是剑气充沛,竟划破了郝贝的左颊。
那伤口不深,也不长,大约半寸不到,就在颧骨之下,可是郝贝整张面孔都如玉雕一般,剑伤及面,登时鲜血涌出,沿着她的脸颊流下来,集到下巴上,一滴一滴地滴在肩膀上。眨眼间,肩上就仿佛开出一朵血红的花。
一时间,所有人都呆住了。
郝贝整个人傻傻地愣在了原地,一双小鹿般的眸子眨也不眨地盯着李穆然,连话也说不出来。不知过了多久,她缓缓抬起了左手,碰到脸颊上的伤口时,忽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阿贝,阿贝!”郝南眼睛睁得比郝贝还要大,飞身纵到李穆然与郝贝之间,两手抓住郝贝的双肩,轻轻摇她,急声道,“痛不痛?没事的,乖,没事的。”
慕容烈与李穆然更是怔住。良久,只听“当”的一声,承天剑跌落尘埃,慕容烈整个人一颤,看向李穆然。只见那高大俊朗的男子原本铁青的面孔已变得惨白,目光中有痛悔,也有疼惜。
“哥!我毁容了!”郝贝被郝南一劝,更觉委屈,眼泪如断线珠子般落下,整个人一下钻进了郝南的怀中,紧紧抱着郝南,哭得撕心裂肺,叫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听到“毁容”二字,李穆然更觉难受。他何尝不知容貌对于女子来说,有时甚至比性命还要重要,可是他那一剑,刺在她脸上,谁也说不好等伤口好了会不会结疤。倘若结了疤,那自己真的是永远也弥补不了对她的伤害了。
想起对薛平、常武二人之死的伤痛,对自己被屡屡暗算的怨气,仿佛方才随那一剑,都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是内疚。他轻叹一声,拾起承天剑,反交剑柄对着郝贝,道:“郝姑娘,我对不起你。你若想解气,便也在我脸上划一剑,划十剑都随你。”
这时郝南已为郝贝将血擦净,又取出随身带的金疮药擦上。郝贝伤心之余,毕竟还是关心自己容貌,早扔了斩风刀,取出怀中的菱花小镜照着。只见镜中的自己左边脸上全是又黄又绿的药粉,搀着新出的血,红红黄黄一大片,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不由瘪瘪嘴,全然不肯听郝南说那伤口不长也不深,便又哭了起来。
李穆然见她不理自己,只好硬着头皮在旁候着。他扭头去看慕容烈,只见慕容烈耸了耸肩,对自己投来一丝同情的目光,旋而又是摇了摇头,转头看向远方。
不知等了多久,郝贝才止了哭。她抽泣着咽下嘴角的眼泪,一双眼睛狠狠瞪着李穆然和他手中反持的承天剑,问道:“你干什么?”
李穆然垂头又重复了一遍,然而话还没说完,一物已劈头盖脸地砸来。李穆然强忍着没有躲,只觉头上一痛,继而一物砸在脚面上。他定睛瞧去,见正是方才郝贝拿在手中的菱花小镜。
他没有说话,微微闭上了眼,只等着郝贝继续大发雷霆。
孰想郝贝的骂声接踵而来:“姓李的,你以为我是什么人?说了比试就是比试,我输了便是输了,还用你装可怜来讨好吗?什么补偿,什么解气!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给我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郝贝骂完了,忽地扭头跑到郝南的坐骑边,怒叱一声,已驾马跑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