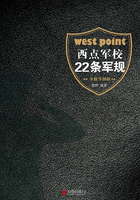有时候,也会想,自己真的没有做另一种人的能力吗?
打牌抽烟喝酒,应该学一学就会的。耽溺于体育频道的有形竞技与时政方面的无形竞技,似乎也不是难事。或者,娱乐的同时兼顾生财,比如那些时时刻刻都聚精会神地留心着风吹草动的人们,一边手捧平板电脑刷着股票基金期货贵金属行情,一边问候着空气与尘埃的母亲。
可是,就是不会啊,只是低头写细小的字,像个一辈子都和针脚打交道的缝纫工。
外人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名利场的交际上,或者寻欢于温柔乡。他们从心底嫌弃这个行当的穷酸无聊,同时还逼真地自叹弗如,说:“真是耐得住寂寞啊。”
寂寞不需要忍耐,不需要挨。倘若话不说这么满,那就是——偶尔才要忍耐,才要挨。寂寞是伴侣,长期的磨合使双方具有不俗的默契度,偶然的错位才会出现“忍耐”和“挨”的局面。错位的幅度决定着或大或小的后果,这与寻常人家的饮食男女发生口角陷入冷战甚至大打出手别无二致。但多数时候,寂寞眷顾着写字的人,写字的人也迷恋着寂寞。就像男女常态的相爱。
以爱为喻实在是庸俗,好似古往今来写爱的文艺作品也在各自的时代里泛滥成灾。乐府情诗花间词,能诵能唱;传奇话本杂剧,能读能演;到了民国时期,郎情妾意的题材除了汇成风生水起的鸳鸯蝴蝶以外,更是在银幕上大行其道。
归根结底,爱是人类最朴素的理想。不得爱者,盼它光临。已得爱者,愿它常驻。
带着山高水长的期望,那些源远流长的故事都被冠以青梅竹马、破镜重圆、凤凰于飞、琴瑟和谐的面目,而对现实的疮痍有本能的抵触。像是不满《莺莺传》的遗恨哀伤,遂二次创作成花好月圆的《西厢记》。
上一部长篇小说《铅华》写成,已是七年前的事了。这一部动笔在三年前。动笔之初,我没有想到会用这么长的时间。这期间,它曾被空置很久——自我感觉需要回想写这本书的初衷,让它在逼近结局的过程中凸显,再逐渐消弭。
慢慢地,就想起来了。我最早是想写一场“不对”的爱情。说“错误的爱情”太笼统武断,它不是错,只是不那么对。对的爱情太多了,不对的爱情也多,只是看起来不值得描摹,仿佛一张曝光报废的胶片,不值得动用暗房冲洗。
一见倾心,扶持前行,爱成大业,这样的爱固然值得歌颂,可永垂不朽的只是很小一部分。那些狭路相逢、荒腔走板、一败涂地的爱即便真是反面教材,首先也该被翔实记载。
这个故事说的就是后面这一种。看起来的确是不够美好,却禁不住这样的故事总是如风一样在城市里来回萦绕。
丝丝缕缕的想法,已借助每一个角色之口做了表达,再过分赘言就很无趣了。其实许多事也都是说不清楚的,模棱两可的,于是这一方戏台上,生旦净丑,各自吟唱,水袖交错,旌旗堆叠,一片乱舞纷呈。
华美的并非浓墨重彩,而是这一段最好的时光。似水流年,锦衣霓裳,付之一炬。回头看去,依稀还有愁惨的火痕。人生自然还长,步入新的阶段,祈求涅槃。只是遗民都喜爱在月下踱步并寻找,执着地幻想着冥冥的风烟消散后,依稀还能隔空看见他们曾经的王朝。
张秋寒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