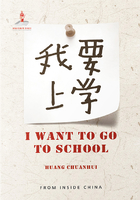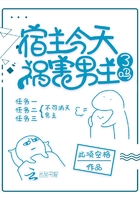我们启程向日内瓦方向出发。此时,阴云密布,黄昏早早降临。梵特睡着了,头向我的方向歪着。从他身上能闻到酒精和烟草味。他讲籁雅在圣莫里茨参加比赛的事情时,又掏出烧酒来喝,还用快抽完的烟屁股点燃了新的一支。要是在我自己的车里,是不准抽烟的,我受不了,会觉得喘不上来气,马上会觉得衣服上都是烟味。可现在没有关系,不知为什么,现在我一点也不受影响。
我看了他一眼。他早晨没有剃胡子,还穿着昨天穿的那件衬衫,昨天他痛斥那些去看梵高病房的游客时,把领口撕开了。那上面三个扣子敞着。这是一件没有熨烫的衬衫,经过无数次洗涤,已说不清原来是什么颜色了,外面是一件皱巴巴的黑外套。他用嘴和鼻子同时呼吸,此外还能听到一些呼噜声,呼吸显得有些吃力。
他闭着眼睛的样子,好像很需要保护似的。一点不像那个曾经想造假钞,或者在联邦广场下象棋、让对手一败涂地的人——就因为那个对手敢盯着他,而更像一个害怕露丝·阿达的人,虽然他永远不会承认;尤其像一个不愿意对一个孩子承担责任的人,因为他有种感觉——对自己他都不知道该如何承担责任;还像一个将梅甸大夫的话当作鞭笞的人,因而提到他时,只说那个北非人。
我试图想象汤姆·考特尼睡觉的样子,并想知道,如果他同一个女孩住在一起,而这个女孩却要为拉小提琴费尽心血,那该是什么样子。对这些问题梵特都已变得很不确定了。“即使在实验室,我也觉得自己好像知道得越来越少。”他说。
竞赛选手们按照姓氏拼写顺序出场。这意味着,籁雅将是倒数第二个。
“我们坐在一起进早餐时,她脸色苍白,淡淡地笑着。没有谁被要求必须去听竞争对手的演奏,不过当我建议,别人演奏时我们去散步时,籁雅不耐烦地摆手拒绝了。这一天她什么都不听我的。有一阵子,我突发奇想,想象着自己什么都不说,离开酒店,乘下一班火车去克洛滕。而事实上,当照在观众席的灯光灭掉后,我一分钟都没少地一直坐在她身边。我们没有交换一句话,也没有互相对视,但我知道籁雅每一秒钟的所思所想。是通过听她的呼吸,通过她的坐姿及在椅子上的动静感觉到的。这样的分分秒秒,令我难挨,又令我高兴,因为在离籁雅这样近的地方,我可以通过她的无言,破译她的内在。”
“前两个参赛选手的演奏,动作僵硬,不值一提。我能感到,籁雅有些放心。这感觉令我欣慰,可是这放松后面隐藏的残酷性,又令我在回味中感到震惊。从现在起,我的内心充满了这类很矛盾的感觉。他人的缺点既意味着希望,可以从籁雅深呼吸中听到的轻松,又意味着残酷。”
“我跟别人下象棋,遇到决定胜负的紧张局面时,是怎样的情况呢?我眼前出现了父亲,出现了他用满是瘢痕的手,移动棋子的样子。当看到失败不可避免时,他会叹口气,作出无可奈何的投降状,说:‘你都是怎么走的呢?’一次,当我看到自己失败在即,便让国王倒下做出投降状,父亲迅速抓过棋子,让它直立起来。他不属于可为此类举动作出解释的人,可他的脸,一下子变得有棱有角,还有些白皙,仿佛由大理石刻成。这使我意识到,在他疲倦、厌烦的表面背后,还藏着怎样不屈的骄傲。他就这样以筋疲力尽的沉默教给我,要想着取胜,但又不要让这个准备状态,同残酷归到一起。从他在病房最后一次握我的手算起,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次他比平常握得要紧得多,因为他已经料到,他会在夜里离去。”
“我坐在女儿身旁,女儿正迫切期待着他人的失利,在这个时刻,我感到对父亲从没像现在这样想念过,尽管我曾无言地——内心里也无言地对他充满了不满与气恼。成年人应该怎样将自己的体验,让孩子知道呢?如果你发现孩子身上有着令人震惊的残酷,你应该怎样做呢?”
“上午共有五位选手上场,其中两位没有来吃午饭。另外三位,闷声不响,头低在餐盘上,只顾吃饭。他们一定已意识到,他们的演奏没有取得光彩的成功,现在他们只能忍受他人的注目——这也是比赛的一部分。我看看这位,瞧瞧那位,这些跟成年人一样演奏的孩子,现在也同成年人一样,用勺子喝着他们的汤。我想,我的上帝啊,这有多残酷。”
“父母们也知道,他们的表演不够好。一位母亲抚着女儿的头发,一位父亲把手放在儿子肩头。突然间,我意识到,当别人的目光向我们这边扫来时,尽管也都亲切友好,但还是残酷的。他们在把我们当成演员。我们不能再沉浸于自我,我们需要为别人表现,他们让我们离开自我。最糟糕的是:我们还必须假装自己是一个特定的人物。这是别人的期望。其实我们根本不是什么特定的,我们更愿意将自己藏在舒服惬意的模模糊糊之中,这也许恰恰对我们最重要。”
我想起保罗口罩上吃惊的目光,这目光让我在自我中缩成一团。我还想起了一位护士低下头的样子,她不忍心看我在那一刻的无能为力,这比保罗的惊诧更令人难受。
“下午的比赛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惊喜。上台表演的女孩叫索尔维格[34],这个名字很具童话色彩。她带有雀斑的脸上似乎没有笑容,裙子像个大口袋搭在她身上,胳膊瘦得令人怜爱。我自然而然地等着可能会出现的、让我们尴尬的较微弱的琴声的出现。”
“然而,琴声炸响了!演奏的是俄罗斯曲目,我没听说过那个作曲家。那是烟花鞭炮般的声响,滑音、双音,位置跳转得令人眼花缭乱。女孩的头发好像没有洗,看上去一缕一缕的。可突然头发飞了起来,她的眼睛也闪闪发光,柔弱的身体随着激越的音乐轻柔地荡起来。台下一片静寂。然后掌声超过了所有我们上午听到过的演奏。此时每个人都清楚这点:比赛这才刚刚开始。”
“籁雅一直一动不动地坐着。我没有听到她的呼吸,我看看玛丽,玛丽的眼睛像在说,籁雅会与这个女孩有得一搏。籁雅闭上双眼,两个拇指慢慢地一起搓起来。我感到一阵冲动,很想用手去抚摸她的头发,用手臂去搂她的肩头。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克制自己这个冲动的?最后一次拥抱她——我的女儿,到底是什么时候?”
“再有两位选手演出后,就该轮到她了。那个女孩让裙边绊了一下,那个男孩一个劲地在他裤子上擦手,苍白的脸上可以让人看到害怕,手指潮湿会造成琴弦上的手滑。籁雅不太紧张了,玛丽翘起二郎腿。男孩开始演奏时,我走了出去。”
“我从座位上站起身的时候,既没看籁雅,也没看玛丽。没有什么可解释的,这是一种逃避,要逃离这些孩子的惶恐不安。这些孩子被哄到这里,有人告诉他们,来遭受对手及评委的打量与聆听,非常重要。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二十岁,最小的十六岁。这是一个青少年音乐会,这座城市到处可以见到它的广告,看上去美观、平和,金色粉饰下面是潜在的恐惧,令人窒息的抱负和潮湿的手指。我在路边深雪中跌撞跋涉,远远地我望见等顾客的出租车车列,我又一次想起克洛滕。籁雅从舞台上会看到我的座位空着。我用雪冰了一下脸颊。半小时后,当我湿着大腿步入酒店大厅时,籁雅已经进了等候室。我坐了下来,玛丽一句话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