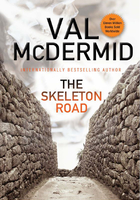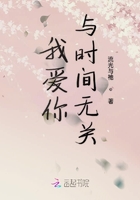他讲道,参赛前的最后两个星期,籁雅可以不上课,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玛丽那儿。玛丽把其他的课都推掉了。他们排练巴赫的奏鸣曲,还一次又一次听帕尔曼[33]的录音,听他如何演奏。有时,她们会练到深夜,那样的话,籁雅就住在玛丽那儿。“那把‘斯特拉迪瓦里’琴太绝了,谁也没法跟它比。”对帕尔曼的小提琴,籁雅说过这样一句。这句话一定一直回荡在梵特的脑际。
有时他梦见籁雅又得湿疹了,有时他醒来,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他梦见籁雅站在舞台上,好像一下子想不起下面该拉什么了。
比赛开始的两天前,我们驾车去了圣莫里茨。那时正是一月底,一直下着雪。籁雅的房间在我的和玛丽的之间。酒店大厅里他们刚刚搭好了台子。看到电视台摄像机时,我们都吓了一跳。籁雅走上台,在上面站了半天,有时用手在裙子上擦了擦。她说,她想现在练琴,于是她与玛丽一起回了房间。
我现在还能感到,那天的雪落到我脸上的感觉。这些雪帮我熬过了那些日子。我租来越野滑雪板,上了路,滑了好几个小时。以前我和塞西尔经常这样做,我们不走通常的路线,常常一言不发地在深雪里留下我们并行的印迹。就是在这样的行进中,我们第一次提到了孩子的话题。
我不能考虑孩子问题,我说。塞西尔站住脚:‘为什么?’
对这个问题我早有所准备,所以我将双手搭在滑杆上,低下头,说出了自己打算作解释的句子。
‘我不希望负这个责任。我不知道怎样对他人负责。我连怎么对自己负责,都还不清楚呢。’
除了这样的话我也说不出别的来。至今我都不知道,它对塞西尔产生了什么影响,她是否听明白了,是否当真对待了。我们结婚刚刚一年的时候,有一天她告诉我,籁雅在肚子里了。我胆战心惊,可她已经成了我的锚,让我不能失去了。
九年前,我最后一次关上塞西尔病房门的时候,动作很轻,好像她还能听到似的。就在那前一天,她说:‘你得答应我,对籁雅你要好好……’我说,‘当然,’我打断了她,‘我会的。’后来我很抱歉,没有让她把话说完。这时,冷风把雪花吹到我的脸上,令我窒息。然后,我快速滑回酒店。
第一次上台演出时,籁雅遭受到怯场的打击,她像遭了一场大病,你对它做不了什么。这其间六年已经过去,她已经掌握了应对方法,比如演出临近时,想些其他的事情,能吸引她注意力的事情来做。如果是在学校演出,那对她非常有帮助并令我惊讶赞叹的是克拉拉和她那伙追随者坐在观众席上。丽丽很生气籁雅能给庆典带来光彩。尽管在跑道上、在游泳池里,每次比赛她都能获胜,她仍觉得这些不足以作为抗衡的筹码。籁雅知道这点,这样当她看到丽丽穿着破了口的衣服,懒洋洋地坐在第一排时,她所有的羞涩都可以一扫而光,尽情享受起这一刻来,那些技术难关,也可以轻松克服,就好像它们从来没有过。
但在圣莫里茨,一切都不同了。如果她能在本次大赛中获胜,那么以后可以考虑开始一个独奏家的职业生活。我是反对这种职业的。我不想被迫看到,籁雅被怎样吞噬在怯场、对新闻的愤怒和对湿手的担忧中,尤其不想每次都为她的记忆发抖。这样的发抖是有原因的,从那次回旋曲上出现错误后,比较严重的错误再没有出现过,没出现过可以跟我在国际象棋比赛时出现过的全线崩溃相比较的错误。琴声也从未被突如其来的忘却卡住过,手指也没有因为不知道下一步该滑向何处而僵住。只是有一次,她演奏一首莫扎特奏鸣曲时,演奏第二乐章前演奏了第三乐章,一时间让观众觉得,她以为第二部分结束,乐曲就结束了。对此,坐在钢琴前面的约尔表现得镇定自若,对这个意外尴尬,给出了一个暖人的慈父般的微笑。‘对不起。’籁雅过后说。我希望,这个‘对不起’我再不会听到,再也不会听到了。
酒店餐厅里,十名参赛者坐在吊灯下,都是一副不把他人放在眼里的架势。十张桌子之间隔着较远的距离,第二天他们都要通过自己的小提琴争取成功。那些参赛者的讲话,在我听来,显得过分生动夸张,他们与自己的老师一起忙碌着,好像要显示对竞争对手的不屑一顾。
籁雅一言不发,时不时地将目光投向其他桌上。她穿着一袭高领黑礼服,那是我在山上滑雪时,她与玛丽一起买的。参赛时她也要穿这裙子,高领会遮住由于紧张引出的颈部红斑。对这些红斑,籁雅突然间不再能忍受,于是她们将事先准备好的那条露肩长礼服放到一边,去买了这条新的。穿上这件新礼服,配上盘起的发髻,她的头颅显出某种修女式的严厉,这让我想起玛丽·居里。
我们第一个离开了餐厅。籁雅进了她房间后,我和玛丽还在走道里站了一会儿。我第一次看到她吸烟。
‘您不希望籁雅获胜,是不是?’她问。我暗暗吃惊,好像偷东西时被人抓到。
‘我这么容易露馅吗?’
‘只要是关于籁雅的事。’她笑着说。
我很想问,她有什么期望值,她对籁雅的机会是怎么想的。她很可能看出了我的心思,因为她扬了扬眉头。
‘那,我们明天见。’说完,我就走了。
夜里,我站到房间的窗户前,还观赏了一阵圣莫里茨白雪皑皑的夜景。隔壁籁雅的房间还亮着灯。我又说了几次对塞西尔承诺过的话——关于要负责任的。我不知道怎样做才算正确。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