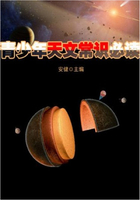祁智
一
这麦子从我的脚下推向前,推到天边,成为一个整块。遇到风,也是整块耸动,像河里的波浪向前涌。那种耸动很壮观,如果是向远处涌去,好像能把天边冲远了;如果是从远处涌来,好像整个麦田会翻卷过来。
我禁不住后退一步。
孙定远拉着我的胳膊问:“小水,你怎么啦?”
“啊——没怎么啊。”我笑着说,“你看——麦浪。”
“麦浪?”孙定远看着我,跳开两步,一脸坏笑,“小水,你是想小麦了吧?”
小麦叫环雪,家在西来街六弄口。爷爷眼睛瞎了,奶奶瘫在床上,爸爸前年在建筑工地摔断腿,家里很穷。妈妈受不了,跟一个在长江上打鱼的渔民走了。男方给了她家一麻袋小麦,大家就喊她“小麦”了。
大家也经常帮助她家,这家在她家门口丢一袋小麦,那家在她家门缝里塞点零花钱。
小麦比我们低一年级。学校排节目,让我和她演哥哥妹妹,要我们手拉手上场。我不肯拉,她也不肯。手拉不到一起,戏就排不下去。我找来一根小棍子,我抓这一头,让小麦抓那一头。
“这像什么样子啊?”校长哭笑不得。
有一天,排节目的时候,小麦突然拉住我的手。她是女生,比我低一年级,但手劲比我大多了,我怎么甩也甩不掉。
“哥哥,你看,朝霞镶满天,红日刚露头。”小麦拉着我的手说着台词。她的普通话很好,声音清脆。
“哈哈哈哈……”看热闹的同学起哄。
我开始被大家笑话,大家动不动就“哥”啊“哥”的。
我恨死小麦了。
后来,刘锦辉打听到了小麦拉我手的原因。她想早一点把戏排完,因为有许多家务要做。
我心里突然原谅小麦了。她的眼睛很漂亮,眼睫毛很长。我从来没有被人喊过“哥哥”,更没有被女孩子喊过。“哥哥”两个字,像两粒水果糖,让我心里甜蜜蜜的。她的手冰凉,还有老茧和裂口。每次拉手,她的手都会在我的手里温暖起来。手一温暖,老茧好像也软了,裂口好像也平了。她的手在我的手里,像一只要飞的鸟。
去年过年,我让妈妈给她做了一件花棉袄。
“妈妈,你不许说。”我竖起一根食指,认真地点着妈妈,“说了,就不是我妈妈。”
妈妈用食指钩住我的食指。“好,我不说。”
“为什么不要说?”妈妈笑着问。
我瞪着妈妈说:“我是男生,她是女生。”说完就跑了。
我确实原谅了小麦。但是,当人家说我和小麦手拉手,我要做出愤怒的样子。
孙定远细声细气地说:“哥哥,你看,朝霞镶满天,红日刚露头。”
“你……你瞎说!”我扑向孙定远。
“小水要抓我啦,快跑啊!”孙定远大叫着跑进麦田。麦子和麦子之间,有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缝,缝下面是田埂。我也跑进麦田。我跑的是孙定远左边的一条田埂。我冲开密密的麦子,就像一条船推开严丝合缝的水。一条条麦穗,像一条条小鱼撞击着我,很快落在我身后。有一些麦粒会飞起来,辣辣地弹在我脸上。我眯着眼睛,阳光下的麦田模糊而明亮。
“布谷,布谷。”一只布谷鸟在麦田上空叫。布谷鸟,你永远不知道它在哪里。它的声音出现在这里,其实已经飞远了。
突然,刘锦辉从我左边的一条田埂上来了。他的速度很快,刚和我并排就跑到了前面。
刘锦辉左边那条田埂没有人,但麦子下面好像有一支箭射向前方。
“汪!”
一条黑狗从麦田里跳出来,像一条乌鱼冲出水面。它是刘锦辉家的狗,叫箭头。箭头兴奋地叫着,又跌进麦田。等它再一次跳出来,“轰——”一大群麻雀腾空而起。
那群麻雀,好像是一大把树叶,被无形的大手抛向了天空。
二
箭头的速度飞快。麦田深处的麻雀,没有一点察觉,箭头就到了它们身子下面。箭头到了,它们并不知道来的是什么,只是本能地惊起。它们刚刚飞离麦子,有的腿还蹬在麦穗上,箭头已经蹿了上来。
“叽喳——”麻雀一起飞起来,先到了一个高度,然后向四处飞蹿。它们乱七八糟地飞过,在我的头顶、耳边刮起飕飕的冷风。
等我松开手,麻雀已经不见了。刚才爆发的一团麻雀,如同一个突然的梦。我愣在麦田中央,孙定远、刘锦辉也愣在麦田中央。阳光照在麦子上,泛起耀眼的金光,无边无际,整块地起伏。
突然,在我们的右前方,一团麻雀轰地飞起来。一定是箭头在麦田底下乱穿,惊动了它们。果然,箭头又一次像乌鱼蹿出:“汪!”
这团麻雀不是刚才的那团,至少不完全是,因为从麦田里还弹出两个大家伙。两个大家伙拖着长长的尾巴。
“野……野……野鸡!”孙定远说。
两只野鸡把翅膀张到最大,滑翔着,像树叶飘过我们的头顶,飘向不远的地方,然后放下细长的腿,“站”到麦浪里就不见了。在它们落下去的地方,又轰起一团麻雀。
麦田里隐藏了多少鸟啊!它们吃掉多少小麦啊!
我忽然想,如果当时小麦家有一麻袋小麦,小麦的妈妈也许就不会改嫁了。
我让孙定远和刘锦辉在田边等我,回家拿了一件军用雨衣,还有一根竹竿。
“小水,又没下雨。”孙定远说。
刘锦辉猜到我要做什么,激动地踏着步。“要演戏了。”
我和孙定远、刘锦辉走到麦田中间。我披上雨衣,让他们一边一个钻进来,再戴上帽子,扣上扣子。我要装扮成稻草人。鸟儿飞到我们头顶,我突然挥动竹竿,像打枣儿一样打它们,至少会把它们吓得半死。
我们三个人,蒙着一件军用雨衣,站在麦田里。热气顺着腿向上涌,太阳在雨衣外面烤。雨衣里又闷又热,像蒸笼。但我们憋住,一动不动。
一群一群的鸟飞过来,好多是麻雀。它们对麦田里突然出现的雨衣感到有些意外,飞上飞下,飞前飞后。我们不敢动,眼珠子跟着转。那些鸟很快识破了我们,落到竹竿够不到的地方。有一只胆大的麻雀,站到我紧握的竹竿上。雨衣里越来越闷热,我们头晕目眩。我刚想挥动竹竿,孙定远热得坚持不住,腿软了,瘫了下去。他瘫下去的时候,抓着我的手。我的竹竿翘了起来,麻雀就像一颗小石子,被竹竿甩了出去。
三
我和孙定远、刘锦辉坐在腰沟的河堤上。我们想让麻雀上当,却弄得自己满脸痱子,又红又痒,样子还很滑稽。
桐村由两个一前一后的村子组成。前面一个村子有七个组,我们这个村子有六组,每组四五十户人家。我家在八组东边,靠近西来镇;刘锦辉家在八组最西边,靠近九组。村子由东向西。村东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小桥。桥东对着西来镇六弄口,小麦家就在那里。
西来的村子,都叫埭。埭是土坝的意思。很早以前,这里还沉浸在长江里。后来江水后退,老祖宗筑坝,在坝里边建房子、种地。江水继续后退,老祖宗又在前面筑坝。
腰沟东西走向,和埭平行,夹在埭和埭的中间,像一个人的腰。腰沟是埭的分界,也方便灌溉。
“我们扎稻草人吧。”我说。
孙定远问:“为什么要扎稻草人呢?”
“赶麻雀。”我侧着身子说。
孙定远问:“赶麻雀?为什么要赶?”
“呃——”我说,“它们偷吃小麦——是……是真小麦。”
“小麦?小麦还有真假啊?哪个是真小麦,哪个是假小麦呢?”孙定远指着我说。他转过脸,对刘锦辉说:“小水又说小麦,小水就想着小麦。‘哥哥,你看,朝霞镶满天,红日刚露头。’”
我瞪着孙定远。他绷紧身子,做出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不过,我现在不打算找他算账。我笑着说:“那么多鸟,吃多少小……小——粮食啊。”
“小——粮食?小麦吧?”孙定远坏笑着。
我挥着手说:“那么多麻雀呢。”
“那么多小麦呢,还怕几个麻雀吃?”孙定远也挥着手,比我还用力,“不对,小麦就一个——”
刘锦辉推推孙定远,要他别说话。
我站起来说:“我们扎稻草人。每人扎一个,排成一排——”
“啊呀,好……好啊!一……一直……直排到……到天边……边。”孙定远跳起身,手指着远处对刘锦辉说,“螳螂,你跑!你跑得快!你一口气跑到天边。”
刘锦辉激动得满脸通红,紧张地搓着手。“天边?天边在哪里?”
“在那里——”孙定远指着西边说。
向东一眼看到西来镇,向西是看不到边的麦田。麦田就像一条河,流向遥远的地方。
刘锦辉揉揉眼睛说:“那不是天边啊。我有一天跑了很远,跑到八圩了,天边还是那么远。”
“跑到跑不动了,看到的就是天边。”孙定远有把握地说。
我笑着说:“那得扎多少稻草人啊?”
“呃——”孙定远抓抓头发说,“是啊。”他看看四周又说:“要不这样,到我们组的尽头吧。”
我一挥手,孙定远和刘锦辉跟着我,在腰沟上狂奔。
腰沟两岸,有一些杂树。河滩上种着蚕豆、油菜。蚕豆花和油菜花都谢了,豆荚和油菜籽荚开始饱满,一条条听话地垂挂着。风一阵一阵,一阵凉,一阵热,带着说不清的香味。
“啊呀快看,那里——”孙定远指着腰沟下面说。
腰沟下面有一条土路,从腰沟下面通到埭上刘锦辉家门口。这里是八组和九组的分界。组和组之间的农田,靠宽一点的排水沟或者宽一点的土路分开。
土路和腰沟连接的地方,插着一个稻草人。
四
稻草人绑在一根竹子上。扎稻草人的麦秸秆是去年的,光泽不明显了,但稻草人是新扎的。一根根麦秸秆整整齐齐,像一个人很认真地梳了头发。扎稻草人的绳子,捆得很认真,也很匀称,每根绳子之间的麦秸秆,都像一节藕。
“咦?”孙定远摸着稻草人的手。稻草人的手,不是平直地伸着,和身体成一个十字架,而是垂在身体两边。
孙定远把稻草人的手臂向上扭。扭上去就垂下来,再扭,还是垂下来。他看看我们说:“坏了吧?”
“不是坏呢。”刘锦辉蹲下去,把手臂摆到原来的位置上。双臂一前一后,像一个人走路的姿势。
“你怎么知道的?”孙定远问。
刘锦辉红着脸,搓着手,两条长腿轮流提着。
箭头好像知道刘锦辉受到了表扬,呜咽着,龇着牙,翻了一个跟头。
我仔细看着稻草人。一般的稻草人,都是随便抓一些麦秸秆、稻草捆捆扎扎,乱蓬蓬的。这个稻草人却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很有精神。
“看这里——”我指着稻草人的脖子。
稻草人的脖子上,有一条用麦秸秆编的细项链。
“真像啊。”我摸着项链说,“像一根金项链。”
“不要——”刘锦辉突然说。
我吓得缩回手。“不要?怎么了?”
“没——怕弄断了。”刘锦辉绞着衣角说。
“这是哪个做的啊?”孙定远点头,“哪个把稻草人编得这么好,还编金项链。”
田野里没有人,太阳已经升得很高。阳光更加明亮,每一粒都在麦叶、麦穗上跳跃。麦田像潮水涌向天边,无数的麦穗,像赶着潮水的一条条小鱼。
我拔出稻草人,扛在肩上。
五
“就按照这个样子扎。”我指着稻草人说。稻草人插在空地上,像一个人站在我们面前。
箭头听懂了我的话,低头摇尾向草堆里钻,咬出一嘴稻草。孙定远接过去,闻闻,捂着鼻子给刘锦辉。
“霉的。”刘锦辉也闻了闻,丢到草堆上。
到哪里去找那么好的麦秸秆呢?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有草堆。但都是去年堆的,已经垮塌、缩小了,草色灰暗,一股霉味。
“这么好的麦秸秆,肯定是一根一根选的,要选好长时间。”我摸着稻草人说。
孙定远闻闻稻草人。“一点霉味都没有,就是麦秸秆的味道。”
霉烂的草堆让我们垂头丧气。
麦田在微风下,波浪缓缓起伏。麦田上空,蓝天辽阔。埭上升起一柱柱炊烟。炊烟直直地向上,在很高的地方飘散。
孙定远说:“要这么认真扎一个稻草人,干什么呢?”
“有人正好没事,就扎了一个稻草人。”我说。
“……”刘锦辉张嘴又合上,然后点点头。
孙定远看看我,看看刘锦辉,也点点头。
我们推翻好几户人家的草堆,拣一些好一点的麦秸秆,一人扎了一个稻草人。
刘锦辉扎得很认真,头上加了两根辫子。我想说你怎么扎了一个女的,话到嘴边咬住了,因为我看到,我无意中扎的是一个男的。男的肚子有点大。我忽然明白,我扎了一个“爸爸”。
我的爸爸在兴化做老师,放暑假和寒假时,他会坐船、坐汽车回到西来镇。假期快结束了,他会再坐汽车、坐船去兴化。
刘锦辉扎的,一定是他的妈妈。他刚生下来,妈妈就死了。他爸爸刘油果抱着他,一家一家讨奶吃,他才活了下来。
我偷偷地看看孙定远,怕他点破刘锦辉的用意,让刘锦辉伤心。他手忙脚乱,没注意我们的稻草人。他扎的稻草人还没绑到竹竿上就散了。有一些草没绑住,披披挂挂。他往下撸,越撸越多,稻草人身上的草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一根竹竿。
“哈哈哈哈……”孙定远很开心,“光杆司令。”
太阳当头。麦田的气温升高了,我们的腿热得麻酥酥的,胸口被热气蒸着,呼吸发烫。拔来的稻草人,被我们插在最靠路边的地方。路过的人看到了,一定会说这么漂亮的稻草人啊。然后插刘锦辉扎的,再插我扎的。
孙定远扎的稻草人,被插到麦田中间。他扎的稻草人,松松垮垮,远看还马马虎虎。
六
“不……不见……见了!”孙定远跑到我家说。
我问:“什么不见了?”
“稻……草人。”孙定远说。
“你的?”我笑着说,“你的稻草人谁要啊?”
“不不不……是我的,是偷……偷……偷来……来的。”孙定远说。
“偷——”我明白了,“那个是吧?”
孙定远拉着我去麦田。
我只看到了三个稻草人,靠路边的那个稻草人不见了。
“呜——”箭头到了我们脚边,快得像从地里钻出来的一样。
刘锦辉迈着长腿也到了。
太阳偏西,但光芒没有减退。麦田在逆光中向西铺开,麦子像被融化成了糖稀。天边和麦田相接的地方微微泛黄,好像糖稀把天幕洇湿了。
“那个不应该插在路边的。”我说,“插麦田中间就好了。”我对孙定远说:“把你扎的插在路边,就不会被人拔走了。”
“呃——”孙定远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扎得再好,也还是稻草人。”
“那也是人啊。”刘锦辉说。
孙定远说:“是人,是稻草的人。”然后,他像踩着弹簧一样跳起来,什么也不说,就向西奔去。
箭头竖起头,判断了一下,嗖地钻进旁边的麦田。
孙定远很快就跑到那条土路上,转身向南,向腰沟跑去。
箭头突然从麦田里钻出来,像一个影子闪到腰沟上。
孙定远到腰沟下面了。他弯下腰,又站起来,举着稻草人向我们晃。
我和刘锦辉跑过去。
“稻……稻……稻草……人……真有不……一样的。”孙定远结结巴巴地说,“它……它它它……会……自己……走走走。”他没说完就笑了,指着竹竿问刘锦辉:“它就一条腿,怎么跑?”
“它……它跑不用腿的。”刘锦辉说。
孙定远两条腿把箭头夹住。“对。仙人,会飘,会飞,不会走。”
太阳挂在西边的半空。没有风,麦田像平静的河面。麦田上有几只鸟在飞。
我看着土路、腰沟、埭。稻草人不会自己走的。即使自己走,那它是哪个扎的呢?稻草人不会自己扎自己吧?
我忽然有了一个想法。我拔起稻草人,扛回来,还把它插在路边,然后爬到桑树上。孙定远和刘锦辉跟着爬了上来。箭头在树下跳着。刘锦辉向它摆摆手,指指麦田。它兴奋得翻了一个跟头,压低身体,扁平着退进麦田,隐在麦秸秆后面。
“布谷,布谷。”一只布谷鸟在头顶叫。抬起头,却什么也没有,只有干干净净的天空。
太阳慢慢向西,风向转了。夕阳下的麦田,整块地耸过来,就像一个躺着的巨人,突然要站起身。无数的鸟,在晚霞中成为斑斑点点,飞向埭上的竹林。
七
稻草人,一大清早又不见了。
我忽然想到了腰沟,急忙向那里跑。清早的土路,被两边麦子上的露水打湿,有些滑。一些会跳的虫子,唧唧唧唧地弹起来,落到麦子里。湿重的麦子低垂着头,一个个像不肯醒的样子。
箭头跑得比我们快,尖起脑袋就没了影子。等它再一次出现,已经到了腰沟那里。
“汪汪汪——”箭头卖力地狂叫着,一定是发现目标了。
我们赶到腰沟下。
稻草人站在原来的地方。
这真是怪了!孙定远的脸皮绷得紧紧的,喘着气站到我身后。我一把抓住他的衣服,生怕他要跑掉似的。
刘锦辉搓着手,两条长腿原地踏步。
箭头很知趣,跑到腰沟上。它贴着一棵杨柳树站着,竖起耳朵、夹着尾巴张望。
“唔——”箭头发出低沉的声音。它是在提醒我们,有人来了。
我们慌忙蹲下来,使头低过麦子。
“螳螂,你听出来没有,哪个?”孙定远问刘锦辉。
刘锦辉侧着头、皱着眉,认真听着。他的耳朵很灵,能比我们先听到很远的地方的声音。他抬起眼皮说:“是——”他看看我,说:“小麦。”
“呃——嘿嘿嘿,小麦!”孙定远对着我坏笑。
“小麦怎么了?”我对孙定远说,“你就知道小麦。你喜欢她啊,你拿去。”
“你喜欢她啊,你拿去。”孙定远学我说话,又说,“你让我拿去就拿去啊?她是你的啊?她听你的话啊?”
“去!”我瞪着孙定远,眼睛慢慢露出麦田。平着麦田看出去,小麦从很远的地方走来。她只比麦子高一个头,就像水波上漂来一顶帽子。我有些心慌,脸上发烫。
“哎哎,你抓我干什么?”孙定远晃晃衣袖说。
我讪笑着松开手。“不能抓啊?”
“嘿嘿嘿,”孙定远滚到我够不到他的地方,“你以为我是小麦吧?”
刘锦辉小声问我:“怎么办?”
“跑……跑跑……跑!”孙定远撅起屁股。
我想说跑,但两腿发软。我看到隐在麦子后面的墒沟,猫腰爬了进去。
八
阳光透过麦子,灌进墒沟。麦秸秆细密地站着,在顶部合拢,把我们掩盖住。几只小甲虫在麦秸秆上爬上爬下,忙忙碌碌。墒沟里密不透风,又闷又热。我们大汗淋漓,像蹲在越来越烫的水缸里。
“小麦来了。”刘锦辉小声说。
我赶紧低下头。箭头看看我们,身子扁着伏在地上,舌头伸出来像一只鞋垫。我听到有人走过来了,走路的时候碰着麦子,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那人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住脚步。然后,那人深吸一口气,又重重地吐出,清清嗓子说:“哥哥,你看,朝霞镶满天,红日刚露头。”
是小麦在说话,她的声音很清脆。
我像背后被猛地推了一下,头压得更低,嘴差一点就要啃到泥。地上有一棵麦穗。我忽然发现,麦穗像小麦漂亮的眼睛;麦芒长长的,像小麦的眼睫毛。我心一慌,赶紧闭上眼睛。
孙定远一定在笑,只是把笑声忍住了。他整个身子都在笑中抖动。
过了一会儿,小麦好像走了。我们连滚带爬出了麦田,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以为孙定远会取笑我,但他不看我,手在地上乱划。刘锦辉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孙定远,嘴张开又闭上,张开又闭上,长腿踏来踏去。
“呃——”我说,“呃——”
“哈哈哈哈——”一阵大笑,从孙定远的嘴里喷了出来。
“你……你笑什么?”我问。
孙定远模仿小麦的声音说:“哥哥,你看,朝霞镶满天,红日刚露头。”
“这说明什么呢?”我心虚地说,“这……这是节目里的词。”
孙定远说:“哥哥——她可是背后喊你哥哥哦。”
“我?怎么是喊我呢?我和她——有仇。”我着急地说。
“你和她有仇?有仇还和她拉手啊?”孙定远说。
我跺着脚说:“是她拉我的手,坏了我的名声!”
“坏名声?心里美滋滋的。”孙定远向刘锦辉眨眼。
“我……我……”我左右看看,寻找着什么。我忽然看到了稻草人。
稻草人站在麦田里。
我冲进麦田。麦子一棵棵拦住我,我就像在水里走一样困难。我弯腰用双手撸开麦子,用力踩出每一步。麦子被我踩倒一大片。
刘锦辉害怕地说:“小水——”
我拔起稻草人,脚踩着,手拽着。麦秸秆捆扎得很紧,撕扯不动。细麻绳勒紧我的手指肚,我的手指快要断了。
“你你你……你疯啦!”孙定远带着哭腔说,“我……我……我说……说……说着玩的。”
刘锦辉从后面抱着我,把我的双手紧紧箍住。箭头咬住我的裤脚,向后拖。
有人拉我,我更来劲了。我身子猛地一扭,把刘锦辉甩开。我不扯细麻绳了,扯麦秸秆。麦秸秆很快被我抽散,一根根躺下,和倒伏在地的麦子混在一起。
“你不是说我美滋滋的吗?”我指着地上的麦秸秆,很开心地看着孙定远。但不知怎么的,我的双手在抖,心里想哭。我想起小麦的手,她的手上有许多老茧和裂口。我还想起一麻袋小麦。
“哇——”刘锦辉哭了。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哭声很响。他哭得脸都变形了,脸上只剩下一张嘴。他又弯下腰,抱起散乱的麦秸秆,着急地跺着两条细长的腿。
刘锦辉的哭,把我和孙定远、箭头都吓住了。我和孙定远都觉得奇怪,小麦的一个稻草人,怎么会让他这样伤心?
孙定远结结巴巴说:“螳……螳……螳螂,你怎……怎么……了。”
“哎,你……你哭什么啊?”我拉着刘锦辉的肩膀问。
“小麦啊——”刘锦辉大声哭着,“小麦……扎的……”
小麦的妈妈改嫁去了八圩。八圩在长江边,在桐村西南边。每到换季的时候,妈妈都要悄悄给她做一双鞋子,再托人带给她。今年春天,妈妈带给小麦的单鞋偏紧。她长大了,妈妈估摸不准她脚的大小了,就托人带信,昨天或者今天傍晚,来拿她脚的尺码,地点就是插稻草人的地方。
“托人?”我想起来了,刘锦辉的姑姑家在八圩,“那人是你吧?”
“螳螂,稻草人每次是你送回来的吧?”孙定远问。
刘锦辉没有回答我们的话,忽然像想起了什么,蹲到地上,拨拉着麦秸秆。“那个呢,那个呢,那个呢——”
“呜——”箭头一个箭步扑到前面,咬起麦秸秆编成的项链,一转身跳起来,把项链送到刘锦辉手上。
“这是尺寸,小麦脚的尺寸。”刘锦辉擦着眼泪和鼻涕,张开嘴笑着说。
九
我和孙定远、刘锦辉新扎了一个稻草人。我们扎的稻草人,不如小麦扎的好。好在小麦的妈妈来的时候,天黑了,看不清稻草人的好坏。
我把那条麦秸秆项链,小心地围在稻草人的脖子上。
我们把稻草人插到麦田里。
太阳落山了。天和地相连接的地方,飘起了一条长长的红绸带。麦田上空,天色灰蓝,已经有了几颗眨眼的星。几只迟归的鸟,鸣叫着,急急地飞,隐进埭上的树林和竹园。麦子向西铺展,暖暖地伸进晚霞。清甜的麦香,就像水面的蒸汽,一丝丝,一缕缕,缠绕在一起,混合在一起,让人很容易想到满晒场的麦子。
我们默不作声,跟着箭头,沿着土路向埭上走,像三个移动的稻草人。
“布谷,布谷——”一只布谷鸟,在暮色里飞。
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喊“哥哥,哥哥”。
选自江苏《少年文艺》2016年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