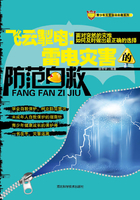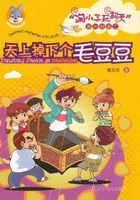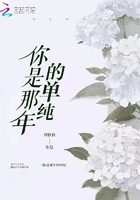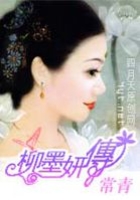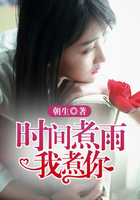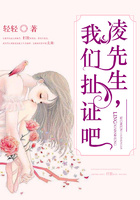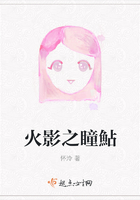周伟
阳光的味道
阳光下的奶奶,总是一脸阳光地坐在禾坪上,看着她那禾坪前的瓜蔓引蛇一般爬上瓜架,攀绕,慢慢地绿了一片,然后,一朵小黄花开了,又一朵小黄花开了。
不几天,那一朵朵好看的小黄花,一朵一朵地不见了。我找来找去,只见瓜架下凭空多了好多长长短短的青瓜,长者四五寸,短者二三寸,一律悬挂,如漫天挂满了纺锤和棒槌。
我在瓜架下走来走去,或看或摸,或量长短,或比画大小,或做上记号。忽然,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便向阳光下定坐着的奶奶箭般直飞而去。我着急地问:“奶奶,你看你看,为什么它一出生就满脸皱纹,疙里疙瘩的?”
我双手捧上瓜伸到奶奶的眼皮底下,阳光下的青瓜原形毕露,却一点儿不害羞不怕生,安详无语。
奶奶呢?她也只是笑,边笑边摸那瓜,一遍又一遍。布满皱纹的瓜,竟在奶奶的手上很滑润,有光泽,好听话。
我从奶奶手上把瓜拿了过来,说,它肯定委屈。准是哪一朵童谣花早早地谢了,它心里烦啊苦啊!
奶奶的笑僵了一下,我瞬即看见苦瓜的皱纹在她的脸上闪了一下。
我的猜想不久便得到了证实。奶奶摘下那瓜做菜,一片刚夹到我的嘴里。我就嚷了起来:“苦,苦死了!”从此,我再也不肯吃苦瓜。
后来有一回,奶奶让一个红辣椒糖逼我就范。奶奶笑着看我,说:“多呷几片,然后,回味回味看。”
奶奶手中的红辣椒糖在我眼前晃荡。我夹了一片又一片苦瓜,放在嘴里。我想那时我是闭了眼的。
味还是苦。当苦味渐渐淡去时,一种微凉并略带甘甜的味儿便升到了舌尖、口腔,随后就觉得清爽、痛快和惬意。肉厚脆甜,味道清香绵长。
奶奶还说,别看它有些苦,能除邪热,解劳乏。
我并不管奶奶说的,只是想着,这瓜,以苦味得名,能食能医,只是苦了它自己。
奶奶对苦瓜情有独钟,变着法儿给我烹调苦瓜:素炒如青菜,油煎如荤菜,还可熬成苦瓜瘦肉汤,鸡蛋炒苦瓜……最妙的要数苦瓜肉丸,将苦瓜切成一寸长的筒块,挖去瓜瓤,放入沸水中用旺火煮至半生时捞出滤干水分;再将瘦肉剁烂,加入葱花、盐,掺入薯粉,拌匀作馅;把粉团肉馅塞入空心的苦瓜筒块中,再入油锅煎,待筒块两面的粉团肉馅略呈黄色时,掺入汤、姜、大蒜头一并煮熟,起锅前放盐与味精。苦瓜清凉,瘦肉鲜甜,色美味香。
此后,我更是日日都要去瓜架下看那些宝贝疙瘩了。奶奶依旧天天坐在阳光下的禾坪上。瓜架下的瓜一日日变大,青皮愈来愈黄了。
有一天,我看见一条瓜裂开了很大的口,露出了里面的红瓤。我马上摘下,立马送到奶奶的面前。
奶奶随着裂口把瓜完全撕开,露出更多更漂亮的红瓤里子。奶奶撕了一块红瓤放到我的嘴里,笑着看我,说:“你尝尝看。”我不敢大嚼,只是用舌头舔了一下,竟然,很甜!
我不禁替这瓜感叹:想不到,它在最后竟是以爆炸自己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鲜艳和甘甜!
我发觉自己在太阳光下迅速地成长,当然这成长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在味道上的成长。我对味道愈来愈有感觉、经验了。
比如对苦瓜,我就慢慢体味出苦味之后,着实可去烦消渴通便,清心明目益气。更有感动处,苦瓜是苦的,情爱是苦的,人生是苦的,真正体味出,总会苦尽甘来。
许多年后,奶奶葬在了她的苦瓜架旁,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在那天,我才完完全全地知道奶奶是个苦了一辈子的人。她儿时父母早亡,八岁起给人做丫鬟帮工,后来嫁给地主做小老婆……
在大伙的印象中,奶奶总是坐在屋前的禾坪上,一脸阳光地招呼着来来往往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们。搬个凳子,要你坐;端杯茶水,要你喝。带个东西捎个口信,她都代劳,且负责得很,从不出错。下雨天,她要借把雨伞给你;炎炎夏日,她要借顶草帽或斗笠给你,随你什么时候来还。碰上吃饭的时候,算你有口福,一定邀你入席。缺个油盐酱醋茶,娃儿读书还差几个学费钱,大多都找奶奶借……仿佛奶奶总是一个有说有笑的“观世音菩萨”,带给别人的尽是欢乐和甘甜。
那天我回到了老家,走在苦瓜架下,我看见一朵小黄花开了。
离开苦瓜架旁,我好像忽然听到一句:天燥热,来碗苦瓜拌稀饭!这是奶奶的声音,好亲切好温馨。
一地阳光雨露
一个人,身边总拢养着一个人。看他睁开双眼,打量四周,欢蹦乱跳,跃上枝头,喊住春天,憧憬秋实……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草露花开,香飘四季,风流云散。
奶奶就是。
奶奶一生没有生育,身边却总拢养着一个人。那会儿,是四哥。四哥是奶奶在匡家的第四个外孙。匡家是奶奶过去的婆家,家大业大,后来一声喊,说败就败落了,一个家四散开了。奶奶来我们周家时捎上了四哥。三岁的四哥皮包骨头,一身软塌无力,抻一下,再抻一下,如一根细线松紧般拉长又缩短,奶奶就觉得心一紧一松,一收一缩,隐隐地作痛。
不管四哥的身体如何不争气,奶奶笃定要把他拉扯得直苗条条、高高大大。奶奶天天把四哥拢养在身边,不停地按摩、拿捏着,奶奶总是有无穷的劲。家里没有什么舍不得的,能吃的吃,能换的换,能卖的卖。
看着地上堆雪人的四哥,奶奶见四哥整个儿一团雪。
好久,四哥起身,环顾天地,雪天一色:打量自个儿,全身披满雪花,热气腾腾。
奶奶立在不远处,冻成一蔸雪地里的白菜,郁郁葱葱。
四哥总爱玩水,奶奶总是担心。每回奶奶都必跟着。
奶奶总是先挑一处小溪。清清小溪,水在石上流,鱼虾水中游。奶奶总是先挽起裤腿下到溪涧试水,再把四哥剥了个笋白,然后用湿手在四哥胸口上拍三下,如此停当,方可放四哥入水。奶奶这时仍蹲在水中,定定地看着水中光溜溜的四哥。四哥玩得兴起,早已忘了身边的奶奶。水,被他旋成浪花朵朵,泼洒成一地碎银,水淋淋、湿漉漉的,飞溅了奶奶一头一脸和全身,奶奶笑了。
在四哥的记忆中,他儿童的天空里总是风雨较多。他常常见着奶奶在那样的日子里被牵到大队部去“听课”“做作业”。奶奶不像别人一样落魄邋遢,总是穿戴得齐齐整整、干干净净,手里总牵着他,镇定自若。
奶奶“听课”“做作业”时,总把他拢在身边,拿一本图画书让他描画。他清楚地记得那本毛边破损的书里有一幅美丽的画图,他描着描着,就像真的一样。
春天来了,灵性的油菜花开了,开了!明晃晃、懒洋洋的阳光下,大地被渲染成一望无边的金黄。四哥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嗡嗡飞呀飞的小蜜蜂,一朵朵,一簇簇,飞上这朵,又飞上那朵,再飞旋开去,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和中间。他不觉得累,他只感到美,美得华实,美得震撼;他只感到幸福,幸福得无边,幸福得眩晕。
四哥有水桶高的时候,奶奶特意为他打了一对小水桶。
有一天,奶奶说,从明早起,自己起来挑水。四哥晓得,他挑不挑水,家里都是有水喝的,每天五伯大清早都挑得缸满桶满。当然,奶奶定有奶奶的意思,他只管等着奶奶的絮叨。
果然,每天天不亮,奶奶就催他下床挑水。奶奶说,越早水越清,越早水味越正。踏着露水时,奶奶又说,看,粒粒珍珠呢。第一回挑水,四哥挑了大半桶,水总是淌出来。第二回,他就少挑了许多,想是不会淌出,挑起来,一路轻快,还是淌出来。第三回,奶奶开始絮絮叨叨,把桶子里的水满上,再看看。四哥依了,竟然没淌出来。奶奶说,看看,一桶水不淌,半桶水淌得厉害。
挑水回家,一身汗,四哥伸勺一舀,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干,手一抹嘴上的水珠。奶奶笑着问,甜吗?四哥一回味,果真甜!以前怎没觉出甜来哩?奶奶像是替他解答:自己挑的就是甜。
四哥后来长得直苗条条、高高大大离开奶奶,走到天远地远的广州大亚湾闯世界,有好几年难得回来看奶奶。有人问奶奶,有没有四哥的音讯,晓不晓得四哥在那边的情形。奶奶就满院子里跑,跟这个跟那个,有鼻子有眼地唠叨,细数着四哥一日三餐的枝枝叶叶,夸张地形容着四哥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大家都惊讶于奶奶的梦幻。奶奶说,我有根线牵着呢,四毛伢子在外头只要稍稍动一下,我能不晓得?大家还能说什么,时时刻刻,那根无形的线,一直拴在奶奶的脔心尖尖上。
四哥在远离奶奶的日子里,常常半夜里无由地爬起来,久久地木坐在床上……他好像听到,有人一声声亲切地唤着他的名字……窗外,月光如水。
天上,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星的眼,漫天的星眼,眺望着,眺望着远处,万家灯火通明。
地上,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一个个人行走在路上,匆匆忙忙。但是,没有谁的心上不念想着一个最亲最亲的人和那方生命中最美丽的天空?因为,生命深处的颤动,总是绵绵无绝期。
明天,月白日出,又是一地的阳光雨露。看啦,瓦檐上的几根小草,正在伸展着身子。
阳光故乡路
故乡的路程其实很近,却离我很远。
我站在笔直的水泥村道旁,望而却步。当俯下身来时,我看见成群结队的蚂蚁。顿时,我觉得自己渺小得就像一只蚂蚁,甚至还不如一只蚂蚁。它们也许小得只是一只蚂蚁,也许贱如草根,却总是无比地勤劳、团结和强大。潮湿、温暖、肥沃的土地,是它们的安身之处、立足之地、生命之本。你看看,一只只蚂蚁,总是一起工作,一起建筑巢穴,一起捕食。一个个,拉的拉,拽的拽,即使是一只超过它们体重百倍的螳螂或蚯蚓,也能被它们轻而易举地拖回巢中。它们尽管没有飞翔的翅膀,但从低处爬行,也能跃上树枝,登上高楼。
有一天,我读到美国学者吉姆·罗恩说过的一段话,他认为蚂蚁有令人惊讶的四部哲学。第一部:永不放弃。第二部:未雨绸缪。第三部:期待满怀。最后一部:竭尽全力。这是多么令人叹服的哲学!读完,我的心灵也为之一颤。
原来,我远不如一只蚂蚁。蚂蚁有很强的求生欲望,我们常常看见被水淹没的蚂蚁,它们总是努力地挣扎,拼命地爬上爬下,找寻生命的出口,脱离危险和困境。是的,热爱生命的蚂蚁启示我们,我们也应该热爱自己宝贵的生命。生命是短暂的,生命更是美好的。感受生命,珍爱生命,生命之花才会盛放出永不凋谢的花朵……
然而,小时候的我最讨厌蚂蚁。对于养蚕,我却很上心。奶奶常常抚摸着我,笑说我像一个蚕宝宝:白白的,肉肉的,胖胖的,嫩嫩的。奶奶见人就说,宝宝馋,宝宝蚕;馋宝宝,蚕宝宝,饱养蚕宝宝呢!奶奶还说我跟蚕宝宝一样,整日吃了睡,睡了吃,养得白白胖胖,滑嫩光鲜。奶奶说,尽管那时候日子过得紧巴,一家人总是勒紧裤带省下来给我吃。奶奶还跟人说,养蚕宝宝跟养儿没有什么两样,都娇嫩得很,冷不得热不得。冷时,要用干柴干草给蚕宝宝取暖。这样,蚕宝宝才会长得快,长得好。
如奶奶说的一样,转眼间我也长大了。长大了的我来到了城里,来到城里的我似乎忘记了蚕的生长全过程。或许是我只记得饱养蚕宝宝的幸福和快乐,或许是奶奶没有跟我细说蚕长大后破茧成蝶的道理。其实,我应该早就知道的,只是孩童时的我贪玩,懵懵懂懂。及至我在学校里才学到这样的书本知识:长大了的蚕,过了一段时间后便开始蜕皮。约一天的时间,它不吃不睡也不动。蚕经过第一次蜕皮后,就是二龄幼虫。然后每蜕一次皮,就增加一岁。通常,蚕要蜕四次皮,成为五龄幼虫,才开始吐丝结茧。这时,五龄幼虫需要两天两夜的劳累才能结成一个茧,并在茧中进行最为痛苦的最后一次脱皮,成为蛹。最后,蚕破茧而出约十天后,羽化成为蚕蛾,破茧而出,获得新生。
破茧成蝶,无疑是心灵的一处驿站,是生死轮回的一个美梦,是生命的一次复活,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为了美,为了自由,为了大爱,为了希望……蚕能破茧成蝶,况且人乎?于我来说,一切一切的困境和痛苦,又有什么可怕?放眼望去,大地上到处都是一个个白茧,圆圆的,温润的,晶莹透亮,光彩夺目。
我沿着小溪走出村庄,小溪还是那样缓缓地流淌,悠悠地哼唱,阳光一点儿一点儿地追赶着,一路走走停停,听小溪不停地歌唱。看行云流水,看春光点点,看万物淡然……远处,有三两孩童骑在牛背上,一个个悠然自得,带着晚霞一起回家。他们的背后是绵延的大山,安宁而又平和。
选自《儿童文学》(经典)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