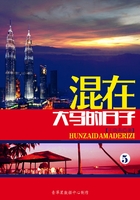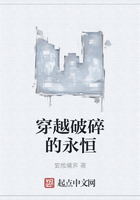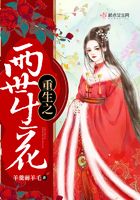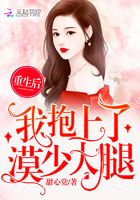自1898年,小仲马的《茶花女》由林纾翻译过来“断尽支那荡子肠”之后,法国文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而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读者、译者和学者一直在不断地续写法国文学“来世的生命”,创造法国文学与新语境、新读者一次又一次的相逢际遇。
倘若把外国文学在本土的“移植”看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完整的译本出现之前,往往有对某个文本、某个作家的介绍和分析,或是节译;紧接着,在第二阶段,出现了完整的译本,这是基于第一阶段的铺垫之后,在译者、接受环境都有所准备的前提下的进展;第三阶段,基于完整的译本之上,才会有对该文本的接受与研究,文本才开始在异域的土壤中绽放另一段“来世的生命”;最后一个阶段,随着对该文本研究的深入,可能会出现新的译本——在某种程度上,新的译者在重新翻译的过程中,其立场和视域也正是受到了新的研究成果的影响。虽然从“移植”的理想过程而言,这四个阶段彼此衔接和更替,但是具体就某一部作品而言,因为目的语接受环境的变化,四个阶段不一定是完整的,四个阶段之间也不一定是泾渭分明的。它们彼此之间有可能出现长时间的停滞,“移植”阶段有可能不完全,也有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里,出现了两种“移植”阶段彼此交叠的状况。
我们旨在考察从一个多世纪以前开始,法国文学在中国所走过的历程,考察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主体对法国文学作家、作品所作出的阐发与研究。我们拟将法国文学在新中国的100多年放置于上述“长期过程”的框架中加以考量,因此,法国文学的译介、翻译和研究,都是我们考察的对象。当然,我们的重点是在不同的时期,中国的译者或者学者基于原本或者译本的批评。为此,我们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在此加以厘清的,因为关乎到该课题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第一个方面是:如果说我们是要对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作出考察,也就是说,属于学术史研究的范畴,那么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是怎样的一个概念?事实上,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外国的本土文学研究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包含翻译、介绍的过程,而且译介占有相当分量的比重,它也是外国文学与中国不同时期接受环境得以遭遇,从而产生新的碰撞和思考的前提,也就是说,它更属于世界文学的范畴,并且,无论其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时代的,却总包含所谓“当代性”的成分在其中。第二个方面是: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法国文学之于外国文学的关系是怎样的?总体而言,法国文学的研究当然是被置于外国文学研究的框架之下,但是,法国文学的研究有不同于其他国别文学研究的地方吗?第三个方面是:在不同的时期,法国文学在中国遭遇到了怎样的接受视野,从而又成就了怎样的研究结果?中国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环境又在何种程度上决定法国文学研究的数量和质量?
一、法国文学?翻译文学?
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其他国家的外国文学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其他国家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两种途径:一是区域研究。比如汉学,包含某一特定语言辐射区域内的所有“文化”概念(哲学、史学、文学或者社会经济等)的研究。二是从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我们都知道,区域研究无论其领域如何,主要依据的材料都是所研究区域的原文资料,而比较文学依据的文本则包含原本与译本两种。就研究途径本身而言,其他国家的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并无实质区别。不同的只是在中国,文学研究从传统上而言与区域研究之间界限分明,区域研究通常并不包含文学的研究,彼此之间甚少融合。
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国的文学翻译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或许与其他国家的文学翻译历史相比,尤其是与处在多语言区域的欧洲国家相比,并不算长,但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外国文学“进口量”却是空前的。究其原因,或许有这样几点:首先,中国文学翻译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且很快与汉语语言和文学的巨大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几乎在其他国家的文学翻译史上都不存在。[1]其次,与第一点也不无关系、互为因果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翻译高潮中,担纲文学翻译事业的是中国的诗人、作家。他们不仅承担起翻译与创作的责任,还同时承担起文学变革与社会变革的使命,是“新身份”的构建者。再者,尽管就这100多年的历史来看,在不同的时期,翻译文学与汉语文学之间的关系有时显见、有时隐身,但是,总体而言,当汉语文学与其语言传统和文化传统在激变中进行了“决裂”性的告别之后,翻译文学在100多年里一直对汉语文学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这也就意味着,因为这100多年以来中国文学翻译的数量与质量,同时也因为文学翻译与本土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因为近30年以来中国译介学的发展,在中国已经提出了有别于外国文学的翻译文学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我们理解,外国文学进入中国之后,在翻译的阶段就已经发生了语言与文学、文化的碰撞和改变。而这种改变,对我们从更多的角度来考察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指出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的这个前提,在我们看来尤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从法国文学研究的构成者上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假定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环境与法国本土的法国文学研究环境是一样的。倘若忽略了这个前提,我们的法国文学研究最终将走向无意义。一方面,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正是基于“视域融合”和比较的意义才得以存在,并且必须存在。它也是外国文学“来世的生命”的一部分。另一个方面,在法国文学研究的成果中,绝大部分是从事法国文学的译者来完成的。我们对此所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他们对原文的了解和研究会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普遍状况一样,直接决定他们的原本选择和翻译结果。而他们的翻译结果又往往是另一类研究者们的基础,并且直接影响到与中国本土文学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第一代的法国文学译者,包括最早将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的研究者中,大部分人并不直接精通法语,他们的翻译主要是依靠合译和转译的模式来实现。而与此同时,我们正处在上文所谓的外国文学在本土的第一个“移植”阶段。因此,这个阶段我们所能够观察到的法国文学研究的特点十分清楚:一是在法国翻译文学的原本选择上,视野十分混杂,并且通常取决于法国文学在其他国家译介的状况;二是作为译介的研究,成果产出的数量之大、速度之快,甚至要超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三是在20世纪末那个思想碰撞的时期,法国文学研究者的立场十分多样化,具体体现在这个时期法国文学研究的成果中,即研究方法和评论表现形式十分多样。文学研究立场的问题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甚至转化为激烈的争论和冲突,并且直接影响到了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接受环境。
但是,法国文学译者和研究者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批懂法语的学者从法国留学归国,无论他们在法国留学的专业是什么,他们的翻译与研究立场较之前人的确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并且在翻译和研究的对象问题上有了自己的选择。事实上,我们也的确发现,这个时期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对象和策略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呈现出某种承继的关系,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呈现出更大的“专业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法国文学研究无论是在视野、方法上,还是对象上,都具有同质的倾向。这种同质的倾向有其社会环境的原因,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十多年之后,又因社会环境的原因,这种同质的文学研究也荡然无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间,法国文学研究的主体仍然是兼有译者和研究者的身份,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不仅留学于法国,而且出身于法国文学研究领域。在这个时期,对法国文学的研究,其他领域的学者很少介入,除了少数其他外国文学领域的专家。
同质化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八九十年代,法国文学研究的视域骤然打开,从单一的法国视域走向了比较以及整个外国文学研究的视域。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过了十年的停滞之后,使得法国文学能够迅速摆脱当时单一意识形态桎梏的,仍然首先是法国文学的研究者,例如柳鸣九。不能否认的是,大量的法国文学专家在这个时期也如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家一样,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贡献于翻译,而经历过近30年的曲折道路后,他们从事文学翻译的态度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比,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法国文学研究立场的变化正是从80年代的直译态度开始的,这也为后来与比较文学视野的相逢提供了基础。
而在新世纪的前后,法国文学研究的方法也进一步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这其中既有法国文学研究本身的贡献,也有时代的因素。我们知道,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对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就十分关注。与中国对本土文学的评论不同的是,在短短的20年间,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从外部环境到文本再回归外部环境的一个来回,而这个来回完全取决于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而不是法国文学研究本身。虽然在法国滋生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颠覆了外部环境决定论的文学理论,但法国的结构主义却需要绕道美国才能抵达中国。或许是距离太近的缘故,新世纪法国文学研究方法之分散、对象之琐碎,以至于虽然已经过去十几年的时间,竟然都没有形成一致的趋势和倾向。这与八九十年代,法国文学研究之于外国文学研究的贡献是不同的。
二、法国文学之于外国文学
解释完作为翻译文学的法国文学和作为外国文学的法国文学之后,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说明法国文学与整体的外国文学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别的文学都是与一定的文学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也都会贡献于某一个既定的文学形象的形成。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国文学在众多的外国文学中,一定有其辨识度很高的“身份认证”,而这个身份与各个阶段研究者的选择以及基于选择之上所形成的结果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法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是18世纪的启蒙时代文学和19世纪进入“现代”之后的文学——不仅传统的文学样式戏剧和诗歌受到各国文学的追捧,以夏多布里昂、雨果等人为首的浪漫主义和以巴尔扎克等人为首的现实主义更是将当时还是非主流文学样式的小说带向高潮。而20世纪,法国的小说家们在诗歌与小说的领域也都进行了令人瞩目的叙事和语言的探索。
这在某种程度上铸就了法国文学在中国的形象。与其他国别的文学例如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或是苏俄文学等相比,法国文学在中国无疑有其特别的道路。同时,纵观这100多年来法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其特点也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我们发现,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法国文学从启蒙时代的文学开始与“思潮”这个词就脱不了干系。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家们尤其青睐法国的启蒙作家,20年代就有了卢梭《忏悔录》的翻译,翻译家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中国“性学”专家张竞生。而伏尔泰、狄德罗等更是在第一时间来到了中国。启蒙时代的作家们往往也兼有百科全书派的身份,因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代表的是平等、自由、民主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可以说,法国文学给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知识的“光明”,而这也正是启蒙的真谛。
20世纪的法国文学更是与“思潮”两个字密不可分。早在40年代就传入中国,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存在主义文学,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遭逢冷遇,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迅速掀起一股“存在热”。法国文学翻译界和研究界迅速加入了这股“存在热”,并成为80年代存在主义文学、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主力军。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的思潮。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有不解之缘的后现代思潮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在80年代也迅速得到了传播。在结构与解构框架下得到介绍的罗兰·巴特、德里达、福柯等人,直至今天继续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德勒兹、巴迪欧、朗西埃等人,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兼有哲学家与文论家的身份。因此,如果说从中国的“启蒙”时代开始,法国文学就为中国带来了文学中的新思想,那么一个世纪之后,中国的“新启蒙”时代同样也离不开法国文学和法国文艺理论。
其次,我们能够看到,在法国文学的研究中,诗歌、戏剧固然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在20世纪初期及末期的两次翻译高潮中,诗歌、戏剧的翻译都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因素,但是在法国文学整体形象的塑造中,小说家显然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与法国语言文学乃至文化开始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期有关。18世纪和19世纪显然是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世纪,如果说前者是启蒙时代的世纪,后者则可以被我们定义为叙事的世纪。正是因为19世纪的法国小说家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努力,小说渐渐成为主流的叙事方式,同时,由诗歌、戏剧占据文学主流形式的局面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在这样一种历史的遭遇中,我们发现,中国的读者在一个世纪之后,与法国文学之间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关系:一方面,虽然不是从原文翻译,法国19世纪小说第一时间绕道英国、美国或日本,进入了中国,这就使得中国的读者对法国文学在第一时间就消除了陌生的感觉;另一方面,19世纪的法国是大革命才将结束,资本主义正处于迅速上升的时期,阶级矛盾特别突出,而当时的现实主义小说作为与现实世界两相映照的一种叙事形式,以不同的手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这种社会状况正好与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状况不谋而合,从而很容易被中国的作家拿来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去。中国左翼文学对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和自然主义作家的偏爱,包括左翼文学家们对法国小说的偏爱、翻译、介绍和研究,与此不无关系。所以,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中国的读者们对法国小说作品不能说是没有偏好的。同样,在20世纪的上半叶,小说也作为一种主流的文学形式渐渐在中国得以确立。这种变化使得文学的叙事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非常凑巧的是,进入20世纪之后的法国文学同样也在小说叙事上——与此相对应的还有关于小说的叙事理论——作出了进一步的探索。因此,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学以一种同样亲近的方式接纳了法国在小说叙事上的探索,并且,这也对中国80年代以降的新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最后,同样值得指出的一点是,法国也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选择的目的国之一。因而,自从中国文学翻译初期转译与合译的翻译模式不再流行之后,中国很快就有了第一代通晓法语、有着专业法国文学研究背景的法语译者,李青崖、毕修勺、李健吾、傅雷、穆木天、焦菊隐等人都属于这个行列。前一代译者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新中国成立之后,稍后于他们登上法国文学舞台的新一代译者也与他们一起成为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重要力量,例如赵少侯、沈宝基、罗大冈、吴达元、罗玉君、陈占元、郑永慧等人。和前一代法国文学翻译家、研究者不同的是,新一代的译者往往具有专业的背景,倘若他们涉入研究,其研究结果与前一代人相比已经有了差别。虽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的产出很少,研究方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应该说,他们的成果是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而在80年代,也是法国文学的翻译家率先回归到文学自身的轨道上。事实上,也正是这些早期的翻译家和研究者塑造了法国文学在中国的形象。这个形象既有别于整体的外国文学,也有别于由法国文学史家们塑造出来的法国文学的形象。在这个基础上,勾勒在中国的法国文学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就尤其必要,也尤其重要。
三、法国文学与研究语境的变化
我们说,文学从来不是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的,文学研究也是如此,翻译文学的研究同样如此。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文学所应承担的使命、对文学性会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对文学创作就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文学也总是个体的产物,因而社会环境与文学之间不是绝对的规定与被规定的关系。
具体到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来说,社会环境的决定性影响会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对原本的选择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我们会选择不同的外国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其二,不同的社会环境也会对文学翻译的立场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从而对外国文学的形象塑造产生影响。前面两点都决定了外国文学在中国研究的宽度与基础。其三,不同的社会环境更是会决定对外国文学的关注程度、关注角度,甚至会影响到外国文学的研究方法、批评风格等,从而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其四,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同的社会环境会造成对外国文学的不同需求,从而赋予外国文学以不同的“使命”,而在达成了对外国文学所应承担的“使命”的理解之后,外国文学研究者们对作品的评价与判断所依据的原则自然是不同的。后面的这两点往往决定了外国文学研究的质量与深度。
而法国文学在中国不同的时代所得到的理解与研究充分印证了我们上述的观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文学甫进中国,中国正处在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动荡不仅是政治的,也是思想的、文化的、文学的、语言的。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在这个时期的传播速度、译介方式,当然,更决定了文本的选择。我们看到,最先进入中国的法国小说,包括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惨世界》、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等,既具有读者亲近的导向,也反映出了社会对科学、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可以说,那时的法国小说并没有构成属于自己的完整形象,也并不是依循自身的规律有秩序、有计划地得到译介,它更多是与其他外国文学混杂在一起,当代的与古典的混杂在一起,各种文学的形式混杂在一起,以最快的速度达成当时中国在文字、文学、思想上的变革需求。
当然,文学必然呈现出自身的规律,法国文学更是如此。从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开始,法国文学的译者与研究者就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并且是文学的目的——地完成法国文学在中国的整体形象构建。除了译介与传播的需要之外,法国文学史本身的构成也成了这些译者、研究者的重要依据。这时候的译者与研究者往往都有自己特定的翻译对象与研究对象,研究与翻译并举的现象也很普遍。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有了一定的基础:法国作家、流派、思潮包括法国文学史的发展轨迹,在中国都得到了初步的介绍。
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环境无疑是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包括中国社会之间特殊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虽然法国文学在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得到继承,但是从1949年到1978年,日渐单一的意识形态破坏了本应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文学研究工作,使得法国文学研究在研究的对象、选取的作品、批评的方式、批评的话语、研究的方法上都趋于统一。而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法国文学的研究也和其他外国文学一样,更是渐趋沉默,除了极少数供批判使用的“内部资料”有所翻译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成果可言,即便有与法国文学相关的论文、讨论,也几乎完全是非文学的。
这种状况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得到改变。从改革开放到80年代末期,中国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法国文学的渴求状态。这依然是一个经过长时期封闭之后,对一切新思想、新方法的渴求。而20世纪的法国文学以及法国文学理论恰恰又以提供新思想和新方法而闻名。虽然此时的中国已经拥有较多的法语人才,但是在80年代,中国仍然从英文转译了一些法国文学作品,尤其是法国文学理论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新思想、新方法迫不及待的心情,另一方面也昭示着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或者说正在准备进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具体说来,对法国文学研究的直接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最直接表现是研究队伍的变化。不仅仅是法语语言文学的学者在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其他语言文学领域——尤其是美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文艺理论领域——以及文、史、哲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法国文学、文化、思想的研究者,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补充了由法国文学专家重新兴起的法国文学研究,并且在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
在90年代,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组织。这个事件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翻译、研究外国文学的形势。90年代到新世纪到来的这十年间,法国19世纪的作家、作品在中国的复兴与此可能不无相关。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显现的时刻,中国的法国文学翻译与研究从对象上来说也基本上能够保持与本土的法国文学同步。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的形态虽然与法国自身的文学研究形态仍然千差万别,但是研究对象的同步性带来了新的视野,而新方法也为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成果。
现在,新的世纪也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在新世纪里,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甚至到了令人忧虑的地步。作为对全球化语境的反思,文学研究与权力问题直接挂钩,世界的文学研究语境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20世纪中叶一度兴起的文本中心,从对形式的迷恋又转向了文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研究,转向了内容,或者说,转向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研究。但是,新世纪的变化提给中国文学研究——包括法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十分尖锐:如果说我们还身处21世纪之中,还没有足够的时间距离让我们来看清新世纪的法国文学,如果说这个问题对法国文学的翻译并不直接构成影响,那么在全球化与反殖民语境下,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在何等程度上依然不失其意义?并且在这个怀疑的时代,面对无法再“通过一系列大主题、大问题、大赌注,遵循着我们对一定时期的文学进行研究时一贯采用的、文化的、社会的或是人类学视角”[2]来组织的新世纪法国文学史,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可以并且应该迎来什么样的新视野?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或者中国文学理论之间,可以并且应该构成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在此不下定论,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在我们思考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时必须有所考虑的问题。文学所呈现的关系之所以复杂,之所以值得我们从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和角度来审视它,是因为它不仅是文本的、形式的,是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更是与这个世界文化系统的其他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世界;而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研究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跨越了两个语言的系统、两个文化的系统,是另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构成。它生成在目的语的语言文化中,而对象却有着出发语语言文化的“前世”。然而,唯其复杂,才是与“人”相关的,也才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
注释
[1]或许我们可以想到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这在众多欧洲国家的文学史上也是空前仅有的案例。毫无疑问,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德国文学甚至是文化思想的构成,但是,就语言的构成而言,却不是依靠这次的文学翻译高潮推动的。德语语言的激进变革时期也与翻译相关,即路德的《圣经》翻译。
[2]M. Delon,F. Mélonio,B.Marchal et J. Noiray,A. Compagnon,La Littérature fran?aise: dynami-aque&histoireⅡ,sous la direction de J.-Y.Tadié,Paris: Gallimard.2007,p.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