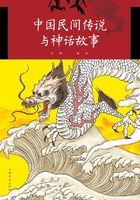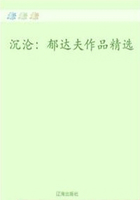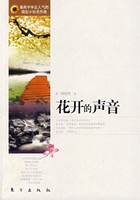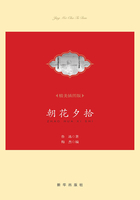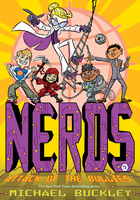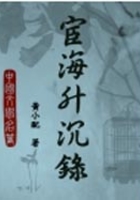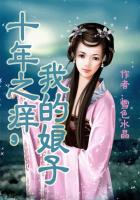我于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我的处女作发表十二年之后,开始接受关于文学的采访,至今已经有将近十六年“被采”的经历。
我的大部分访谈都是根据文化记者提供的采访提纲“写”成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书面文字。为了文本的连贯、清晰和全面,我还经常会需要增减采访提纲的内容,调整采访提纲的结构,甚至润色采访提纲的语言,以增加问题与回答之间的张力。因此,我一直将这一部分访谈视为是自己的“作品”。它们的完成过程与我其他作品的创作过程有不少的相似之处。
这些“作品”中有不少的名篇,如《面对卑微的生命》、《“写作是最艰难的人生冒险”》、《“文学永远都只有一个方向”》等。就像我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些“作品”不仅是我个人文学道路上的坐标,也为一代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追求提供了见证。
收集在这里的访谈作品大都是我的“原作”,与媒体上经过删节和编辑之后发表的版本有程度不一的出入。而为了这一次结集出版,我一如既往,又对每一篇“原作”进行了重新的梳理。
我将近三十年独立于主流和正统的文学道路是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路。我总是说,文学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我的宿命。但是,在整理这些访谈作品的过程中,我还是忍不住会不断责问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孤独?为什么要如此抗争?为什么要如此殚精竭虑?为什么要如此含辛茹苦?……从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歌中借用的这篇短序的题目就是我对所有这些责问的回答。
如果我能够选择,我肯定,我还是会选择悲天悯人的文学。
薛忆沩
2015年1月8日于蒙特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