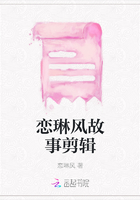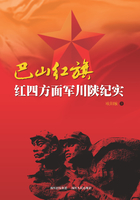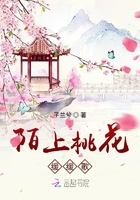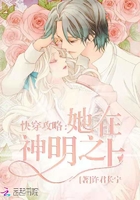牛津,在我的心目中,是何其“牛”的两个字。二〇一〇年,香港作家周蜜蜜女士嘱我为她“牛津版”的长篇小说《文曲谱:香港的离散与追忆》写一篇序言,我有一种仿佛中了双色球彩票大奖般的窃喜。当典雅的牛津版《文曲谱》寄来的时候,有好些日子,我都把它摆在办公桌上最显眼的位置,就像《围城》里的陆子潇,桌子上总是摆着那个印有“外交部欧美司”的大信封一样,恨不得每一位来办公室的同事都能翻阅一下。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跟OXFORD沾上边,真是“与有荣焉”。因为长期以来,我以为只有像董桥、林行止、刘绍铭、李欧梵、金耀基、小思这样的文人,才配得上做牛津版的作者。当然,还有更年轻一辈的毛尖和马家辉们。
算起来,做毛尖的粉丝已经有十来年了,书柜里大致收集齐了毛尖所有的书。当然,毛尖出版的书不能算多,也比较容易收集齐全。我的周围也颇有几位铁杆的“毛尖迷”,分布在电视界、文学界和高校校园里,有的还是直接受到我的“影响”而迅速迷上毛尖的,因为他们最初阅读的毛尖的书,都是从我这里借去的。就在几天前,还有一位热衷上“我们约会吧”和“一站到底”之类的电视节目,经常给一些“欠扁型”的嚣张男“灭灯”的八〇后妹妹,不知哪根筋被绊动了,突然想读点书了,而且还想读点“有个性的”,这当然是好事,读书使人灵秀嘛,我赶紧送了两本毛尖的书给她:“好好读,这里面的爽快和重口味都适合你,大女孩需要大钻石。”两本书,一本是新版《当世界向右的时候》,一本是毛尖的影评新集《例外》。
本来,还有一本毛尖的书,是更适合推荐给她看的,但我担心明珠投暗、有去无回,没舍得给她。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极为珍贵,因为这是册“伟大的牛津版”,书装富丽典雅且不说,重要的是,这是毛尖的亲笔题签本。书名有点匪夷所思,叫《有一只老虎在浴室》,董桥先生作序,收录了毛尖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和《苹果日报》副刊“苹果树下”的专栏文字六十篇。
记得《诗经·召南》里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的句子,各家注解都不一样,而我一直愿意从字面上去理解它。毛尖这本书里的文字,正是嬉笑怒骂、汪洋恣肆、“舒而脱脱”,既站在“阿拉普罗大众”的伦理立场上,又充满最专业的批判精神和娱乐精神;有充分的道义感和侠骨豪气,路见不平,敢于拔刀相助,匡扶正义,心地坦荡而爽快,宁要大钻石,也不要所谓小清新。
虽然也是一些影评和时评,却是从犄犄角角的细节入手,利剑快刀,旁逸斜出,直捣这个畸形社会和那些假模假式、总想凌驾于普罗大众之上的既得利益者的死穴,若庖丁解牛,砉然响然,莫不中音,读来使人禁不住要大呼过瘾。例如,本来是在谈银幕巨星伊丽莎白·泰勒的,却忍不住要荡出一笔:“几天前,北京民政局局长刚刚发布消息:针对老年人的医疗补助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九十五周岁以上老人将可以同一百岁老人一样,享受百分百的医疗报销待遇。据说这个消息搞得网民很兴奋,因为九十五岁才叫老人,那么二三十岁还让父母喂养着就正常,四五十岁犯点错就是青少年犯罪。至于七十九岁的玉婆还思量恋爱订婚结婚,也就两个字:应该。”读来使我如获阅读《围城》时的那种辛辣和幽默的快感。谈谢霆锋,谈得何其公允和独到:“江湖儿女江湖长,这是香港电影的不二法门。香港电影,从绯闻中学习恣肆,从色情中发展想象,从血腥中提取幽默,总之,那些可能败坏电影的东西,在香港电影江湖里,奇怪地有了可能性,如同谢霆锋一路走来,黑黑白白的那些事,顶包案也好,艳照门也好,却向他馈赠了最好的礼物。十年前,我会说,谢霆锋这种长相的孩子,我班上也有好几个,但现在,没有了。”
擅长幽默和机智的作家,大都不屑于玩弄小清新,而是更喜欢像毛尖在书中写到的那样,只需略施一点点“咸湿”,就立刻“毁掉了小清新”。钱锺书、林语堂、甚至鲁迅,以及黄瞮、黄永玉、李敖等等,都深谙此道。毛尖的文字似乎也不屑于小清新,而且也常见引人入胜的咸湿之句。这也正是毛尖的书比一般女性文字更富有人道情怀、更显得“舒而脱脱”的地方。有时她写得也真够坦荡和爽快,例如她说,老百姓喜看黄片,可不“就为了那点黄喽”;3D版《肉蒲团》好看,不就因为“3D效果呈现的肉新鲜”!她说有一些人的心又硬又冷,摸上去“就像假胸一样”。
董桥先生在序言里推崇毛尖的文章“灵清”、“开朗”、“有品有格”,坦承自己读毛尖文章“于是惊叹,于是拍案,于是折服”。我觉得,这些评价毛尖是当之无愧的。
据说,迄今为止,影响过人类命运和历史的,有三只伟大的苹果:一是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偷吃的那一只,一是砸在牛顿头顶上的那一只,还有就是被乔布斯咬了一小口的那一只。循此思路追想一下,迄今为止,在我个人的记忆里也有三只意义非凡的苹果,不,是三棵苹果树。一棵生长在我初中时一位女同学的外婆家的院子里,那时候我常常和她一起坐在晚霞映照的苹果树下写作业,有时还一边吃着她外婆给的苹果,一边津津有味地读着只有她家才有的厚厚的小说。正是在那棵苹果树下,我第一次读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也是她家的那些小说,在我少年的心灵里最早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使我在日后悄悄走上了文学的小路。另一棵生长在德国慕尼黑的那个名叫布鲁顿的小小古堡的院子里,那里是伟大的杰拉·莱普曼夫人亲手创办的一座国际青少年图书馆,我曾有幸去那里访问过。小城堡的院子里长满低矮的苹果树,通红的苹果落满了草地,站在苹果树下,我呼吸到了来自全世界的芬芳馥郁的书香。这个长满苹果树的小庭院,多少年来一直让我心驰神往。还有一棵,就是毛尖女士的苹果树了。这些写在“苹果树下”的文字,这些牛津版的苹果,在涂着蜡光般的树叶间窸窸作响,香气四溢,它们用一种独特的气息熏染着我、魅惑着我,甚至在改变着我已有的那些文字感觉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