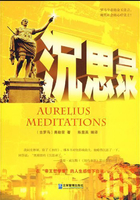“我娘死了不久,我便溺水了,您还记得吗?”
安丰年僵硬地点了点头。
安歌顿了顿,平复下激动的情绪,再开口时,语气明显要低缓很多:“我是被安诗诗推进河里的。”
“如果不是我命大,一次又一次从鬼门关里逃出来,爹,你以为你现在还能看到我好端端地站在你面前吗?”
“我装鬼吓唬大伯不假,但有人把诅咒用的纸人藏进我房间里,借机来陷害我,置我于死地也不假,是谁处心积虑要置我于死地,爹,您还用再问吗?”
“可是、可是.......”安丰年踉跄后退一步,“诗诗她、她为何要害你呢?你是她的亲堂妹,从小又忍让她,她没理由、没理由啊......”
“那大伯又为什么要奸辱娘,逼死我娘呢?”
一声问,把安丰年问住。一时间,安歌这些话在安丰年的脑子里炸开,炸得安丰年头疼欲裂,他抓着自己的头发,跌坐在藤椅上,感觉到了窒息。
他一直以为他妻子的死是因为自己,是因为自己混账没用,是因为那天自己抢了她最后的私房钱去赌博,她才绝望而终,却不成想......
一个是他的妻子,一个是他的大哥;一个是他的女儿,一个是他的侄女......
安丰年抓着脑袋,他想不通,想不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您把他们当成是一家人,可是他们真的把咱们当成了一家人吗?”安歌又一声质问,安丰年艰难地闭上眼。
他的眼一闭,死去的妻子的样貌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紧接着是安歌被人从外面带回来,落水后奄奄一息的模样,他们坚持要把安歌送上火架的样子......
这一瞬间,安丰禄一家三口一直以来,对待他们的残忍行径一幕幕地在安丰年脑子里过了一遍,最后画面定格在胖夫人强行在他怀里抱走安博书的时候。
“啊——!”
安丰年长啸一声,这一声啸里,夹在了许多说不尽的情绪。
安歌静静地等着,等到安丰年终于安静下来,她抓住安丰年的手,低声问:“爹,难道您真的能就这样看着娘这样死去吗?”
“您手上有大伯的把柄,大伯暂时或许不敢对您下手,但是您想过没有,他是个冷血的人,我和娘他都能狠下心去,对您难道就真的狠不下心了吗?”
“你想怎么做?”安丰年终于妥协。
“爹,把您知道的,关于大伯的事情都告诉我。”
两人双目对视,安丰年的意志本就不强,又被安歌方才的一番话把意志全部击垮,加上迷魂术的左右,安丰年果然一五一十地将他知道的和盘托出。
安丰年的语速很慢,他知道安丰禄的许多事不假,但安丰年很少当着他的面谈起政务,故而他知道的东西很零碎。
有些是很久之前就知道的,还有些是安丰年无意之间偷听到的。
安丰年的记忆很零碎,他的语言也就很零碎,他絮絮不止地说了小半个时辰,这小半个时辰里,他说累了,便停下来喝一口水,然后继续说。
从安丰禄踏入仕途起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年里,安丰禄做过许多亏心事。
他年轻时买官行贿,后来娶了胖夫人,得到胖夫人娘家的帮衬,一路直升、平步青云。搜刮民脂民膏的事情,安丰禄干过;徇私舞弊的事情,安丰禄也干过。
太陈旧的事情,证据便已经不好找了,再加上安丰禄这人做人做事都小心得很,轻易不会给人留把柄。
近十年安丰禄做的事,便很少让安丰年参与其中了安丰年只晓得他依旧在参与买官、卖官的勾当,几年前安丰年曾在书房里见过一本花名册,花名册上记录着他买卖过的职位以及卖方、买方和涉案官员等。
至于现在这本花名册在什么地方,安丰年便不晓得了。
安丰年列出的这些罪状上,且把搜刮民脂民膏、贪污受贿和中饱私囊撇去,只说买官卖官这一条,安丰禄纵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安歌心里暗自掂量计较着,很快有了数:“咱们只要想办法找到那本花名册,或者是他贪污受贿的证据,自然可以绊倒大伯了。”
安丰年叹口气,“闺女你说着容易,但证据哪有那么容易找的,再者,现在大哥跟孙将军结为了亲家,我虽然不在朝野,却也知道朝野上一大半都是孙将军的人,如此形势,想要扳倒大哥,难如登天啊!”
想到孙友志,安丰年心里又打起了退堂鼓,拉着安歌的胳膊劝道:“咱们势单力薄,你娘死不能复生,我刚刚又想了想,为了她搭上咱们的命不值当,何况、何况......”
安丰年一阵犹豫,“何况孙将军在朝中一手遮天,我之前甚至无意之间听到他和大哥密谋要将皇帝逼下皇位,换成孙显荣坐江山。现在孙将军已经离开京都回北疆去了,他回了北疆,随时可以率领北疆大军压境,到时候这天下姓什么还说不准,闺女,你就不要冲动了,好吗?”
安丰禄和孙友志要造反!?
安歌顿时一惊,急忙追问:“这个消息都有谁知道?陛下他知道吗?”
“我是无意间在书房外偷听到大哥和孙将军的对话的,如此大事,谁敢妄语?再说,就算是皇帝知道又有什么办法,咱们大齐一大半的兵权都握在孙将军手里,只要孙将军不明目张胆地造反,皇帝不还是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个皇帝还真是个蠢货!”安歌心里骂一句,开始不安起来。
安丰年还在劝她,劝她不要轻举妄动,安歌没有去骂安丰年孬种,因为安丰年确实是个孬种。
自己妻子的真正死因以及安诗诗残害安歌的事情,让安丰年热血冲动了片刻,片刻的热血过后,安丰年开始想的,便是自己的命了。
他在想自己的命,安歌则是在担心程舒志。
她晓得孙友志和程舒志之间有仇,晓得孙友志权势大,却不晓得,孙友志在朝野中竟然是只手遮天的人物。
程舒志要对付这样的人物,谈何容易?更何况现在孙友志已经想着造反了,倘若他真的反了,率领铁骑压境,到时程舒志又该如何?
眼见着程舒志刚刚考中状元,前途刚要开始光明,黑暗马上就又要袭来了,安歌开始不安,开始为程舒志担忧。
“不行,我一定得把他们要谋反的消息告诉程舒志!”
刚生出现在就去状元府里面见程舒志的念头,安歌突然又想到昨天眼见的一幕,怒气又窜上来,心里一阵狠劲儿,索性对程舒志不管不顾,扭头又生出新的念头把这股狠劲儿给压下去了。
“我告诉他这个消息,才不是因为我担心他,而是因为他来来回回救了我这么多次,我不能做没良心的人,我这是为了偿还他的救命之恩。”
这个理由很好地说服了安歌,但她暂时又不愿意见到程舒志。
她心里还是有气的,她不想见到程舒志和李秀云亲亲热热地在一起,给自己添堵,可消息又不能不送。
安歌想了又想,终于想出来一个折中的法子。
“爹,有纸笔吗?”
“你要做什么?”安丰年警惕地问。
“你甭管我要做什么,有的话你给我拿来,没有的话你给我买来,我有大用。记得,还要个信封。”
安丰年心里起着嘀咕,现在却不是很敢违背安歌的意思,乖乖地出去买纸笔了。
附近读书人少,卖纸笔的人也就少,安丰年出去了有一会儿,才把笔墨纸砚买齐一套回来。
安歌磨了墨,在信上写道:“孙友志与安丰禄欲反”,只九个大字,她便收了笔,把墨迹吹干,纸塞进信封里,信封用滴蜡封住,封面上写“程舒志亲启”。
她把信纸塞进怀里,拿起帷帽戴到头上,丢下一句:“我出去一趟。”还没等安丰年问她去哪儿,她便一股烟似的,打开门溜远了。
安丰年现住的这个地方,周围虽多是穷人,但是距离京都的繁华不算远,距离状元府也不算远。
她怀里揣着信,一路走得飞快,直走到状元府外。
状元府的大门紧闭,她没有敲门,而是选择从旁边的一棵矮桃树上翻上屋檐,踩着檐瓦朝里走。
安歌不晓得哪里是书房,程舒志现在又在何处,她小心走到前厅顶上,趴在房顶,仔细留意院子里的人。
状元府的屋檐高得很,下人们都低着头,谁也不往高处看,来来回回走了几个人,都不曾发现安歌。
安歌留心瞧着,直到李秀云端着一碗羹汤从圆拱门里走出来,看见她,安歌心里窜出火来,低声骂一句“奸夫**!”然后从怀里掏出信。
她把信用绳子随便绑了两下,绑到一根木棍上,木棍狠狠一丢,正砸中李秀云的脑袋。
“谁啊!”李秀云吃痛,不由骂一句,听见骂,大壮从书房里探出头来,便瞧见了落在李秀云脚边的信。
他走出来拾起信,抬头朝信来的方向看,不知是自己眼花还是如何,他觉得自己仿佛看到了一抹一闪而过的白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