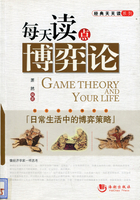众所周知,我是一位作家。作家靠写作为生。我做过各种活,车间搬运工、邮递员、公司小职员,后来我就把工作辞了,一心坐在家里当起了作家。要当一名作家并不困难,困难是当了作家以后才真正有的。首先便是生活困难,我写各种各样的作品,但仍然填不饱肚子。
肚子是个坏东西,它逼我为了满足它而拼命工作,然而尽管我工作很勤奋,但并不代表我就可以有很好的收入。我写的一些东西很难发表,可这并不怪我。编辑和读者要我讲故事,但我根本就不会讲故事。一味地讲故事在我看来是很愚蠢的。为了寻找到故事,我不得不经常向我的一些朋友要故事,让他们给我讲,讲他们自己一些亲身经历过的,或者是听来的。应该说他们的故事讲得真不错,有时根本不用进行多余的加工,就是一篇“好小说”。幸好他们没有决定当作家,如果他们也干这一行,那么我想作家这一行里肯定要饿死不少人。最近我碰到我好多年前熟悉的一个朋友,因为一种你能理解的原因,我在这篇文章里叫他“K”。我是在我们这个城市西郊的一个小饭店里无意中碰见他的,他正在喝酒,已经有点醉了。见面了无疑很高兴,他非要到我的宿舍里再聊聊,他说的再聊聊其实就是到我宿舍里再喝酒。我宿舍里有酒,我在生活里也同样离不开酒。我们俩就痛快地喝开了。他一边喝就一边对我说了他最近回乡下的故事——
火车一过江,K的心情就迥异起来,城市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锁在沉重的灰黑色的雾霭里。当火车开上大桥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同时轰鸣声让他耳朵感受到紧张的气压。过了大桥就到了江北地面上了,他看见了乡村,皑皑的白雪覆盖在广阔的平原上。“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一片莹白。”K想起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里开头的句子。几乎非常吻合的情景啊。这是一列简陋的小火车,里面挤满了各色各样的人,同时散发着一种好像是胶鞋里的气味。K回去奔丧,他接到了老家发来的电报,说他父亲快要死了。电报上写的是“病危”,但他相信父亲是死了。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老家了。奔丧使他决定回去。大片白色的雪光从窗前掠过。时间在火车的快速奔跑里有点吃力地把暮色慢慢地一点一点往黑暗里拖,就像一只蚂蚁在搬运一只螳螂的庞大尸体。K的心情在他目光注视着的平坦的田野里像烟一样轻散开来,甚至慢慢有点飘扬。父亲的死让他终于有理由回乡下去,他已经远离了那个陌生而偏僻的地方。车厢内的灯光黄黄地漾开来,洒在每一个旅客的身上,他们的面目都有点恍惚。与K同坐的是那些面目模糊的男女,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坐在这一起,他和他们完全不相干,但现在却不得不彼此忍受心里的憎恶和厌烦。他看到他们中间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嘴唇鲜红。车厢里一片嘈杂声。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嘈杂里。他们毫无意义地讲着无数的废话,而他们自己以为是有意义的,他们生活的意义之一就是讲废话。那些废话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呢?K抽起烟来,他想以抽烟的姿态保持自己的独立,但他很快发现有更多的男人也抽起烟来。他们烟抽得比他更猛更呛,他们和他是一样的人。他们不想让他孤单和特殊,显示出任何不同。他在那一刻感到一些无奈,那个年轻女人边上的几个男人都在讨她的好,向她说话。他听不清他们在讲一些什么,K不想听,他看见那个女人的红唇在笑。年轻女人和那几个男人的关系非常暧昧。他们都是暧昧的。K想,我在这趟车里也成为暧昧戏剧里的一个角色。茶水泼散了音乐变成噪音或者说噪音汇成了音乐,浓得呛人的烟雾中打嗝与小孩子的哭声、臭臭的带鱼味、骂人与大笑……混乱而黯伤有点末世景象。逃亡与奔丧有着相同的主题。K把这些人都视作逃亡的人。我们为生活而忙碌以为死亡离我们很远,只有死亡从容不迫地在生命中的某个地方静待着。K想到父亲死是一定的,可是他死了也不饶他,要让他去看看那张由于死亡而一点不生动的脸。死是可耻的然而又是必然的,看来我们每个人都逃不开可耻。人是什么?人是死亡。死亡才是我们的本质。K看到他眼里的那些旅客,知道他们离死亡都很近。他们在轰鸣声里酣然入睡,夜色已经完全控制了外面的世界。我们在夜色里穿行。他看到有人大张着嘴发出拉风箱一样重重的鼾声,口水挂得很长。这其实是一副垂死的样子。他看到了他们白森森的骨架。他们没有什么,灵魂已经飞了,肉体是什么?它会烂掉,剩下的只有骨架。一颗滴着血的心脏在骨架里有规律地跳动着。红唇女子身边的那些人终于倦了,只剩她一个人在生动。他闻到了她身上肉欲的香味。她的眼睛在看着他。你干什么去?回家。这些是你的同伙吗?不,我可不认识他们。你是个有趣的人,你看起来很严肃。啊,我只是长得就这样。他们开始攀谈。他们在交谈里熟悉起来,彼此都知道自己是多么地需要一个对方,我们需要对方来证明自己的欲望正常和生理健康。K看见了她的胖乎乎的圆脸很白,有一种妖气。在这样的旅程里,应该有点实质性的东西。K想我可以干她,而她也是需要的。时间和空间给他们提供了舞台与机会,他们只是两个角色做无法拒绝的事。他们在捏手与眼色以及身体扭动的各种暗示里无法得到根本释放,他们的腿交织在一起像蛇一样,激情让他们都变得凶狠起来。K听到自己的呼喊声,整个车厢成了他的胸腔,呼哧呼哧就像一头大象发出的嗥叫。他看到她眼里放出光来,照亮了他的心脏。他们没有再犹豫,终于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奔向厕所。他们穿过长长的过道与那些昏睡着的人,在巨大的轰响声里,他们觉得整个车厢里都安静极了,一个列车服务员也看不到,这个车厢里只有他们这两个充满欲望的男女。他们挤进一个厕所后赶紧把插销别上,一下就变成完全的两人世界。他们确信没有人发现他们,铁轨在他们的脚下飞驰,他要动作,但她却拦住了他。他怔了一下才知道她要什么,觉得她真是一点人情也不讲。他从钱包里掏出两张纸币,她看了一下,才默许了他的动作。情绪上来了。金钱是最好的春药,K想,她在催他。特殊的环境给他们性交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红唇女子没有一点怨言,她默默地接受他的进攻。K一件件地把她的衣服往下脱,怎么也没有明白她到底穿了有多少条衬裤,好不容易让她下身赤裸了。他看到了她的两条光腿,看到了她夸张的毛发,它们像受到静电吸引一样,四处绽开,旺盛蓬勃。很多树木从窗外一闪而过,K还看见了月亮,半圆形,白里发灰,它飞快地把那些树木拦头斩断。冷风从脚下往上泛,他们靠在洗手池边做,很困难,却很努力。K一边做一边惊讶于自己的勇敢,这是他过去从来也没有经历过的。这归结于一种意外,他想,他没有想过会遇上红嘴唇女子。他们很快就做完了,年轻女子一言不发很快地穿裤子。K听到的只有车轮在经过铁轨接头时发出的哐当哐当的声音。他拉开门,让她先出去,然后他自己一人在里面点上了一支烟,洗了手才回到座位上。他看到她穿戴整齐地端坐在那里,他冲她笑了一下,但她却没有笑。
“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它太简单了,简单到让我感到意外。开始我完全不能肯定她是什么样的人,后来我知道了。我理解了。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像她那样的人有成千上百,她们分布在各个角落。她们都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在这个城市里打工,挣一口饭吃,环境改变她们。如果我是那样出身的女子,我也容易这样做。世界上最可耻的是不能生存,而不是别的什么。她说她是在一家小饭店里当女招待,不过我估计她也做些别的什么工作。”K对我说。
K把她带回了乡下,族人和村邻都来看望。他已经很有些年头没有回来了,于是他们对K就亲热得不得了。小村子被大雪覆盖着,雪光照映着那个女子的脸,显得很干净。K让她擦掉了那些过重的脂粉。他们有协议,她陪他回来看望他的父母二老,扮成他的媳妇,他必须付给她丰厚的报酬,就像他们在小火车上的卫生间里做的一样。K对我说:“老家人一直不知道我已经离婚了,我也从来不对他们说。在老家,离婚是可耻的。老家给我来的电报,让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去。在老家人的心目里,我是很不错的,娶了个城里女子作妻子。如果我对他们说我离婚了,那不会得来一点同情,他们会认为我完全失败了。这当然不是主要的,要紧的是我必须让父母心里有一点安慰。没有人会认出她来,我前面的那位只是在多年前结婚的时候和我回过一趟老家,数十年来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接到电报的时候我真犹豫啊,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找一个妻子回去,于是坐在火车上的时候,我就想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然而当那个年轻女子答应我装成我的妻子一起回去的时候,我心里也担心,担心她的轻浮会让乡邻们看出破绽。我们从县城转车,她开始像山鹊一样地一路上说个不停,汽车里的那些村民都用好奇的眼神打量她,她太招眼了,她要我给她买了很多零食,不时地吃,脚下落了一地的果壳。我们还气得吵起来了。车上有一个乡镇厂长一样角色的人,从她上车后,眼光一直没有从她身上挪开过。她看出来了,笑得就更开心,也更放荡。我看得出来,她开始有心撩他了,一边往我身上靠,一边拿眼睛飞那个乡镇厂长。我对她说,不要这样。她根本不在乎。那个男人后来就同别人调换了位置,坐在我们的边上,假装问我话,我没理,他就很快和她说起来。他果然就是个厂长,他掏了一张名片递给了她,她看了一眼就塞到小皮包里去了。她让他看得出来她对他很感兴趣,很快他们就开始打情骂俏起来。车上的人都用别样的眼光看着我。我脸红了。本来那个很土气的厂长还有些顾忌,他不敢太放肆,但她却一点顾忌也没有,他的胆就大起来,他们一边拉手一边窃笑,甚至耳鬓厮磨。要是我们不是在汽车里空间有限而是在前一天的火车里,他们一定也会去个什么地方。她只想卖!我对她说:‘你干什么?’她还是那样笑着,问,‘你管得着吗?’我说,‘你是跟随我的,我们说好了的。’她笑得更加开心了,这回是一边看着我,一边往那个人的怀里靠。‘婊子!地道的婊子!’我在心里骂她,同时我心里开始后悔我不该这么做,她根本不合适随我回家,她只会毁了我。但我受不了车里的那些目光。那些人无疑都在嘲笑我。谁都会认为我就是她的丈夫,而现在却扮演着一个非常不光彩的丈夫的角色。我生气地对她说,‘你注意点。’她还说,‘你管不着。’我大声说:‘你不要这么不要脸,你也许以后可以卖。’她一下子就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而愤怒地对我嚷开了,‘去你妈的!我叫你少管。你要不愿意我们现在可以就这样分手。’我说:‘他妈的,你别这样!’而那个男人在她的一番耳语后,居然对我怒目相向,而且捏起了拳头,挺起了胸膛。在最后的那一刻,我妥协了。我妥协不是因为怕她,我确实想到了要带她回去,好向老家人交待。我不想让他们看到一个‘失败’的‘我’。我想我自己没有必要这么认真,她只是她,随便别人认为她是我的什么好了,说到底她只是我的一个工具。她对我说:‘你还没有付定金钱呢。’我不吭声。她后来也冷静了下来。那个厂长还试图接近她,但她一下却冷了脸。”
“雪下得太大了。”K说,这样的大雪他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了,特别是他到了城里这么些年,很少看到大雪。他们下了车,往村里走。那个女子蛮高兴的,走在他前面一路不停地玩雪。她把自己的东西全让K背。“到时候你真让我喊你老公吗?”她问,K笑了一下,说:“老公是港台电视剧里的叫法,我们老家人才不这样叫呢,你叫我名字就行了。”她笑着说:“我喜欢叫‘老公’,特嗲。”K问:“你叫什么名字?”她问:“有关系吗?”K说:“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她对K说:“你过去的妻子叫什么?”K说:“叶菊,树叶的叶,菊花的菊。”她说:“名字不错,挺好听的,你就这样叫我好了。我是什么时候到你家去过的?”K想了一想,说:十几年了,十一年。叶菊就说:“正好啊,我就装作什么也记不得了,农村变化太大了。”K笑了一下,觉得她说话里有一种戏谑的成分。她喜欢雪,好喜欢村庄。K想:她对农村的一切熟悉极了,但她却到了城市里打工。她的家一定也很穷,所以她就被很容易地改变为一个随便的女人。她很容易地同他在那个小火车的卫生间里干,那么她也就一定可以同很多男人干。而在和他之前她已不知经历过多少了,他想。村子越来越近,看到雾霭里的炊烟,她竟可以喜欢得叫起来,像个孩子一样。
K的父亲不行了,他已经病了很久了。全家人都在等K回来。K的心情也像夜色一样沉下去。大家看着她,说叶菊跟过去有点不同,好像更年轻了(马上有人反驳说,城里人就是这样,她们越过越年轻),比过去瘦了,脸也长了,不像过去那样圆,眼睛比过去更亮。“叶菊”在他们这样的夸赞里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但她很快就恢复了镇静。她就像家里的媳妇一样,关切地询问一些情况。“我绝对没有想到她会做得这样好。”K对我说。K在心里甚至有些得意,他这回是做对了,做对了一件非常绝妙的事情。他的妈妈问她,为什么没有把孩子带回来,她支支吾吾有点回答不上来,是K解了围,说孩子要复习考学。无疑,他们的回来,成了村里的一件大事。对K老家人来说,也暂时缓解了对于病人的悲痛。
K对我说:有件事你也许想不到,她看到我父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样子,特别是最后断气的时候,她一下就失声大哭起来。K这样说的时候,我看到他脸上的感动,我甚至感觉他眼里有泪光在闪烁。他说:我当时一直想她只是工具,除了我对她有那种性要求之外,我对她并没有好感。我想她只是一个下贱的年轻女人,像她这一行里所有的女子一样。在火车上明明是我主动干了她,但我总觉得主要是由于她的勾引。我还想到她在公共汽车上对那个乡镇小厂厂长的勾引。我不认为她这样的女子会有良心或是别的什么。在我父亲病重的那些日子里,她真的就像一个贤惠媳妇一样,从家里忙到家外,但凡来我们家探望病人的人都发出赞叹,说很少看到城里媳妇能这样的。那些天里,她一改我认为的刁钻和懒惰,还有放荡和恶俗。每天天刚亮,她就起来了,和我妈妈一起到灶下烧饭,然后去喂猪,打扫院子和提水。她过去可能干过不少这样的活,所以她干得很容易。她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家里一点也不怀疑,主要是他们谁也想不到,她只是我雇来的。
“难堪的是晚上。”K说。家里人把K和她安排在一个房里,墙上新糊了纸,炕是新烧的,棉被是新的,床单是干净的。K和她是分被子睡的,他提出和她睡在一起,她没有马上同意,说,你并没有说过要陪你睡觉。K说,你既然扮成媳妇了,自然就要睡觉的。她说,除非你再加钱。K不想再多给她钱。他们就在床上争斗起来。K仿佛突然发现她原来倔强得很,挣扎起来非常顽强。他们不停地在床上滚来滚去,但K却什么结果也没有。她说,没有钱就是不行。K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没有钱就不干?她说,对了,没有钱就是不行。K说,提到钱太赤裸裸了。她说,是你太赤裸裸了!那天晚上,K的欲望还特别强烈,为了得到她,K就同意再给她加钱。可能是炕太热了,K说,那个晚上特别想要。她让他拿现钱,他也照做了。K潜意识里可能还有因为在火车上做得太匆忙的缘故。他们后来就做了,K一边做就一边想到多年前他也是带着妻子回来做的,这回却是带回一个婊子。他觉得很畅快。他畅快是因为自己一边做一边说:叶菊。叶菊说:嗯?K说:我干死你!叶菊闭上眼睛。K说:我是花了钱睡你的,叶菊。叶菊说:你就该花钱,你不花钱还想白睡吗?K说:花钱算什么?你是个婊子吗?叶菊不吭声,咬着牙,半天幽幽地说:你不知道?K就大叫起来,婊子,叶菊,你是个婊子!她就把他掀下来,啐了他一口,说:那是你老婆。他想解释,但他每次一碰到她,她就立即把他推开,打他的手。好事就这样收场了。她再不让他碰她。
她是邪恶的,又是性感美丽的。K在晚上发现她特别具有婊子的魅力。但后来不论他怎么许诺,她也不同意和他做了。她只是很耐心地照顾K的父亲,她的孝顺让很多人感动。她甚至为K的父亲清洗身下的污秽。K的妈妈不让她干,她说,媳妇不就是跟女儿一样么?K完全不记得过去的叶菊对家里有这么好。她们两人完全不一样的。毫无疑问,她让K感动了,同时K还感到自己的麻木,想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对他父亲那样亲近,也许是她那种乡下女子善良的本性得到了久抑后的张扬?K的父亲是在一个深夜时断的气,在那个快要断气的晚上K和“叶菊”在守夜。K让她去睡,可是她说她这几天其实一直在失眠,她不想去睡,睡觉只会让她感到空虚,所以她愿意和他一起守着。K当时心里还有点歉意,他以为是她不习惯新的环境失的眠。蜡烛的光暗暗的,他看见父亲的脸草纸一样黄。死人的脸就是这样,一点光泽都没有。她脸上也没有表情,似乎有点伤心。他觉得她这样是伪装的,她像他请来哭丧的,必须要哭得响亮而悲痛,雇主才能付钱。他觉得她其实不必这样,她做得已经很好。她让他妈妈很是心宽,在悲痛里得到一点安慰,她们常常窃窃私语,使K倒觉得自己是局外人。
那天晚上天很冷,月色很淡,风也大。K在屋里听到了屋后树丛里的乌鸦叫,刮——刮——刮——,他打了一个寒战,他之后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不知什么时候忽然被她推醒了,她急促地说:快快快不行了——她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她紧张害怕极了。K就看到他父亲果然不行了,他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一个生命正像风里的蜡烛一样,坚强地燃烧到最后,眨眼之间就熄灭了。这是正常的,住何人也挽回不了,他想她到底是女人。K仿佛还感觉到父亲的一点暗示,他向他做了一个动作,一个无力的动作,他想说什么?那只手在空中划了一下,就像流星划过,那是什么意思?
她伏到他父亲的身上一下失声痛哭起来。
哭声惊醒了他们全家。
K的父亲的骨灰被埋葬在雪地里,他的家人重新为骨灰盒做了一个坟包。K坐在雪地里,“叶菊”哭得眼睛像桃子一样红,全肿起来了。他感觉女人的心太软。一个这样的女人也心软,让他感觉匪夷所思。她在痛哭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感动了,她口口声声叫着“爸爸”,相比之下,K倒是很冷静。他只是沉着脸,他哭不出声来。一个人归于泥土,从此一切就安宁了,平静了,少了世间的一切苦痛与烦恼,也再不被病痛折磨,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活着对他才是残忍的。K后来在坟包上栽上几棵小松苗,这都是他妈妈的主意。她不再哭了,看着他认真地做着。他对她说:你哭得很认真。她说:你爸有你这样的儿子一定气死,一声也不哭嚎。他说:哭有什么用呢?人已经死了,人迟早都是要死的。就是没有一点病,一个人也不能活到一百岁。她听了没再说什么,倒抓起地上的雪,往他脖子里灌。那把雪瞬间就融化了……他感觉一股热热的细流一直从他的脊背往下流,它居然不是冰冷的。他生平第一次知道雪是暖的。
葬完他父亲,他们决定第二天就回城里。
那个晚上,K觉得她怪怪的,她看着他,问:你想要吗?K在她的目光里就有了冲动,他们就做了,做得特别疯狂。她在他身上大呼小叫的。她一边用指甲抓他的肩膀,一边咬着牙说:你是个畜生。他问:什么?她说:你还能来劲,你有这样的情绪,你就是个畜牲。他听了生了气,就更用力地干她。他想她没有权力指责,她是个婊子货,她敢来指责他,真是笑话!她被他干得都要晕过去了,说:你这个杂种,你轻点。他说:我操死你。她说:操你妈,你这个杂种,我要死了。他说:我就要让你死!干死你!那晚上他干了两次,她好长时间不说话,什么也不说。过了很久,在他快要睡着的时候,她把他推醒了,说:账怎么算?他说:什么账?她说:你不要装糊涂,你要给钱。他说:是你逗我的,我给你什么钱?你应该付给我钱才对。她打了他一下,说:不要脸!他说:你才不要脸。他不想理她。她不能什么事都要钱,他觉得这事不能由他来负责。她横起来,说:你不给钱不行,不给钱就跟你没完!他坐起来,说: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她说: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是不想让你白干,你要给钱。他掀开被子,粗暴地说:滚!没钱!她跳起来,说:你不给钱我让你好看。我要嚷得全村人都知道。他气得就打了她一耳光。她跳起来,哭叫起来,在他脸上抓开来,直抓得他身上横一道竖一道的印痕。他一把就掐住了她的脖子,他真想把她掐死,她的脸色慢慢煞白起来,眼珠往外突起。她的身体在他手里一点点地丧失力量。
他可以把她搞死,K想。
“我要……死了……”她脸上现出可怜的神情,他才松了手。
她伏在床上大哭起来。
他怀着一种厌恶的心情,数了钱给她。
她接到钱后没有再看他一眼,说:你是个坏种。
K心里想笑,脸上却没有笑起来。
K对我说:我们坐着同一班火车,又回到了城里。回到城里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到处是灯火通明。她一下子活跃起来。她体内的马达开动了,是城市给她全身通了电。我忽然想带她回自己的住家,但她却没有答应,打了我的手,说:去你的吧,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过你这样的男人。我说:你还没有到一辈子。她沿着路牙走着,在等待出租车。我知道没有希望带她回去过夜。她是个婊子,乡下那几天已经让她烦透了,她需要呼吸城市的气息。只有城市里的暧昧而淫荡的气息才能让她恢复美好的感觉。我裹紧了大衣,也缩着脖子往车站牌那走,她忽然叫住了我。我们站在一块,她掏出一沓钱来,对我说:这是你妈给我的,是她一辈子的积蓄吧。我意外极了,我妈没有对我说这件事。我问:她什么时候给的?她说:你父亲下葬那一天。我想说点什么,她扭头就走了,抛下一句话:我不拿我不该得的。我朝她喊道:她给你的就给你吧。她好像从鼻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
这真是一个让我意外的结尾。
K说他回到家里,拿出那笔钱,感觉那笔钱还有她的体温,事实上它早已是冰冷的。钱,永远都是冰冷的。他数了一下,有三千多。这对于他在乡下的妈妈,当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说他想了想,其实是不应该接下这笔钱的。
听了这个故事,我说不出话来。我在最初的惊讶之后总觉得这个故事有些不太真实,是的,故事不够圆满,有明显的漏洞。就算是K的前妻很少回去,哪怕真的是只回去过一次,村里人没了印象,K的家人也应该是能认出来的。除非这里面有一些更复杂的原因,我猜不出来。
K很认真地对我说:这不是我编的,它是真的,他显然看出了我的猜疑。
城市里漆黑的,我站在窗前,看到在下雪,一片一片地漫天飞舞。我踏过雪地,跳上了火车,往K的老家而去。乡下,我熟悉的乡下……
我走在雪地上。甩下K,甩下城市,甩下过去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