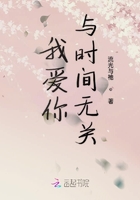一
记忆总是靠不住,小说家契诃夫逝世,过了没几年,大家为他眼睛的颜色争论不休,有人说蓝,有人说棕,更有人说是灰色。同样道理,历史也是靠不住的玩意,有人进行了认真研究,考证出胡适先生并没说过那句著名的话,他并没有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我们更愿意相信,胡适确实说过这句格言,有些话并不需要注册商标,谁说过不重要,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历史这个小姑娘不仅任人打扮,而且早已成为一个久经风尘的老妇人。
一九七四年初夏,我高中毕业了,接下来差不多有一年时间,都在北京的祖父身边度过。这时候,我读完了能见到的所有雨果作品,读了几本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读海明威读纪德读萨特,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读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胡乱地看着书,逮到什么看什么。事实上,北京的藏书还没有南京家中的多,因此我小小年纪,看过的世界文学名著,已足以跟堂哥吹牛了。
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年代,就在前一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分析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有首打油诗,开头的几句很有意思:
五十年代生,今生是苦命。
生下吃不饱,饿得脸发青。
本应学知识,当了红卫兵……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吃“狼奶”长大,公认最没有文化。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像做生意算账要仔细一样,爬雪山过草地,打日本鬼子打“右派”,这些都可以算作资历和本钱,经历了最残酷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却不能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有各的造化,轻易地就为一代人盖棺定论,硬说人家没文化,多少有些不太妥当。记得有一次和女作家方方闲谈,说起我们的读书生涯,很有些愤愤不平,她说凭什么认为这一代人读的书不多,凭什么就觉得我们没学问。本来书读得多或少,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跟有无学问一样,有,不值得吹嘘,没有,也没什么太丢人,可是这也不等于说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
事实上,相对于周围的人,无论父辈还是同辈、晚辈,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属于那种读书读得多的人。说卖弄也好,说不谦虚也好,在我年轻气盛的时候,跟别人谈到读书,谈古论今,我总是夸夸其谈、口若悬河。有一次在一个什么会议上,听报告很无聊,坐我身边的格非忽然考我,能不能把白居易《长恨歌》中“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后两句写出来,我觉得这很容易,不仅写出了下面两句,而且还顺带写出了一长串,把一张白纸都写满了。
女儿考大学,我希望她能背些古诗,起码把课本上的都背下来。对于一个文科学生,已经是最低要求,女儿觉得当爹的很迂腐太可笑。我说愿意跟她一起背,她背一首,我背两首,或者背三首四首。结果当然是废话,女儿的抢白让人哭笑不得,她说不就是能背几首古诗吗,你厉害,行了吧。现如今,女儿已是文科的在读博士,而我实实在在又老了许多,记忆力明显不行了,不过起码到目前为止,虽然忘掉太多的唐诗宋词和明清小品文,然而那些文明的碎片,仍然还有一些保存在脑子里,我仍然还能背诵屈原的《离骚》,仍然能将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默写出来。
丝毫没有沾沾自喜的意思,我知道的一位老先生,能够将五十二万多字的《史记》背出来,这个才叫厉害。真要是死记硬背,一个十岁的毛孩子就能背诵《唐诗三百首》。我所以要说这些,要回忆历史,无非想说明我们这一代人未必就像别人想的那么不堪,同时,也想强调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非常地无聊,无聊到了没有任何好玩的事可做。没有网络,没有移动电话,没有NBA,没电视新闻,今天很多常见的玩意都根本不存在。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现在回想起来,索性废除了高考,没有大学可上,有时候也并非完全无益。譬如我,整个中学期间,有大量的时间读小说,有心无心地乱背唐诗宋词和古文。坏事往往也可以变为好事,我知道有人就是因为写大字报练毛笔字,成为了书法家,因为批林批孔研究古汉语,最后成了古文学者。
二
在一九七四年,我第一次看到了厚厚的一堆小说手稿,这就是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特别关照,别的小说家差不多都打倒了,都成了“黑帮”,独独他获得了将小说写完的机会。我还见过浩然的《金光大道》手稿,出于同样原因,这些不可一世的手稿,出现在了我祖父的案头,指望祖父能在语文方面把把关。后一本书没什么好看的,是一本非常糟糕的书,根本就让人看不下去。我一口气读完了《李自成》,祖父问感觉怎么样,我当时也说不出好坏,回答说反正是看完了,已经知道故事是怎么一回事。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文化像沙漠一样的年头,阅读毕竟是一件相对惬意的事情,毕竟姚雪垠还是个会写小说的人,还有点故事能看看。
在此之前,能见到的小说,都是印刷品,都已加工成了书的模样。手写的东西,除了书信,就是大字报。虽然隐隐约约也知道,我第一次完全明白,小说还是先要用手写,然后才能够印刷成文字。第一次接触手稿的感觉很有些异样,既神秘,又神奇,仿佛破解了一道数学难题,一时间豁然开朗,原来这就是写作的真相。有时候,故事的好坏并不重要,关键是你得把它写出来。李自成是不是高大全也无所谓,它消磨了我的时间,满足了一个文学少年的阅读虚荣心:你终于比别人更早一步知道了这个故事。很多事情无法预料,八年后,《李自成》第二部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我跟别人说起曾在“文革”中看过这部手稿,听的人根本就不相信,说老实话,我自己都有些不太相信。
有时候,阅读只是代表自己能够与众不同,我们去碰它,不是因为它流行,恰恰是因为别人见不到。“文化大革命”中文学爱好者对世界名著的迷恋,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不能够很顺利地看到。同样的道理,人们更容易迷恋那些被称之为“内部读物”的黄皮书,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是因为它们反动,是“毒草”,因为禁,所以热,因为不让看,所以一定要看。有时候,阅读也是一种享受特权,甚至也可以成为一种腐败,当然,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写作也会是这样。《李自成》这样的小说,从来不是我心目中的文学理想,它也许可以代表“文革”文学的最高水准,但它压根不是我所想要的那种文学,既不是我想读的,也不是我想写的。我曾不止一次说过,从小就没有想到过自己将来要当作家,因为家庭关系,作家这一职业对我并不陌生,然而我非常不喜欢这个行当,而且有点鄙视它,因为按照别人的意志去写小说,勉为其难地去表达别人的思想,这起码是一点都不好玩,不仅不好玩,而且很受罪。
一九七四年,民间正悄悄地在流传一个故事,说江青同志最喜欢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记得有一阵,我整天缠着堂哥三午,让他给我讲述大仲马的这本书。三午很会讲故事,他总是讲到差不多的时候,突然不往下讲了,然后让我为他买香烟,因为没有香烟提精神,就无法把嘴边的故事说下去。这种卖关子的说故事方法显然影响了我,它告诉我应该如何去寻找故事,如何描述这些故事,如何引诱人,如何克制,如何让人上当。我为基督山伯爵花了不少零用钱。三午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有着极高的文学修养,常会写一些很颓废的诗歌。同时又幻想着要写小说,他的理想是当作家,可惜永远是个光说不练的主,光是喜欢在嘴上说说故事。
我不止一次说过,谈起文学的启蒙,三午对我的影响要远大于我父亲,更大于我祖父。历史地看,三午是位很不错的诗人。刘禾主编的《持灯的使者》收集了《今天》的资料,其中有一篇阿城的《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很诚挚地回忆了两位诗人,一位是郭路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食指,还有一位便是三午。这两位诗人相对北岛多多芒克,差不多可以算作前辈,我记得在一九七四年,三午常用很轻浮的语气对我说,谁谁谁写的诗还不坏,这一句马马虎虎,这一句很不错,一首诗能有这么一句,就很好了。
关于三午,阿城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很传神:
三午有自己的一部当代诗人关系史。我谈到我最景仰的诗人朋友,三午很高兴,温柔地说,振开当年来的时候,我教他写诗,现在名气好大,芒克、毛头,都是这样,毛头脾气大……
振开就是北岛,毛头是多多,而芒克当时却都叫他“猴子”。为什么叫猴子,我至今不太明白,是因为他一个绰号叫猴子,然后用英文谐音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还是因为这个笔名,获得了一个顽皮的绰号。”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就知道并且熟悉这些后来名震一时的年轻诗人,就读过和抄过他们的诗稿,就潜移默化地受了他们的影响。“希望,请不要走得太远,你在我身边,就足以把我欺骗。”除了这几位,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人,有画画的,练唱歌的,玩音乐的,玩摄影的,玩哲学的,叽里呱啦说日语的,这些特定时期的特别人物,后来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有一个叫彭刚的小伙子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的画充满了邪气,非常傲慢而且歇斯底里,与“文革”的大气氛完全不对路子。在一九七四年,他就是凡高,就是高更,就是摩迪里阿尼,像这几位大画家一样潦倒,不被社会承认,像他们一样趾高气扬,绝对自以为是。新旧世纪交汇的那一年,也就是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在大连一个诗歌研讨会的现场,我正坐那等待开会,突然一头白发的芒克走了进来,有些茫然地找着自己的座位。一时间,我无法相信,这就是二十多年前见过的那位青年,那位青春洋溢又有些稚嫩的年轻诗人。会议期间,我们有机会聊天,我问起了早已失踪的彭刚,很想知道这个人的近况。芒克告诉我彭刚去了美国,成了地道的美国人,正研究什么化学,是一家大公司的总工程师,阔气得很。
一时间,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就好像有一天你猛地听说踢足球的马拉多纳,成了一个弹钢琴的人,一个优雅地跳着芭蕾的先生,除了震惊之外,你实在无话可说。
三
在一九七四年,“毛头的诗”和“彭刚的画”代表着年轻人心目中的美好时尚,这种时尚是民间的,是地下的,是反动的,然而生气勃勃,像火焰一样猛烈燃烧。如果说在一九七四年,我有过什么短暂的文学理想的话,那就是能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像毛头那样的诗人。三午的诗人朋友中,来往最多的就是这个毛头,对我影响最大最刻骨铭心的,也正是这个毛头。毛头成了我的偶像,成了我忘却不了的梦想。我忘不了三午如何解读毛头的诗,大声地朗读着,然后十分赞叹地大喊一声:
“好,这一句,真他妈的不俗!”
从三午那里,常常会听到的两句评论艺术的大白话,一句是“这个真他妈太俗”,另一句是“这个真他妈的不俗”。俗与不俗成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说白了,所谓俗,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所谓不俗,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就是非常非常地独特,老子独步天下。艺术观常常是摇摆不定的,为了反对时文,就像当年推崇唐宋八大家一样,我们故意大谈古典,一旦古典泛滥,名著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又只认现代派。说白了,文学总是要反对些什么,说这个好,说那个好,那不是文学。
有没有机会永远是相对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一九七四年,因为没有文化,稍稍有点文化,就显得很有文化。因为没有自由,思想过分禁锢,稍稍追求一点自由,稍稍流露一点思想,便显得很有思想。有一天,三午对毛头宣布,他要写一部小说,然后滔滔不绝地说自己准备怎么写。那一阵,毛头是三午的铁哥们,三天两头会来,来了就赖在了长沙发上不起来,说不完的诗,谈不完的音乐。也许诗谈得太多了,音乐也聊得差不多,三午突然想到要玩玩小说。他是个非常会吹牛的人,这个故事他已经跟我说过一遍,然后又在我的眼皮底下,兴致勃勃地说给毛头听。在一开始,毛头似乎还有些勉强,懒洋洋坐在那,无精打采,渐渐地坐直了,开始聚精会神。终于三午说完了故事梗概,毛头怔了一会,不甘心地问:完了?三午很得意,说“完了”,于是毛头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说我要向你致敬,说你太他妈有救了,这绝对太他妈地棒了,你一定得写出来。
和许多心目中的美好诗篇一样,三午的这部小说当然没有写出来。人们心目中的好小说,永远比实际完成的要少得多。时至今日,我仍然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故事梗概。一名老干部被打倒了,落难了,回到了当年打游击的地方,从庙堂回落到江湖,老干部非常惊奇地发现,有一位年轻人对他尤其不好,处处要为难他,随时随地会与他作对。老干部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忍让着,讨好着,斗争着,反抗着,有一天终于逼着年轻人说了实话。年轻人很愤怒地说,你身上某部位是不是有个印记,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的战争年代,还能不能记得有那么一位村姑,在你落难的时候,她照顾过你,她爱过你,可你对她干了什么。这位老干部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位年轻人是自己的儿子,是他当年一度风流时留下的孽债。年轻人咬牙切齿地说,你把衣服脱下来,你脱下来。老干部心潮起伏,他犹豫再三,终于在年轻人面前脱光了自己,赤条条地,瘦骨嶙峋地站在儿子面前,很羞愧地露出了隐秘部位的印记。
如果三午将这个故事写出来,如果时机恰当,在此后不久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这样的小说获得全国奖项也未必就是意外。说老实话,就凭现在这个故事梗概,它也比许多红极一时的得奖小说强得多。不妨想一想一九七四年的文学现场,不妨想一想当时文学观念上的差异。“文化大革命”已是强弩之末,“四人帮”正炙手可热,那年头,最火爆的文学期刊是《朝霞》,那年头能发表的作品不是说基本上,而是完全就不是文学。当然,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当时文学期刊上的文字是文学,我以上提到的那些活跃在民间的东西、那些充满了先锋意义的诗歌、三午要写的那个小说,就绝对不是文学。
极端的文学都是排他的,极端的文学都是不共戴天。事隔三十多年,以一个小说家的眼光来看,三午当年准备写的那部小说,就算是写出来,也未必会有多精彩。同样,白云苍狗时过境迁,当年那些让我入迷的先锋诗歌,那种奇特的句式,那种惊世骇俗的字眼,用今天的评判标准,也真没什么了不起。无可否认的却是,好也罢,不好也罢,它们就是我的文学底牌,是我最原始的文学准备,是未来的我能够得以萌芽和成长的养料。它们一个个仍然鲜活,继续特立独行,既和当时的世界绝对不兼容,又始终与当下的现实保持着最大距离。有时候,文学艺术就只是一个姿态,只是一种面对文坛的观点,姿态和观点决定了一切。从最初的接触文学开始,我的文学观就是反动的,就是要持之以恒地和潮流对着干,就是要拼命地做到不一样,要“不俗”。我们天生就是“狼崽”,是“文化大革命”不折不扣的产物,是真正意义的文学左派。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要从事文学,就一定要革文学的命,捣文学的乱。
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开始偷偷摸摸地学写小说,所以说偷偷摸摸,并不是说有什么人不让写,而是我不相信自己能写,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我从来就是个犹豫不决的人,一会信心十足,一会垂头丧气。记得曾写过一篇《白马湖静静地流》的短篇,寄给了北岛,想试试有没有可能在《今天》上发表,北岛给我回了信,说小说写得不好,不过他觉得我很有诗才,有些感觉很不错,可以尝试多写一些诗歌。
到了一九八六年秋天,经过八年的努力,我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尝试过,也发表和出版了一部分,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还有很多小说压在抽屉。这时候,我是一名出版社的小编辑,去厦门参加长篇小说的组稿会,见到了一些正当红的作家。当时厦门有个会算命的“黄半仙”,据说非常准确,很多作家都请他计算未来。我未能免俗,也跟在别人后面请他预言。他看了看我的手心,又摸了摸我的锁骨,然后很诚恳地说你是个诗人,你可以写点诗。周围的人都笑了,笑得很厉害,笑出了声音。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也许是我当时不修边幅,留着很长的胡子。反正让人感到很沮丧,因为我知道自己最缺的就是诗才,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我无法掩饰巨大失望,问他日后还能不能写小说,他又看了看我,斩钉截铁地说:
“不行,你不能写小说,你应该写诗,你应该成为一个诗人。”
这位“黄半仙”也是文艺圈子里的人,他只是随口一说,根本没想到会有什么后果,根本就不在乎我会怎么想。当时在场的还有很多位已成名的小说家,小说家太多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我只是一名极普通的小编辑,实在没必要再去凑那份热闹。一时间,我想起了北岛当年的劝说,说老实话,那时候真的有些绝望。虽然已经开始爱上了写小说,虽然正努力地在写小说,但是残酷的现实,也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真没有写小说的命。
这时候,我已经写完了《枣树的故事》,《夜泊秦淮》也写了一部分,《五月的黄昏》在一家编辑部压了整整一年,因为没有退稿,一直以为有一天可能会发表出来,可是在前不久,被盖了一个红红的公章,又被无情地退了回来。《枣树的故事》最初写于一九八一年,因为被不断地退稿,我便不停地修改,不停地改变叙述角度,结果就成了最后那个模样。我已经被退了无数次稿,仅《青春》杂志这一家就不会少于十次。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在这家编辑部当编辑,可就算有铁哥们,仍然还是不走运。
一个人不管怎么牛,怎么高傲,退稿总是很煞风景。还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南京的一帮朋友聚在一起,像北京的《今天》那样,搞了一个民间的文学期刊《人间》。我的文学起步与这本期刊有很大关系,与这帮朋友根本没办法分开。事实上,我第一部被刊用的小说,就发表在《人间》上。没有《人间》我就不会写小说,那时候我们碰在一起,最常见的话题就是什么小说不好,就是某某作家写得很臭。我们目空一切,是标准的文坛持不同政见者。这本刊物很快夭折了,有很多原因,政治压力固然应该放在首位,然而自身动力不足,克服困境的勇气不够,以及一定程度的懒惰,显然也不能排除在外。我们中间的某些人在当时已十分走红,他们写出来的文字不仅可以公开发表,而且是放在头条的位置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管今天把当时民间文学刊物的作为拔得多高,希望能够公开发表文章,希望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同,还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始动机。官方的反对和禁令会阻碍发展,文坛的认同同样可以造成流产。毫无疑问,民间刊物是对官办刊物的反抗,同时也是一种补充。我们的文学理想是朦胧的,不清晰的,既厌恶当时的文坛风气,又不无功利地想杀进文坛,想获得文坛的承认。很显然,在公开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自己的文字是很难抵挡的诱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家中,有一次北岛来,我跟他说起顾城发表在《今天》上的一首诗不错,北岛说这诗是他从一大堆诗中间挑出来的,言下之意,顾城的诗太多了,这首还算说得过去。安徽老诗人公刘是我父亲的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因为和顾城父亲顾工熟悉,让顾城给他寄点诗,打算发表在自己编的刊物上,结果顾城一下子寄了许多,仿佛小商品批发一样,只要能够发表,随便公刘选什么都行。
写作是写给自己看的,当然更是写给别人看的。公开发表永远是写作者的梦想,有一段时候,主流文学之外的小说狼狈不堪,马原的小说,北岛的小说,这些后来都获得很大名声的标志性作家,很艰难地通过了一审,很艰难地通过二审,终于在三审时给枪毙了。我是他们遭遇不断退稿的见证者,都是在还不曾成名时,就知道和认识他们。我认识马原的时候,还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的马原非常年轻,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标准的帅哥,他还在大学读书,小说写出来了无处可发,正在与同学们一起编一本非常好卖的《文学描写辞典》。而北岛的《旋律》和《波动》,也周转在各个编辑部之间,在老一辈作家心里,它们也算不上什么大逆不道,尤其是《旋律》,我父亲和高晓声都认为这篇小说完全可以发表,然而最终也还是没有发出来。
五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现代派”一词开始甚嚣尘上,后来又出现了新潮小说和先锋小说。这些时髦的词汇背后,一个巨大的真相被掩盖了,这就是文坛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已消失或者正在消失,有的不再写作,彻底离开了文学,有的被招安和收编,开始名成功就,彻底告别了狼狈不堪。“先锋小说”这个字眼开始出现的那一天,所谓“先锋”已不复存在。马原被承认之日,就是马原消亡之时。北岛的《波动》和《旋律》终于发表,发表也就发表了,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诗人毛头改名多多,也写过一些小说,说有点影响也可以,说没多大影响也可以。
多少年来,我一直忍不住地要问自己,如果小说始终发表不了,如果持续被退稿,持续被不同的刊物打回票,会怎么样。如果始终被文坛拒绝,始终游离于文坛之外,我还有没有那个耐心,还能不能一如既往地写下去。也许真的很难说,如果没有稿费,没有叫好之声,我仍然会毫不迟疑地继续写下去,然而如果一直没有地方发表文字,真没有一个人愿意阅读,长此以往,会怎么样就说不清楚了。时至今日,写还是不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再说仍然被拒绝,再说没什么影响,再说读者太少,多少有些矫情。我早已深陷在写作的泥淖之中,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写作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为什么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什么和怎么写,无法想象自己不写会怎么样,不写作对于我来说,已完全是个伪问题。
一九八三年春天,我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显然是因为有些赌气,不断地退稿,让人产生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退一短篇也是退,退一长篇也是退,为了减少退稿次数,还不如干脆写长篇算了,起码在一个相对漫长的写作期间,不会再有退稿来羞辱和干扰。从安心到省心,又从省心回到安心,心安则理得,名正便言顺。事实上,我总是习惯夸大退稿的影响,就像总是有人故意夸大政治的影响一样,我显然是渲染了挫折,情况远没有那么严重。被拒绝可以是个打击,同时也更可能会是刺激和惹怒,愤怒出诗人,或许我们更应该感谢拒绝,感谢刺激和惹怒。
思想的绚丽火花,只有用最坚实的文字固定下来才有意义。我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除了写,说什么都是废话,嘴上的吹嘘永远都是扯淡。往事不堪回首,我希望自己的写作青春长在,像当年那些活跃在民间的地下诗人一样,我手写我心,我笔写我想,睥睨文坛目空一切,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永远写作在文学圈之外。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一句口号,就是要“继续革命”。要继续,要不间断地写,要不停地改变,这其实更应该是个永恒的话题。“文化大革命”是标准的挂羊头卖狗肉,它只是很残酷地要了文化的命,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文学革命。文学要革命,文学如果不革命就不能成为文学,真正的好作家永远都应该是革命者。
二〇一〇年八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