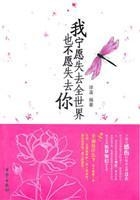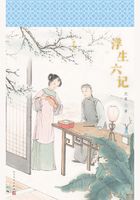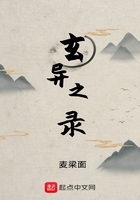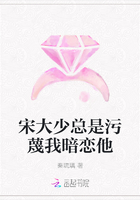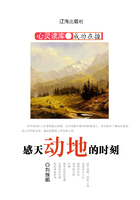来源:《作家》2012年第02期
栏目:海内外传真
捺钵,契丹语,皇帝及中央政府出行的居所,行宮、行在、驻跸地之意。是辽代皇家执政制度的专有名词。辽代帝王与中央政府、皇室成员、地方政要,在一年四季中逐水草而居,春水秋山,冬趋暖夏就凉地伴随着游牧渔猎交换着驻跸地。春捺钵,即辽帝及其中央政府春天的行宮与皇城。
公元2009年,吉林省组织的第三次文物普查取得了震惊世人的重大发现。在查干湖西岸的乾安境内,发现了四处辽代的春捺钵遗址。给考古界带来这一惊喜的,是乾安县文化局的局长马福文和县文物考古所所长王忠军。在全省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会议上,省里专家组的负责同志傅佳欣一再提示,松原的同志一定要注意查干湖周围地带,因为作为绵延了二百多年的大辽帝国,其春捺钵地一直没有被发现,而春捺钵的遗址,一定会在松原境内,在查干湖的四周。
就是省里专家的这一番话,使王忠军同志陷入了沉思。考古发掘这种事的难度自不必说。查干湖的水域有四百多平方公里,很大一部分在乾安境内。而且,乾安众多的湿地、湖泽,也存在捺钵驻跸的可能性。如果从辽代契丹政权兴起算来,至今已千年有余。在这样漫长的沧桑岁月中,许多地貌已经发生了诸多的改变。风雨的销蚀,人类活动的影响,都会湮及历史遗存的信息。若要不漏掉任何可能带来考古发现的重大线索,就要一寸一寸土地、草原的勘察,就要对任何可能掌握历史遗存信息的人进行寻访。而要完成这一看起来极为渺茫的任务,不仅要假以时日,还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和其他物质要素。
2009年11月1日,王忠军家里有一些活忙不过来,就请会泥瓦活计的邢文富帮忙。邢文富是普通的农民,放过羊。当忙完了活计哥俩在一起喝酒闲聊时,邢文富得知王忠军为什么这两年一直走乡串户地野外调查。也就在席间,邢文富向王忠军说起了自己放羊时发现的一些陶瓦片、古钱币和土台基,于是,在邢文富的引导下,王忠军来到了赞字乡后鸣村西的遗址。邢文富把王忠军带到了赞字乡后鸣字村一片开阔的草原。在草原上,可以看到有规则排列的土墩台。与周围的环境相比,土墩台上的植被显然已经遭到人类活动的破坏。土墩台大致都是圆形,也有的是方形,小一些的直径80多平方米,大一点的1500多平方米,最高处大概有三米高,在方圆四五平方公里的草原上,大大小小地布列了520多个这样的土墩台,远远望去,俨然是坐落在草原上的城市建筑群。
当我们把目光落到脚下的时候,看到在裸露的略带碱性的土壤上,雨水使土壤的面层显得光滑,且布满了细微的裂缝。在土墩台的表层土壤上,可以看到许多青黑的陶片。在被雨水冲刷所形成的沟壑断面上,可以分明地看到一些水缸形状的凹形槽,槽里是暗红色的火烧土。火烧土不仅颜色很容易区别,还很硬,握在手里很散落,攥不成团。在火烧土层中,时不时地会挖出一些动物的骨骼。这些动物的骨骼显然经过蒸煮烹饪或是烧烤过,且多为猪骨和牛羊的骨头,是人们作为食物,把肉吃掉后遗弃的骨头。不禁使人们把陶器、铜钱、锅灶和兽骨联系起来。
那么,仅凭这些发现就能将其认定为春捺钵的遗址吗?省文物考古专家认为,在清代以前,乾安这一带还属于郭尔罗斯前旗,是东北的游牧民族活动区,人烟稀少。在这样空旷的草原上,不是皇家,任何民间组织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而且,从营地布局和所发现的一些文物来看,都符合捺钵地的特征。
被考古专家认定为辽代春捺钵遗址的,在乾安计有四处,分别是:赞字乡后鸣村西遗址群,腾字井村北遗址群,让字镇藏字井村北遗址群,余字乡地字村西遗址群。这些春捺钵遗址,大体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集中在查干湖西南岸的地字、藏字和腾字区,这三处遗址,显然是为了靠近查干湖而营造的。另一组在花淖尔湖的湖岸边。从2004年的航拍图来看,这两组春捺钵遗址,都处在两湖的淹没区。规模在5.5平方公里至1平方公里之间。
几乎就在查干湖西岸的春捺钵遗址刚刚被省和国家文物考古部门认定的同时,2010年秋,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的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闫来锁,在查干湖的东岸,前郭县穆家乡的莫古气村东0.5公里处又发现了一处新的春捺钵的遗址,并在十几天后就得到省考古专家的认定。连同在查干湖西岸乾安所发现的四处春捺钵遗址,这已经是一年多来在松原市境内、查干湖周围所发现的第五处春捺钵遗址。
为了在东岸找到春捺钵遗址,闫来锁先期到了查干湖西岸,一处一处地实地考察了春捺钵遗址。随后,他又以闪电方式,走访了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的十几座辽代故城,一边梳理辽代帝王的行踪,一边寻觅辽代城邦遗址的共同点,一边积累资料,学习这方面的经验,以致于一路风尘地赶回松原时,越野车的后备厢里几乎放满了爱不释手的资料,相机记忆卡里也贮满了这方面的图片资料。
在闫来锁的引导下,我来到了位于查干湖东岸的春捺钵遗址。遗址呈带状,寂静地躺在绵延起伏的湖边村落和更远处的庄稼地中间,把人类活动从渔猎到农耕的进化设置了一个自然的过渡带。这个过渡带有3公里长,不到1公里宽。最北端是前郭八郎乡的莫古气村,地势略微仰起,如一个躺着的人稍稍翘起的头部。莫古气,蒙语中也有智慧的头颅之意。这条过渡带由北向南,一直绵延到青山头村,最末端被村落、农田、农田防护林切断。在遗址带的北端,刚从莫古气的“智慧的头颅”上下来,是一条通往查干湖渔场场部的乡路。我就是从这条乡路上走下车来,踏上了这令人敬畏的春捺钵遗址的。
遗址的地貌已呈斑秃状。它既不是草原,又不是白花花的盐碱地。一处处裸露出来的,有如谢顶人白嫩的头顶部分,多呈圆形,是一处处显然高于周边的土墩和台基;而在周边的一处处长满了野草的地方,则是连接着一处又一处台基和土墩的洼地。台基上布满了陶片和瓷片。有两处显然是烘炉的遗址,略带暗红色的黑碴碴的铁焦和铜渣埋在亦隐亦露的碱土中。如果从辽代兴起到覆没至今,已越过了千年的时光隧道,而当时被帝王、宮后及其京几的官宦家眷和军队所给草原带来的伤害,至今仍未能得以平复。[1]
闫来锁是查干湖的原住民和老员工。他还在任基层派出所负责人的时候,就看到周围的村民经常坐在由汽车轮胎的内胎制成的简易筏子上,到湖里打捞古钱币、古玩等。然而却没有把这些散落湖中的文物与春捺钵联系起来。从春捺钵遗址归来,闫来锁又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渔场这些年发现,而由他精心保管起来的一些文物。有古网坠,铁的,陶制的;有鱼叉、鱼钩;有一些由动物骨骼磨制的饰物;也有一些古钱币。查干湖距离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塔虎城”很近,直线距离也就十公里左右,离松花江与嫩江合流之处也就二十多公里。当闫来锁把他平日里零零散散的发现与春捺钵联系起来之后,春捺钵遗址很自然地就浮出了水面。
因为对于闫来锁和所有在查干湖周围生活工作的人们来说,春捺钵遗址是一个几乎每天都会见到的客观存在,而所需要的,只是对它的认知。这些认知之所以极为困难,不仅在于人们要掌握打开历史迷宮的钥匙,还在于人们要有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因为在这些草原的土墩、台基、废墟上,曾经矗立的,是一片巍峨的建筑群,是帝王的宮室,是一座由于四时迁徙而不断游走的皇城。
宋绶《上契丹事》中曾这样描绘到,在东边的方向建了用毡子围成的屋宇,署上“省方殿”的名字,里面都用毡子铺地。后面有两座大帐。接下来往北,又建有毡房,署名为“庆寿殿”,离山还很远。契丹国的君王毡房在西北,只是更远,根本就看不见。[3]
彭汝砺《潘阳诗集》卷八,《广平淀诗》序中说,屋子的门用芦苇编成的箔做成,在编织时不去掉芦苇花,用来作为装饰,称之为羊箔门。在屋顶作为山棚,用木头制成牌子,左边的叫紫府洞,右边的称为桃源洞,总起来叫做蓬莱洞。大殿的名字叫省方殿。山棚之前用花做成门槛(花池),有桃花、杏花、杨柳之类的花木。花阶之下叫丹墀,从丹墀往前走十步叫做龙墀。大殿上都铺上青花织绣的毡子。大殿的台基有二三尺高,三寻左右宽(每寻八尺),在中央部位由台阶登上,成为皇帝的宝座。[3]《辽史丛考》中傅乐焕先生考证后认为,“较《营卫志》所载,省方殿名,两者所同。殿内陈设及殿基高度,亦大体合。彭诗之举箔门,紫府桃源二洞,蓬莱宮诸称,不见《营卫志》,当为‘硬寨’与‘禁围’两重藩籬上名称。”[4]
傅乐焕先生所说的《营卫志》,即《辽史·营卫制》。《营卫制》中对捺钵地宮殿的宏观布列,具体营建,材料选用,功能切分等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皇帝的牙帐以士兵的枪为栅栏,用毛绳连接系牢。每杆枪的下边设置一个黑毡伞,用来为守卫的士兵遮风避雪。在大帐的周围,布列一层小毡帐,每个毡帐可以容纳五名士兵,各自以自己的兵器作为禁卫。在营地的南面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是寿宁殿,都是木柱竹椽,用毡子作为房盖,不设明显出入的门。以彩绘装饰用来挂弓矢的韬柱,用锦缎作为大殿的壁衣,在壁衣的上方另加上一圈红色的绣额。又用黄布绣龙作为地上的屏障,窗的隔扇都用毡子做成,外面套衬黄油绢。大殿的地基有一尺多高,两厢的过廊等小屋子,也都用毡盖,不设门户。在省方殿的北面有鹿皮帐,接下来是八方公用殿。寿宁殿北有长春帐,用卫兵所居住的毡寨加以梗卫。整个皇宮用四千契丹兵轮流执守,每天一千人上岗。在宮禁周围用枪支支撑起营寨,到了晚间则把枪拔起来收缩到大殿内。在更外围,还设了鹿寨拒马,设哨所哨兵,以铃声报警。一年四季,周而复始。[5]
《辽史·营卫制》这段看起来几近于啰唆的描写,对于试图探索千年之前那段史实的人们来说,仍不免过于简约,以致挂一漏万。
比如,营地的占地:南面有省方殿,殿北约二里是寿宁殿。从这段话看,两殿相距约一公里。还说省方殿北有鹿皮帐(当为皇后所居),接下来是八方公用殿(当为会客、会议、宴会、娱乐所用的多功能厅)。寿宁殿(当为太后所居)北有长春帐……从这样的描写来看,营地的规模至少要在两公里以上,而且整个殿的方位和各殿的功能无法确切地描述。再如,上面只写了台基的尺寸,却没有写出大帐的尺寸。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有“南舟北帐”之说。“顷在豫章,遇一辽州僧于上蓝,与之闲谈,曰:‘南人不信北方有千人之帐,北人不信南人有万斛之舟,盖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吴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辽僧之谈合于此。”
另,宋许亢宗奉使到金国的朝廷,见到了金的捺钵地,大体上沿袭了辽人的旧制:“一望平原旷野,更无城郭。近阙,命去伞。北行百步,有阜宿围绕,大三数顷(三数顷,是指营地占地规模),并高丈余(高丈余,大帐的高度)。云:皇城也。”皇城有三数公顷的方圆,矗立在平原旷野上的毡帐有一丈多高。对于宮殿内的描写,许亢宗说,捧着国书从山棚的东边进入。山棚左称作桃源洞,右边叫紫极洞,中间作一大牌,题写为“翠微宮”。……木建隔七间……额上写着“乾元殿”,台阶高大约四尺,阶前有土壇,长宽有数丈,名为龙墀。[6]
宋人对捺钵地描写时也说,捺钵地一般在山坳处,“其地卷阿,负坡阜,以杀风势”。“其居穹庐,无墙壁栋宇。迁就水草,移徙无常。徙帐曰起营,鞑主徙帐以从校猎,凡伪官署皆从行。牛马骆驼以挽其车。车上室可坐卧,谓之帐舆。得水则止,为谓之定营。”[7]车上所搭建的屋室可坐亦可卧,谓之帐舆,说明类如今天的房车,是“以车马为家”的写照,行走之中也是生活。反过来看,这样的车在行走时一定不会追求速度,会很悠闲。
与人们所发现的春捺钵遗址相比,史书和一些典籍所描写的皇宮、皇城,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作为千年不朽的土地、草原、湖泊,还依然在松原这一古老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地挥洒着生命力,而作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王朝,以及象征那一王朝的地上建筑物,则被无情的岁月几乎销蚀殆尽。那些寂寞无言的土墩台,在草原上尽管显得很无助,却依然顽强地保留了下来,且携带着大量来自千年前那个大辽王朝的信息,留待我们去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