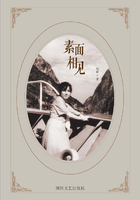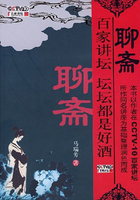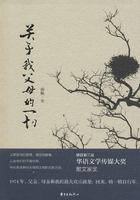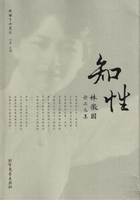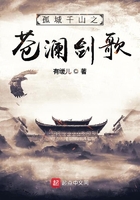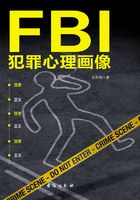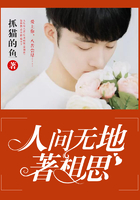在正史中,受到批评、质疑最多的,也许就是《辽史》。由于成书时间短,史料不完备,许多史家甚至把《辽史》看作是未完书。但是,《辽史》中的体例构成及一些论述中,也不乏精彩之处。比如,在《辽史》中,《营卫制》等反映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特色的东西列在了《本纪》之后,就属于正史中的创新,而这种创新,则正反映了这一阶段历史的发展特色。在《营卫制》中,史家有一段开宗明义的论述,对春捺钵的概念作的诠释,为辽代的捺钵依据,南北面官及南北分治等方面的依据作了总结性概括。[8]
在这些诠释和概括上,《辽史》的作者似乎在为一个王朝向世人做出辩解。为什么要做辩解呢?因为作为一个几乎是第一个以阔大的手笔统盘经略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作为一个自始至终都在从事民族融合的大辽,他的行政方式,特别是捺钵制度,在后人看来,会产生一些错误的认知和理解。而且,元人脱脱在修《辽史》时所坚持的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思想,也反映了中华大家庭各民族间追求人格平等的精神,反映了同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金元史官对辽代捺钵制度创新的重视和认同。后来,直到我对春捺钵的了解逐步深入之后,我才发现,时至今天,许多人还不明白“春捺钵”这一概念的准确内涵,不了解为什么要从事捺钵活动,不知道捺钵活动的主要内容,因而也就无从全面认识春捺钵活动。
春捺钵活动,首先映入人们心灵深处的是冬尽春归,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北方又迎来了充满希望的、祈盼丰收吉祥安康的春天。春天,对于农耕社会而言,是播种的季节;而对于渔猎文化而言,春季的生产活动则是钩鱼和猎雁。
钩鱼和猎雁,在《辽史·营卫制》里,只有区区几百字的描述。[9]但就是这几百个字中,就把捕鱼与猎雁,作为完全不同的生产活动区别开来,而且指出了两种活动的时序:先渔后猎;指出了导致先渔后猎的主要原因:天鹅是否来到。既然天鹅还没有来到,没办法,只好先凿冰取鱼。而一旦河上的坚冰融化之后,就无法进行冰上捕鱼,于是春捺钵又继之以猎雁。
冰上捕鱼是北方所独有的冰雪文化的重要内容。这种捕鱼的方式,会使人们形成一种相对于夏秋季节而言的超越自我和自然的能力。由于冰雪覆盖了江河湖泽,人们可以在深不可测的、湍急的、宽阔无际的水面上自由来往,选择最宜处凿冰作业;可以使冰下的拉网作业,在巨大的冰盖子下面形成相对封闭的作业环境,借助冰盖子封堵死鱼儿逃跑的路线。同时,辽帝的冰上捕鱼,还有冰上造帐,张灯诱鱼,薄冰伺鱼,挥叉掷鱼等诸多环节,就使得这种捕鱼方式增添了娱乐的成分和对异族的吸引力。《续资治通鉴长编》(九七2254页),程大昌《演繁露》卷三,对春捺钵的捕鱼活动都做了生动的记述。《续资治通鉴长编》[10]中也说,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是喜欢罩鱼。把毡房设在结了冰的河面上,门遮掩结实,凿开河面上的冰,留出开口的窍,上面用灯来照明,鱼都凑过来,这时再用鱼叉捕鱼,几乎没有失手的时候。《演繁露》中,程大昌相对详细地把辽帝冰下捕鱼活动作了生动具体的描写[11]。在这个描写中,有三个要点给人们极深的印象。一则把契丹挞鲁河钩牛鱼概括为北方盛礼。什么是北方盛礼呢?就是北方的节庆盛典,向南方或是北方其他地方的人们展示地域文化,款待远方嘉宾,如同中原一带时令赏花钓鱼一样,而不是把欢乐留给自己独享,以期在交流中让更多的人们获得同样的快乐,放大快乐的效应,从而引发交流转入交换的良性循环。二则概括了“头鱼”和“头鱼宴”。头鱼,即冰下所捕获的第一条鱼,或是最大的鱼。程大昌的《演繁露》中还说,契丹主在挞鲁河上钩牛鱼,以能否钩到牛鱼,来为一年的丰歉吉凶占卜,在这里,头鱼又具有征兆吉祥的神学色彩。牛鱼、头鱼即得,就要离开冰帐,到专门用作宴会的大帐开“头鱼宴”。作为北方的盛礼,作为一年吉祥的象征物,头鱼宴是春捺钵的重要内政外交活动。对内,犒赏王公贵族和军政大员;对外,安抚属国,修好邻邦。所以,在这里,“头鱼宴”,也可称得上开年大宴,开启一年的吉祥,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国宴,而远非世俗理解的饱饱口福而已。三则展示了冰下捕鱼的场景。这种捕鱼方式,包含着沿河上下十里用网截拦河中之鱼,使二十里长的河道内的鱼都不得跑掉;包含着从河的上下十里往中间拉网,“为渊驱鱼”;包含着透水引鱼、薄冰伺鱼、绳钩掷鱼等诸多因素。而这种捕鱼方式,同如今的查干湖冬捕,已相差无几,说明查干湖冬捕的捕捞方式,保留了千年之前的辽代春捺钵捕鱼的一些传统技术。同时,从钩鱼地点来看,一般在混同江,在鸭子河,时间在正月。在辽代中后期,辽帝的钩鱼活动主要集中在松原的查干湖一带。其中混同江26年,鸭子河14年。另有长春(州、河、水)14年,鱼儿泺、大鱼泺5年。
相对于钩鱼一般在正月的混同江来说,猎雁一般发生在二月的鱼儿泺、长春河(州、水)。当年的鱼儿泺,应该就是现在的查干湖,而长春河(挞鲁河),就是洮儿河注入并消失在查干湖的最末一段。其中鱼儿泺20年,长春河(州、水)13年。如前所说,发生在二月的春捺钵活动主要在于冰泮雁归,天鹅飞来,冰上的捕鱼活动已经完结且无法继续,于是辽帝一行的生活从湍流不息的江河转入相对于是止水的湖泊和即将进入湖泽的河流的尾闾。在这样的地方,地势更为低洼,形成一片汪洋湖,周围长满了芦苇、蒲草、莲荷、红菱等水生植物,成为天鹅、大雁等候鸟生养和哺育后代的理想栖息之地。
《辽史·营卫制》在猎雁方面有一些生动的描写。从那些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当湖面上的坚冰已经开始融化,南方的雁阵已经北归的时候,便开始放纵鹰鹘去捕鹅雁。每天早出晚归,从事戈猎活动。皇帝到达狩猎的位置之后,侍御的士兵都穿着墨绿色的衣服,各自准备一把击打天鹅的链锤,一枚刺鹅的锥子,一个装盛喂鹰食物的器具,以皇帝为中央,在湖的岸边各相去五七步排列。皇帝这时头上戴的是比较随便、不拘官礼的紫皂幅巾,[12]系上玉腰带,站在上风瞭望。发现天鹅的士兵举旗,从外到里的士兵骑马去报告皇帝,远处传来鸣角和鼓响。鹅惊腾起时,左右包围的骑兵举起旗帜指挥着狩猎的士兵。这时,负责掌管鹰的人员擎着海东青向皇帝进献,拜请皇帝亲自放飞。海东青擒住天鹅坠地之后,如果力不能敌,事先布列好的士兵离得近的,举锥刺死天鹅,取出天鹅的脑子喂海东青。帮助海东青杀死天鹅的人按惯例要得到皇帝赏赐的银两和绢帛。皇帝得到头鹅后,作为祭品进献给庙里的神灵。同时君臣之间还互相以酒相酬酢,彼此之间致贺语,大家都把鹅毛插到头上取乐,赏赐随从人员酒食,遍散天鹅的羽毛。
《续资治通鉴长编》(八一1848页)[13]对猎鹅的描写与上略同,更为简约。但重要的是漏掉了“荐庙”的情节,因而也就没有使用“头鹅”的概念,更没有观察到君臣之间相酬酢,致贺语等情感表达,使猎取“头鹅”的活动以“遂纵饮”和“最以此为乐”来做低级感官的满足式收尾,削弱了猎雁猎鹅活动“祭神”的意义和沟通情感的作用。
从捕鱼和猎鹅的活动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是祭天敬神,祈求得到神灵和上苍对大辽的护佑;其次是为一年的丰厚收获开基振首。《辽史·营卫制》使用的“头鹅”概念,《演繁露》中所使用的“头鱼”概念,以及由头鱼和头鹅所衍生的“头鱼宴”、“头鹅宴”,都有开篇、开局、开基、启始之意,是一年之首,也是整个大辽帝国的一年之初,自然也就使得整个大辽万里疆域的纪年在春捺钵地翻开全新的一页。再次,渔猎活动本身,不仅是对边疆武备的检查视察检阅,习武练兵,更是大会诸侯,犒赏群臣,修睦安抚属国的情感交流机会,是北方的重要庆典、契丹的春天节日。
当然,也有的史家并不认为渔猎活动是契丹人天经地义的生产活动,而只如汉家皇帝一样的四处游玩而已。特别是猎雁,只是为了取天鹅嗉中的珍珠[14],这当然是运用了“经济的眼光”,过于低估了契丹人的政治远见。
因为春捺钵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担负视察防务、安抚属国的重要使命。这样讲会不会有什么牵强的地方呢?显然不会。从大量史料中可知,辽帝春捺钵的主要驻跸地在鸭子河,尤其在其后期。而长春州又因春捺钵而建,两者实为一事,是属地的行政区划名与所辖河流名的关系,史书中已有定论。辽之所以在鸭子河一带置长春州,一个重要任务是巩固边防。辽在中后期,以“澶渊之盟”,与宋朝结成兄弟之谊,换来了相对和平安定的疆域,较少战事。也就在同时,与长春州相接壤的女真、室韦等北方藩属国开始兴起。特别是方兴的强悍女真部落,内部逐渐完成了兼并、统一,不肯屈居臣下。在这种情况下,辽对女真加强了戒心,采取了两手策略。既要拴住安抚女真,使其成为与自己一道同大宋抗衡的统一战线,又要防备、弹压、镇服女真,防止演出“养虎为患”的一幕。所以,在《契丹国志·州县载记》中,长春州明确地列在节镇三十三处之中;在《契丹国志·控制诸国》一项中,长春州一带的主要任务被确定为了弹压、安抚女真,以防止其衍生出边患;在《契丹国志·诸藩记》中[15],明确记载了在长春州设置了东北统军司。这些记载,已经把长春州作为边防城和军事基地的特殊军事地理位置充分地揭示出来。正因为其如此重要,才在这里设置了东北一带统辖军队的军事指挥协调机关——长春路(《契丹国志·控制诸国》),而从路一级协调范围来看,已达十余州,北及泰州,南至龙化州、银州等地(见本书“关于长春路中的‘路’”)。同时,也正因为如此,在辽的执政后期,才出现了辽帝春捺钵地一直集中在长春州一带的事实,其维护统一方面的国防意义和军事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作为一个国家,春捺钵活动最本质内容还是经邦济民的经济意义。这除了渔猎本身对于北方少数民族来说是主要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的原因外,还由于长春州作为春猎地,同时还兼有中央政府的财政金融中心职能。根据《辽史·本纪》所记载,在辽兴宗皇帝执政的重熙二十二年秋,公元1053年在长春州设置了钱帛司。这是中央政府所设的三个钱帛司之一,带有区域性货币发行、融资和财政支付中心性质。《契丹国志·州县载记》中对此也作了记载。[16]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把钱帛司设在东北方的长春州而不是其他地区呢?这同样也是与钱帛司职能密切相关的问题。《辽史·食货志》的记载中,对此做了三个方面的回答。
首先,是需求导向。中央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增加,是辽代经济结构不断升级,社会的分工,包括产业分工与区域间交流的日益增强,使得货币的地位,中央财政的作用不断强化。特别是政权建设、城市建设、军队和国防建设方面的支出,严重冲击了建国前单纯靠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经济结构和社会治理结构,客观上要求必须有相应的财政收入结构和支付制度加以支撑。而设钱帛司,“掌出纳”,则是其重要职能。
其次,是地利之便。长春州处在辽国之东,与室韦是鸡犬相闻的邻近。《食货志》中说[17]自从太祖兼并室韦开始,由于室韦这个地方出产铜铁金银,当地人擅长制作铜铁器,加上冶炼开采的矿场和工厂多在辽国东部,所以在东京设置户部司,在长春州设置钱帛司。设置户部司与富产金银铜铁的关系,可能与统计人口、完成税赋、组织财政收入有关;而设置钱帛司,无疑有代中央政府收缴贵重的金属,可与商品作等价物流通的金、银、铜等有关。这种收缴入库的职能,可能还包括了开采、冶炼、加工制造的监督,制成品的入库和再加工,代中央政府保管和转运、支付等职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春州一定会有大型的中央金库,如果不错的话,还应有铸币厂。这当然有待于考古界深入挖掘、探察、发现。
再次,是支付方面。换言之,是货币的投向。中央政府财政的总体投向当然是全方位的,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的区域支付中心会有特定的指向和重点。反过来说,也会由于特定区域、区位的特定需求而催生支付中心的机构设置。从《食货志》中所披露的四组材料来看,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当时中央财政的兴奋点在哪些重点领域。第一个材料中说,石敬瑭又贡献出沿边境地带所积攒下来的钱(应为燕云十六州的贡赋),用来做军事方面的物质储备;第二个材料说,圣宗统和年间,皇帝拿出宮廷的私房钱,赏赐南京的诸军司;第三个材料中说,辽时,每年的春秋,都拿出中央政府的钱摆酒菜宴请军队的将士,钱非常多,所以东京所铸的钱,一直到大辽执政末期的第二个皇帝道宗清宁中期才开始启用(道宗1055年即位,1101年崩于混同江行宮,在位46年。清宁中期,大约在12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第四个材料说,因为受到自然灾害,中央财政拨款,用来赈济贫穷困乏的灾民,以及诸皇帝所建宮室分到边戍的人户[18]。上面四组材料中所提到的钱,分别来自儿皇帝石敬瑭的晋献,皇家的小金库或首长预备费,前朝贮备,中央财政的年度例支。但在支付方面,则主要用于军事斗争和民政,即充军、济民。以长春州所处地接女真、室韦的特殊位置来看,这一带相对富庶,而人口密度又相对较低,所以中央财政在这里支付职能应主要围绕军事斗争和巩固边防的需要。同时,作为捺钵地,承担中央机关、游走皇城的支出,也应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职能。
说到捺钵的支出,就涉及到捺钵参与群体人数,以及每天人均消费总额,相应物资的补给及来源,带动的相关消费等,多半要靠推测来假定,因为史家所留下来的资料实在是有限。
参与群体来看,《辽史》所记,至少应有4000契丹兵轮番值守是没有问题了。中央机关的高级官员、中下级僚属不应少于1000人,宮后、眷属不应少于500人,长春州驻军机动警卫的部队不应少于2000人,加上相关的间接保障人员,参与者应在万人以上的规模(详见本书“札记篇”)。如果考虑到消费,还要顾及到战马、战车、役使的牲畜等,每天耗掉的粮食不会少于1万公斤。当然,军事方面的支出还要考虑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阿骨打起兵之后,先后曾几次在长春州、宁江州一带兵戎相见,少则五六万,多则兴兵一二十万、六七十万,每日度支自然是惊人的。
在考虑春捺钵期间活动时,还要注意到接受属国朝觐的内容。《契丹国志·天祚帝纪》中说[19],天庆二年的时候(公元1112年),天祚帝到混同江钩鱼,辽疆界之外的生女真在千里之内距离的部落长,按照以往所形成的惯例和制度,都来与天子拜会,正赶上头鱼宴。对此,《辽史》记载略有不同[20]。天庆二年春正月,天祚帝到了鸭子河,五国部长来进贡。二月,皇帝到了长春州,幸混同江钩鱼。界外的生女真酋长在千里以内距离的,按照以往形成的惯例和制度,都到天子钩鱼的混同江朝拜,正遇上头鱼宴。从上两书的记载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当天子到达春捺钵的驻跸地,千里之内属国酋长也必须同时抵达,向天子朝拜,进贡,汇报工作;二是“以故事皆来会”(《契丹国志》)和“以故事皆来朝”(《辽史》)。这里所说的故事,可以理解为制度性安排,以及双方必须信守的约定。从制度考虑,接受属国酋长朝拜,交换情报信息,融通彼此之间的关系等外交方面要务,当是春捺钵的一项固定内容,是一种主权关系、主仆关系、主藩关系的天下昭示,也包含了对属国考核、监督、训导、告诫之意,时时提醒着千里奔来的人们,不要忘了为臣之礼、为仆之道、为子之仪。从约定来看,春捺钵地不可随意更换,以当时的通讯水平,以当时的交通工具,以当时的道路建设水平而言,只有捺钵地相对固定下来,人们才可能从千里之外辐辏到一起。
还有一点,就是为了保持契丹人崇武尚兵的传统。这可以从辽太宗与大臣的一段对话中得到证明。会同三年九月,侍中向太宗进行劝谏,大意是,晋主(石敬瑭)听说您经常游猎,意思是请您能够有所节制。太宗回答说:“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也就是说,这类渔猎活动并不是为了游乐,而是为了习练武备,操练将士。所以许多史家也认为,尽管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之后,在逐步汉化过程中都不免流于文弱,而辽则一直保持了骁勇善战的民族精神,这主要得益于捺钵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