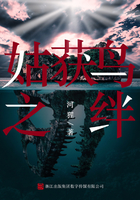平梁县一煤矿发生透水事故
至少三人死亡,三十六人获救,众多疑团待解
本报讯(记者常言)本月四日下午十六时左右,朔方省平梁县仁义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至少三名以上矿工死亡,六名矿工受伤。
据当地安监部门介绍,事故发生时,该煤矿有四十名矿工在井下作业。事故原因初步判断为打通附近的小窑老空水所致。事故发生后,朔方省和西州市有关领导赶赴现场指挥抢险,多支矿山救护队参与了救援。救援人员经过七十二小时抢排积水,救出被困井下的三十六名矿工。这次救援,是该市煤矿救援史上救出被困人员最多的一次。
但是在救援成功的背后,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深思。本次事故在发生八小时后才上报安监部门,比规定的时间晚了六个小时。另外事发矿井地质资料混乱残缺,疑被有意损毁。在报告中,井下当班人数也是经过了三次变动才最后确定。据了解,该矿在生产中长期存在着以掘代探、以探代采、以包代管的问题。
这是平梁县今年以来第二起煤矿事故。发生事故的仁义沟煤矿原设计生产能力三万吨,在朔方省煤炭资源整合中,被列为关闭矿井。
《发展道路报》驻朔方记者站站长常言,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人物,随时身系天下安危。因为经历过的事实证明,他的家庭稳定,经常影响着世界和平。
具体来说,就是他们两口子一吵架,这世界上就准有大事发生。
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他与媳妇就报纸上屡次出现的“本报记者常言、本报通讯员李雪君”现象,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探讨。探讨的成果就是常言最后总算说清楚了那是报社新来的实习生,派给他来带着实习,代价是他媳妇撕掉了若干张报纸。
第二天,常言从电视里看到了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消息。还有三位记者同行遇难。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媳妇与他就“记者站开会发的那套进口化妆品,到底送给了哪个小妖精”为题,进行了面对面的切磋交流。最后常言拉来几个兄弟记者站的证人,才解释清楚了那套子虚乌有的“化妆品”其实根本没发,纯粹是《青年报》记者站为首的那帮家伙的恶作剧,报复常言不肯和他们同去喝酒。后果是媳妇远距离投掷过来的电吹风砸坏了家里的电视机。
第二天,常言从收音机里听到纽约世贸大楼被撞的消息。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媳妇从常言的资料夹里发现一张陈年男女在香山的合影,就问他那女的是谁。常言告诉他那女孩叫李雪君,我在报社时带过的实习生,一起参加工会组织的活动。媳妇又问旁边那麻秆男是谁?常言大笑三声,那不就是当年的我么!媳妇听罢,又看看现在胖头大肚的常言,突然恼羞成怒,在常言的手上狠狠咬了一口。
在常言的疼痛中,大地一阵抖动,汶川地震了。
常言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媳妇,吓得她许久没敢再挑起争端。
后来只要再吵架,常言也就有了独门暗器——“注意世界和平!”尽管媳妇不怎么把常言放在眼里,但对世界和平还是很放在眼里的,所以这办法居然也奏过几次效。
只是慢慢地,常言自己也开始疑神疑鬼,觉得这婆娘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特异功能,她的情绪真的跟世界和平有什么勾搭?理论上说,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完全是有可能的。
这天常言和媳妇在电话里拉家常,媳妇先是客气地问他一个人在朔方驻站累不累,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然后又循循善诱地抱怨,你们报社也太不以人为本了,把你一人发配去朔方,害得本宫独守空房。说到这里常言已经基本上清楚了,这婆娘显然是要把自己诱导上犯错误的道路。常言坚决不上当,故意装糊涂,顾左右而言他。果然,媳妇开始教育他要独善其身,保持革命晚节,不要让朔方的哪个狐狸精勾引了去……
常言见路数不对,急忙把话题扯开:“我们记者部主任恁地可恶,仗着自己是学中文的,就瞧不上老衲的新闻专业,前两天还说新闻没什么学问,只不过是中文专业的一个分支。师太你给评评理,洒家哪一点不如他们?”
电话那头说:“依我看,新闻与中文,都是物理系的业余。”
常言彻底无语。这婆娘学的是空间物理,却是个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写得了程序、斗得过流氓的恶妇,还知道李白的《将进酒》,其实应该念作“枪进酒”,骂人还能骂出“氧化钙”的分子式(CaO)。他曾经用作论文的考据手法,从柳永的词里考证出这位奉旨填词的仁兄到底利用职权泡过几个妞——据称有名可查的有“虫虫、心娘、佳娘、英英、瑶卿、楚楚”等十几个。而且据此得出结论:千古文人,心里都有一个嫖客梦,均是些手无缚鸡之力却常怀叫鸡之心的虚伪家伙。
媳妇根本不搭理他的话茬,继续教育他:“刚到朔方,是不是急不可耐地回西州去了?是不是还在想当年的女同学?你一个人在外,要懂得慎独……”
慎独,这词就相当有文化。常言顺口说:“还没来得及回去呢,正准备过两天去看看,当年班上的校花,如今也不知长成了什么样子。”
电话那头的声音顿时提高了八度:“我知道你这家伙就没安好心!你给我记住,老娘生命里只有丧偶、没有离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小就不是个省油的灯!看见个漂亮的,眼睛里都能伸出手来……”全然不顾常言当年还是个中学生。
常言赶忙说:“小声点、小声点,后来不是看见你了吗?注意世界和平!美国和伊朗正叫板呢……坏了!”
手机上跳出一条微信:“平梁县仁义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被困人数不明。”
常言撂下电话,拎起背包,没头苍蝇般的向平梁县赶去。
三天后。
平梁县的一间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仁义沟煤矿透水事故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县委宣传部长应君堂主持会议。县委书记章培民通报事故抢险情况——按规定,三人以下的事故由县里负责调查。
章培民说:“仁义沟煤矿透水事故,共造成三名矿工遇难,六名矿工受伤。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派出得力救援队伍,经过七十二小时的抢险,三十六名矿工获救。这是近年来平梁县乃至朔方省煤矿事故中,抢险最及时、最成功、获救人数最多的一次。”
应君堂说:“在这次抢险救灾中,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市委市政府及时部署,县委县政府措施得力,在上级的正确指导下,各部门团结协作,共同谱写了一曲抢救生命的赞歌。这次抢险,充分体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以人为本、对职工生命高度负责的精神;体现了各相关部门团结协作、大爱无疆的情怀……”
他接着说:“在过去三天的抢险中,来自省内外的新闻单位进行了大量报道,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抢险工作,我们对在座各位的工作表示由衷感谢!现在,抢险工作已经结束,今天是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大家提问,我希望今后我们有更多机会合作,但是——再不希望在这样的场合了!”
下面的记者们发出一阵轻微的笑声。
“请问章书记,仁义沟煤矿抢险结束之后,县里对下一步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有什么打算?”提问的是《朔方日报》记者吴世升。《朔方日报》是省内新闻界的老大,相当于朔方省的《人民日报》,基本上每次提问都排在第一个,而且吴世升的问题总是提得不温不火,恰好挠到领导痒处,每次都让领导表扬“这个问题提得好”——让人怀疑他们早就串通好了。
章培民果然说:“这个问题提得好。今天上午,我们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将按照‘三不放过’的原则,对事故原因进行详细调查,对安全隐患及时整改,对涉及到的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另外,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我们刚刚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对仁义沟煤矿彻底关闭,封闭井口,从此永远停产!”
听此消息,下面一阵骚动,记者们互相交头接耳。
章培民接着说:“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想表达这样一种决心:尽管平梁县是全省的产煤大县,仁义沟煤矿又是县里的大矿之一,但是,安全为天,生命大于一切。我们必须痛定思痛,壮士断腕,决不能再要带血的煤炭,决不能再要带血的GDP!”
话音刚落,有人轻轻鼓起掌来。
紧接着又有几名记者站起来,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台上的煤炭、安监等部门负责人一一回答。几个问题过后,主持会议的应君堂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这话的意思很明显,新闻发布会到结束的时候了。记者们也都听懂了,有几个准备提问的纷纷合上了采访本,关了录音笔,性急的都准备站起来走人了。
偏偏常言不识趣,站起来说:“请允许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据我们所知,仁义沟煤矿的透水事故已是今年以来,具体来说,是进入今年两个月以来县里发生的第二起煤矿事故,请问这是否暴露了安全监管上的某些漏洞?”
章培民听后皱了下眉头,向应君堂瞪了一眼。应君堂摇了摇头表示无奈。此前,常言已经多次举手提问,应君堂有意不点他的名。谁知道他这时候直接站了出来,作为宣传部长,又实在不好让他闭嘴。这皮球只好踢给章培民了。
章培民很不高兴,反问道:“你是哪家媒体的?”
“《发展道路报》驻朔方记者站,常言。”
章培民说:“原来你就是《发展道路报》的,我还有问题要问你,我们正式公布的事故死亡人数是三名,你们的报纸为什么非要写三人以上?记者同志,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你们要负责任!人命关天,马虎不得哪!”
常言说:“不错,人命关天,这也正是我提问的意思。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至少还有一名矿工下落不明。我非常希望能够证明这名矿工还活着,如果那样,我们会在后续报道中做出更正。如果县里要进行调查,我可以向你们提供他的名字。”
章培民道:“我们注意到你说的那位叫辛孟林的矿工。经过调查,在矿工花名册和下井排班表上,都没有他的名字,所以不能确定是否真有其人。另外我们很不理解,有些新闻媒体的记者,面对三十六名矿工获救的生命奇迹不去宣传,却热衷于关注阴暗面,炒作负面新闻。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你们到底是为政府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
常言说:“事故发生后我到过现场,发现该矿入井管理混乱。不仅事故晚报了六个小时,当班下井人数也是先后变动过三次才最终确定的。”
一听这话章培民有些恼了:“你就不该违反规定,擅自到事故现场采访,知道吗?你是在干扰抢险工作!”
听到章培民说他的采访是“干扰抢险工作”,常言也拉下脸来:“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职责,什么叫擅自采访?依章书记你的意思,这次矿难死亡的三名矿工,难道是被我们的报纸给报死的?”
眼看双方快要戗起来了,应君堂忙出来打圆场:“常站长,您提供的线索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一定认真调查。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他哥哥辛孟贵反映的真实情况,或者是不是另有其他目的。我在这里可以向常站长和各位记者同志透漏一点信息,据县委县政府调查,反映这一问题的辛孟贵,是一个长期上访户。当然,上访是公民的权利,但权利也是有边界的,你的权利不能影响到别人的自由。对不对?同时我们也希望,新闻报道要多从建设性的角度出发,这样才更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不等常言答话,应君堂宣布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平梁县委县政府宴请参加抢险救灾报道的新闻单位。常言在会上刚闹了不愉快,根本不想去,但是应君堂再三劝他和县领导坐在一起喝杯酒,缓和一下气氛。常言脑子一短路,就硬起头皮去了。
晚餐人比较多,县宾馆包间里摆了五桌。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简称“新人经光”的几家大牌媒体早就已经走了,根本没有出席。若不是这次透水事故中有三十六名矿工被救出,这种死亡三人以内的小事故根本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也不会登上他们的版面。那几位只是大篇幅地讴歌了一回抢救生命的奇迹,然后就打道回府了。新华社记者毕敬在抢险还没有结束时,就依照《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套路,写出了一篇《为了三十六名矿工兄弟》的通稿,场面描写得活灵活现。其实常言知道那兄弟根本没到现场,而是一直待在抢险指挥部临时成立的新闻中心。全体记者中,只有常言一人混到了井口附近,但是没采访多长时间,就被火眼金睛的警察和保安识破,请出了现场。常言有意在新闻发布会上搅局,也是在报自己被轰出现场的一箭之仇。
他亲眼看到,那位获救的矿工不仅没有像通稿中那样“含着激动的热泪”对章书记说“感谢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反倒是号啕大哭着骂道:“你们这帮黑心的煤老板,我们的命不如你们的煤值钱啊!什么你们把我救出来的,我就是被你们推下去的!”弄得在场的章培民十分尴尬。
到了宴会厅,常言又有些后悔,觉得自己还是走掉为好。会场上一番龃龉让他实在不想和章培民坐在一起,可是应君堂偏偏把他们安排在了同一桌,还离得挺近。因为“新人经光”走后,常言的报纸就算得上“主流媒体”了。在饭桌上他只认识《工人报》的记者站长闵直方、《经济新报》的记者站长郭戈。除此以外,其他的大都是一些神头鬼脸的人物,采访时不曾见过,现在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有的递过几张名片,五花八门的单位,什么都有。有“中”字头的,是国家级媒体;有“朔”字头的,是省里的报社;还有“西”字头的,那是西州市级新闻单位。新闻媒体的地位是很有讲究的,一般说来,“中”字头的要比“朔”字头的级别高些,“朔”字头的又高于“西”字头的,但也不一定,比如《朔方日报》就是朔方省委的机关报,自是省内第一把交椅,比起某些“中”字头的行业报要牛得多,同理,《西州日报》作为西州市委机关报,又强过许多“朔”字头的行业报。当然,顶级的媒体是“没字头”的,例如“新人经光”,就像是高级领导干部不说职位只称同志或者首长,高级将领往往不穿军装穿便装一样。从这一点上看,常言供职的《发展道路报》有时勉强也混得进这第一梯队中去。
宾馆里众多记者济济一堂,席间章培民有意给常言冷脸看,故意不和他搭话,而是隔过他和《引进导报》的站长钱嘉锡谈得火热。不知道安排座次的应君堂是真不识数还是有意为之,这《引进导报》刊名虽属“没字头”,却是由一个没有听说过名字的行业协会主办,在业内发行量与影响力都不入流,论报社排名其实该到最后一桌去。但是记者站长钱嘉锡是个爱凑热闹的主儿,经常不知深浅地出没于各种场合,常言刚到朔方不久就遇到了他好几次,可谓是十处响锣八处有他。这次采访没见他发一条稿子,还声称“不报事故、不添乱,就是用实际行动支持县里工作”。常言怀疑,自己在井口现场被轰出来,十有八九就是他给县里报的信,因为那天他换上矿工服,拦了辆摩托车往山上走时,在路上只遇到了钱嘉锡一个熟人。
也许是他的工作态度获得了县里的好感,应君堂有意把他安排到了重要桌次。钱嘉锡上了台面也颇为兴奋,频频向章培民敬酒,再三说:“平梁县这种壮士断腕的决心,给全国产煤地区做出了榜样,值得敬佩,我们一定会突出报道!章书记,我们报社准备给您老人家做个专访……”
章培民多喝了几杯,又被钱嘉锡的马屁拍得有些晕,当真摆出一副老人家的样子,挥了挥手说:“你尽管去做!需要费用,一句话的事,咱们县里不差钱!”钱嘉锡听了,乐得嘴歪眼斜,笑起来能从喉咙看到胃。旁边几位神头鬼脸的,也忙不迭地向章培民表态:“我们一定配合县里,做好正面宣传,弘扬主旋律!”
常言心想,什么壮士断腕,只怕是壁虎断尾;什么宣传主旋律,不过是想弄点宣传费罢了。瞧章培民那副嘴脸,就凭他在发布会上那句“新闻到底是为政府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就可以参他一本,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章培民喝到兴处,瞥了一眼旁边的常言,扭头对在座的记者们说:“这就对了,新闻单位是什么?就是喉舌——喉舌发出什么声音,还是要听大脑的,对不对?谁是大脑——当然是党和政府!”说到这里还算靠谱,但是再往下说的话就刺耳了:“喉舌是什么?就是——”他拿起筷子指着桌上的一盘由猪舌头和猪耳朵拼成的名叫“悄悄话”的凉菜说:“就是口条么!对付喉舌应该怎么办?当然是凉拌!哈哈哈……”说完还大剌剌夹了一筷子放进自己嘴里,咬得嘎吱作响。
这话说得连钱嘉锡都有些听不下去了。虽然平时记者也不免这样自嘲,可换了旁人说出来,就不免有些伤面子。这就像是自己的祖国、家乡,或者华中科大校长“根叔”演讲中说的母校,自己可以一天骂八遍,但别人骂不得。这么说吧,人家蒋介石可以谦称自家儿子为犬子,但如果你马鸿逵也跟着说蒋经国你个狗日的,那就离死不远了。
常言把酒杯往桌上重重地一顿,放了不喝,开口道:“我听说古时候文官朝服上绣的是飞禽,武将朝服上绣的是走兽,衣冠禽兽就是这么来的。七品县官论级别,说白了也就是只野鸡。”
章培民当时就被噎住了,自己的舌头和口条混在嘴里,搅动不得。
应君堂忙过来圆场:“我这八品官,补子上还绣着鹌鹑呢,常站长你也来吃只鹌鹑蛋,不就扯平了?各位媒体朋友,喝酒,喝酒,今天一定要喝好。李白斗酒诗百篇,喝好了酒才写得出好文章。”说完看看章培民,章培民这才费力地把刚才的口条咽到肚里,端起酒杯来给大家敬酒。他喝得显然有些高了,加上旁边那几个马屁拍得又紧,一时又有些不知高低,舞动着自家的口条,晃着脑袋卖弄地吟了几句: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又是钱嘉锡转过头来喝彩,巴掌拍得山响,说章书记真是出口成章。其实应君堂知道,章培民每次敬酒念的都是这几句,也只能记得住这几句。他刚才除了打岔以外,也是故意往这方面引,好让章培民表现一下才华。看到效果还不错,应君堂也很为自己补台的机智得意,一副很受用的样子。常言看了心下不悦,随口就接了几句:
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
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
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在场众人听了都有些吃惊,章培民脸色变得红黄绿不断转换,像十字路口的信号灯。应君堂赶忙说:“这诗可不是章书记自己作的,那是李白的诗,《月下独酌》的第二首。常站长,你怎么可以骂诗仙李白呢?”钱嘉锡听罢,也在一旁讪笑:“不知者不怪,不知者不怪嘛!”貌似给常言圆场,实际上在看常言的笑话。
常言冷着脸说:“不敢,不敢,我没那胆子也没那才。不过,这几句也不是我自己编的,是胡耀邦给续的。”
章培民把手里的酒杯往桌上一丢,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这下满桌人彻底冷场了,常言也把手里的筷子一丢,离席而去。
应君堂追到常言的房间,常言没等他开口就对他说,你们县委书记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质问,报纸是为政府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我准备明天在报纸上公开回答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公然把自己摆到老百姓对立面的党政官员。应君堂一听这话,急得把本来准备责备常言的话全忘了,赶紧解释说章书记一时失言。常言没好气地说:“失言,就是不小心说了真话。应部长,你可以告诉他,除了口条以外,我们新闻界还有个说法,当记者的就是条狗,又会舔又会咬。不过我常某是狼狗,不是京叭,你让他小心提防,哪天让我咬住,一定叫他肉疼。”
送走了应君堂,常言再一次想起,每次和老婆闹别扭,这世界就要出点事,居然屡试不爽。这消息要是传到潘基文的耳朵里,联合国是不是该把他们两口子供起来?不过转念想到,更大的可能,是把他们两口子一块捉去毙了。想到这儿,常言的美梦就没再做下去。
从平梁县回来,常言检讨那天的言行,觉得自己也有些过激和失态。和媳妇聊天时提起来,媳妇一针见血地指出:常言,你这是进入了“职业更年期。”
这话深深地打击了常言,事实让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个年轻记者了。换个说法,他的年龄,也许不再适合干记者站了。
他向媳妇表态:“如果到四十岁头上还在这里干记者站,我就去自杀。”
媳妇知道他的话和报纸上说的一样,假话居多,也不认真对待,还半真半假地像计生干部那样给他来了两句:“喝药给瓶,上吊给绳。”让常言一时怀疑,这婆娘到底还是不是自家老婆?转念又想,记者站这工作,到底怎么了?当年他入职时,记者站还是个很风光的单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变得现在这样狼不吃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
记者站是新闻单位派驻各地的分支机构。如果把报社比作一家企业的话,记者站就是各地的采购人员;如果把报社比作一个产业的话,记者站就是原料供应商;如果把报社比作一个国家的话,记者站就是派驻各国的大使。有时候,他们在报社内部也被称为“地方诸候”——每个省的派驻记者不过一两人,和省委书记、省长管的地方一样大。
当然,这都是场面上的说法。而在他们自己内部,更多的时候自称为“新闻民工”——顶着报社的名分,但在很多方面又和编辑部有很大差异,比如说没有北京户口,住房也没他们的份。报社很多决策,更没他们说话的地方。总之,除了布置采访、发行任务之外,“朝廷”的很多事,根本不和他们商量。例如这次记者站轮岗,报社一纸通知,就把常言从富庶的江南调到了边远的朔方。
在常言看来,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江南省一向属于中华大地,而朔方省自古以来,大部分时间都不是祖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战国时期,这里被称作狄戎之地,算是化外番邦;汉唐时期曾纳入天朝版图,后来又长期属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果是唐朝那阵子,他从江南到这里,可以算作是远游,或者行吟,也许是流放;如果在宋朝时候到这里,就算是出国了,要办护照的。每次想到这里,常言就觉得自己像个贼配军。
记者站轮岗时,他满心以为自己会调回编辑部。常言本来就是经济新闻部的编辑,当初他主动提出到记者站工作,还被报社领导当作深入基层一线干事业的典型,大会小会表扬过一阵子。其实他根本没有那么崇高,只因为他媳妇还没成为他媳妇的时候,毕业去了江南省一家研究所。当时他面临两种选择:是当他媳妇的现任老公,还是做他女朋友的前男友。
如今他媳妇受到重用,很快将调回到北京总部。正值记者站轮岗交流,于是他向报社提出回编辑部工作,什么岗位都行。报社领导答应充分考虑他的要求,毕竟他在记者站干得还算出色,况且像他这样的“无知下流”(无党派、知识分子、下派、交流)的坯子,报社真还找不出第二个。
就在全国报纸的头条都是以人为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那天,报社一纸文件把他调到了朔方记者站。他拿着那一页纸,直怀疑有没有印错?媳妇问他,你到底是得罪了领导,还是讨好领导的时候用力过猛,把领导忽悠过头了?在北京没刹住车,开过站直接奔了朔方。
常言这时才恍然大悟,灵山寺那老和尚给他指点迷津,说他的事业线将向北方转移,原来指的是朔方。这妖僧引他花了大笔香火钱,当时他还满心以为是北京呢。
离开江南那天,风轻如怨,雨细如愁。他在自己的微博里贴了贾岛的《旅次朔方》: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常言心想,这贾老头大约和自己心有灵犀,好像一千年前就专门为他写了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