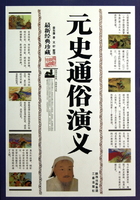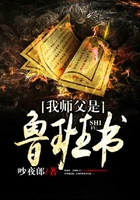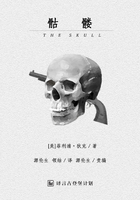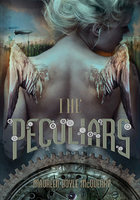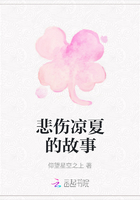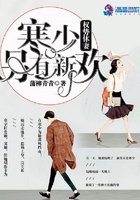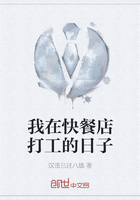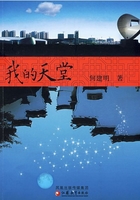来源:《芳草·文学杂志》2014年第05期
栏目:中篇小说
楚米镇最初是一条小街。小街中线是两村分界,北边石爬村,南边烂坝子村。分界线上原先有一块界碑。当年石爬村和烂坝子村争地打架,每次打架必有死伤。界碑今天移过来,明天移过去,还不时被推倒砸烂。传说明成化年间,知县来楚米解决争端,在界碑下砌一间小石屋,把一个行乞至此的叫花子关在里面。叫花子不再是叫花子,被尊为路神。界碑有路神保护,再也没有人敢搬动,地界也不争了。
一九九六年街道改造,将泥土路改成水泥路,铺水泥前把街面铲平铺大石作路基,界碑处的土被运走,有人说亲眼看了,没见到骸骨也没见到棺材什么的。但这并未消除大家对路神的畏怯。水泥地铺好后,原界碑处有一块与众不同的痕迹,晴天是湿的,雨天是干的,天气越晴朗,湿度越明显,雨越大干得越厉害,痕迹有半张桌面那么大,勉强像狮子。
桑原是在楚米镇出生的。他早就定居别处,但他觉得自己是楚米人,不是别处人。一九八三年,桑原考上警校。父亲桑家政叫他补习一年考大学,他没答应,只要能考上学离开楚米,甭管警校农校商校粮校他都去。一九八四年,小公社改称乡,大公社改叫镇,大队改叫村,生产队叫村民组。桑家政在这一年被提拔为吉水县武装部副部长,时年五十二岁。第三年,母亲因学校超编退养,办完手续后到县城和父亲一起生活。桑原的弟弟桑树在这一年走后门得了个工作也到了吉水。桑原回家探亲时只能到吉水,他不大习惯,他高考时在吉水住过三天,在此之前没到县城去过,他总感觉县城这个家是临时的,是陌生的,他常在梦里看见自己无家可归。
桑原的破碎感远没有就此结束。一九九二年,父亲退休了,退休后一个人回到楚米。他声称不需要任何人和他一起回去,因为他回去是有事情要做。桑原回吉水,父亲不在家,感觉这个家很不完整。他到楚米去看望父亲,又觉得这儿根本不能称为家。没回到楚米时,心想一定要陪父亲在楚米住几天,来到父亲的屋子里,他觉得一天也住不下去。父亲的房子在楚米河边,打开门就能看见闪着波光的河水。桑原很喜欢这条河,这条河曾给他带来无数欢乐和浪漫的遐想。但父亲屋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让他感到痛苦:被老鼠啃过的红苕,已经发芽了。掉了一半扣子的衣服挂在柱子上,脏兮兮的。裹满黄胶泥的大皮鞋,硬邦邦干翘翘的。还有透风的板壁,可疑的水瓮,凡此等等。
楚米河之上,有团林、冯家湾、尖山坪、牛鸣塘、苦竹坝十余个村落。再往上几十里,是三县交界的燕毛顶。燕毛顶路径崎岖,三面绝壁。岭北悬崖上有瀑布垂下,在山谷里日夜轰鸣,崖壁上刻了五个字:青泉石上流。说这是楚米来的一个读书人,看了悬崖飞瀑后题写镌刻的。燕毛顶以前是无人区,山林土地都没有主人。光绪十年,有四川綦江人寻找丹砂至此,以为这是世外桃源,把三亲六戚全都迁来,前后迁了三百户。他们在燕毛顶开荒种地,自成一体。可惜好景不长。民国九年,顶上遭受严重虫灾,庄稼绝收,树木死亡,水井干涸,加上土匪骚扰,顶上人纷纷外迁,燕毛顶又成了无人区。直到十年后,才有杨姓、梁姓、王姓等三户人家迁入。因为地广人稀,抓兵派款派不到他们头上。这样悠闲地过了几年,迁入的人家逐渐增多。他们再次自成一体,整修山门,组建自卫队,抵制派款,抵制抽壮丁,不出伕差,拒交厘金,不入户籍。不入户籍,就不是这个国家的人。
因为高度自治,他们日渐富裕。县境交界处土匪猖獗,有一股势力强大的土匪想抢下燕毛顶作营寨,四次攻山,四次被击退。自卫队毫发未损,土匪死了十余人并伤及大半,从此再也不敢骚扰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国人欢呼雀跃,其他乡镇庆祝抗战胜利时没有邀请他们,因为他们既不在户籍上,也没上缴过税款,“不知道他们是哪国的”。燕毛顶有种被抛弃的感觉,既惭愧又失落。第二年春天,由燕毛顶出钱,团林出房屋,从楚米请来先生,在团林的楚米河边设学馆。学馆和私塾不同,私塾只教儒书,学馆增设算术。学馆开张后只来了七个学生,有三个是燕毛顶的,有两个是团林的,剩下两个分别是冯家湾和苦竹坝的。他们都是上过私塾的学童,小的十二岁,大的十五岁。在地里刨食的人对读书没什么兴趣,说读书读不饱,要吃饭才吃得饱,读过几年私塾会写名字会简单记账就行了。
梁大匀是被他父亲梁丙安押送到团林学馆的。梁丙安是燕毛顶自卫队队长,他曾送梁大匀到山下读过私塾,别的孩子三天能背一篇课文,他三天只能背个题目,气得梁丙安把书丢进茅坑,“他娘的永远是个生毛货,笨猪脑壳!”但时间一长,又不甘心,他把儿子带进堂屋,敞开堂屋大门,把一根长扁担横绑在儿子双臂上,再用黄荆条追着抽打。梁大匀跑到大门口,上身一歪,长扁担顺着大门钻出去。梁丙安打儿子相当于智力测验,打完后再次把儿子交给先生,对先生说:我还说他笨,他不笨呀,我在堂屋打他他都晓得逃生,先生你给我好好教,不好好学只管打,打死了不要你负责。梁大匀上了几年私塾,总算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背了下来。到了十四岁,先生说我再也不能教你了,我能教的都教完了,你要么去上新学,要么回家耕读。事稼穑,丰五谷,这点文化也是够的。梁大匀给先生磕了三个响头,欢蹦乱跳回到燕毛顶,他宁愿上山砍柴或者耕地耙田,他和书呀笔呀纸呀有仇,看到它们就心烦。没想到才高兴一个月,父亲又叫他到团林入学,他连连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跑到山上躲了两天,饿得头昏眼花才拱出来。梁丙安之所以逼他读书,是他知道读书的重要性。燕毛顶土匪攻不上来,但抗税和抵制编户入籍并非易事。前不久县长亲自带督察长和行政课长来到燕毛顶,加委梁丙安为燕毛顶剿匪大队长,负责燕毛顶一带安宁,保护山下过往客商安全。梁丙安不想答应,这顶帽子对他、对燕毛顶意义不大,反倒是有了这顶帽子,就得服人家管。县长一眼看出他的心思,答应和他签订文书,燕毛顶仍然可以不出伕差、不入户籍,一切照旧。县长是个白面书生,说话文绉绉,手无缚鸡之力,但梁丙安觉得这人有股气势,他在言谈之间,会让你总是处于下风。梁丙安的苦心和苦恼,梁大匀不懂,即使懂也觉得不关他的事。在前去团林的路上,他满脑子都是对父亲的怨恨。迫于父亲的权威,他不敢大喊大叫,只敢小声嘀咕:“没见过这种人,逼人家读书!”
梁丙安和儿子告别时叮嘱道:给我好好学,学好了我抬轿子来接你,不好好学中途跑回来,我用棍棒接你。梁大匀不点头也不摇头,梁丙安厉声问:听见了吗?梁大匀不耐烦地说,晓得了。梁丙安对先生说的话,和几年前说给私塾先生的一样:他不笨,先生你给我好好教,他不好好学你尽管打,打死了不要你负责。但这次他碰了个软钉子。先生说:我从不打人。梁丙安想辩驳一句,不打怎么行,黄荆棍下出好人呐。看到先生和县长一样,也有深不可测的眼神,他没把这话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