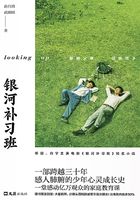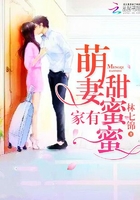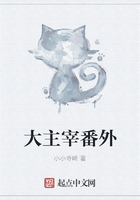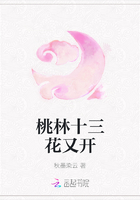来源:《清明》1994年第02期
栏目:中篇小说
三月。
河道里滴水不流。他想:这满河的水呢?流了二十年,就流尽了吗?
太阳也比当年毒辣了许多。
他踩着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忽然感觉皮鞋很别扭,不如当年穿草鞋舒适。
过了河不远便是条儿沟。狭窄的山凹里挤出强劲的风,倒也凉爽。他放下手提箱,掀开夹克衫,一手叉腰,一手夹烟,若有所思地站在村口。
村里很静。偶有狗吠。炊烟袅袅,柔柔地,顺树木缭绕,沿山脊升腾。
条儿沟像一幅静止的图画,静止了二十年。
他很失望。刚才,当汽车翻过一道道山岗,绕过一座座峰峦,驶向大山深处时那一种激奋、那一股渴盼,顿时被一层淡淡的哀伤湮没。
二十年竟没有一丝儿变化?失望变成了黯伤。一回回梦里千奇百怪,说是后山开矿了,煤矿;说是一条金灿灿的大道直插村口,水泥大道;说是家家盖起了洋楼,小二楼;说是村里办起了工厂,竹木加工厂、小型轧钢厂……然而没有,什么都没有,依旧是满目青山,依旧是狭长山沟,依旧是东倒西歪的房屋,依旧是懒洋洋的鸡、懒洋洋的狗。
……天空依然是那轮陈旧的太阳。
人却变了:孩子变成了小伙,姑娘变成了大嫂,汉子变成了老头,老人变成了坟墓。
毕竟二十年了呀!
陌生的眼光盯着陌生的来人和来人的手提箱。
“请问……”他走近村口那户人家。
“你是……哎呀呀,小周!快请进!”
于是女人将家中唯一的毛巾在水中搓了又搓,取半块干硬的香皂狠劲往毛巾上涂,又搓再搓,搓出半盆肥黑的水,然后将毛巾递过来。
他感动了——岁月流逝,热情依旧!
村里在传:“小周来了!”
“哪个小周?”
“学生呀,下放学生!”
“可不:把我这老眼!那辰光,那娃这么点儿高,那么瘦;说着说着呢,这么壮实了,高大了,胡子也黑了……”
东家请,西家拽。满满一屋人围着他,说,说当年;问,问现在。他也说,他也问。
“刘义坤好吧?”
“跛子义坤吗?死了。”
“袁二叔呢?”
“也死了。”
“二婶呢?”
“老了。那不,在沟里洗衣裳呢。”果然有位龙钟老太,一头银丝在风中飘。那是远近闻名几十里的山歌手吗?
“腊狗呢?”
都不肯说,不屑地笑。腊狗讨饭去了。那壮实的小伙,当年的团支部书记,演过郭建光的红脸膛汉子,谈起女人总是笑得神秘而羞怯的愣头青,竟去吃百家饭了吗?
他许久无语。当晚住在冬生家,一夜不曾睡好,乱想。
天刚朦胧,他就起了床,来到村口。
有雾,在村中飘忽,在山涧缭绕。竹林中该有众多鸟儿歌唱呀,却只听得一群麻雀在吱喳。当年见惯了的斑鸠、黄雀、白头翁……都去了哪里?村后的山上,怎么全是些灌木矮竹?那一株株粗大茂密的树木呢?
他站到一截树桩边。这就是当年那株银杏树吗?当年他说这叫银杏树,全村人都笑,说该叫白果树,还给他取了个外号“一姓树”。还记得吗,后来闹鬼,他病了,村上人硬是在曾奶奶的坚持下伐倒了那株两个人抱不过来的银杏树,他好心痛哟j至今他的笔记本里还班门弄夹着几枚枯干的银杏树叶,可是曾奶奶早已作古……
对了,当年这树的旁边不是有一座水碾子吗,那是用来碾米磨面的,以水冲击底盘木页而驱动碾磙,成天“吱——呀,吱——呀”,转动着古老的情韵。可是如今水碾子连同那水碾屋哪里去了?
哦,还是有了变化,毕竟十二年了!
他居然没有注意到,条儿沟也用上电了。昨夜,那昏昏的电灯不是取代了当年的油灯吗?
他顿觉欣慰,心情开朗了一些。
有“嘎嘎”鸭鸣。
一群鸭,足有五、六十只,摇头摆尾,风度翩翩,唱着晨曲。有一人,掮一柄竹竿,竿梢绑一把破芭蕉扇,晨雾中悠悠而来。
盯着那人看,似识,似不识,竟想不起是谁。
“小周吧?”那人问。
“旺生!”他兴奋了,蓦然忆起当年修战备公路时旺生与玉莲那一段故事,那一份痴情。
“放鸭呀?你家的鸭?”他问。
旺生很冷淡。“山分了,地也分了。人多,闲着没事,养几只扁嘴子,能捞几个算几个。”
说罢“罗——罗——”吆喝着鸭群走进雾中,一把破芭蕉扇在半空中摇动。
他笑一笑,点燃一支烟,想:毕竟不是二十年前了!
晨雾更浓。匆匆走来一个影。近前一看,是黑柱。
“小周,今儿晌午在我屋里吃,说定了。”
“你去哪儿?这么早。”
“我到后冲叫我屋里的去。前日她妈病了,她去了。我去叫她回来做饭。”
“随便弄点吃吧,何必跑十几里地。”
黑柱嘿嘿笑,“我哪会做饭呢。”
他心里一怔:噢,男人不做饭,依旧是二十年前的习惯。
黑柱走了,顺着弯弯的山路拐向后山。
他转过身来。条儿沟依旧隐藏在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