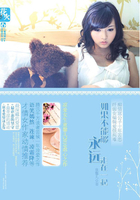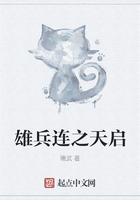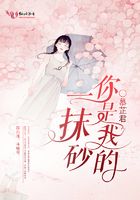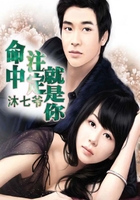来源:《南方文坛》2013年第06期
栏目:当代前沿
题解
“蚕在茧中找到了自己”,原典出王辛笛(1912—2004)写的《香港小品》[1](1982)。此诗感慨其1981年出访香港时获悉的一则史实:一位香港女士在20世纪60年代觅得辛笛1948年版《手掌集》(手抄本)而爱不释手,居然也耗数昼夜抄录全本,却浑然不知诗人当年尚未作古。这当不免让辛笛在庆幸旧作“墙内开花墙外香”之余,又顿生“世上已千年”之感[2]:原来海内外已将其沉寂甚久的诗性复出,视作活的“文物出土”了。毕竟他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九叶诗派”领军人物,却因故自1949—1981年几无新诗问世,然香港却依旧慕名其1948年前的佳作不已,这就太让诗人恍然于“蚕在茧中找到了自己”。当“蚕”意指诗人,“茧”则在隐喻时势对诗性才情的外部约束、缠绕与幽闭。亦可说历史尘封。这可谓名句。
诚然,当笔者借此名句来形容辛笛与其旧诗的血脉关系,则又须注入另层涵义,即在辛笛很少写新诗的三十年间[3],不宜说他已中止创作,相反,他几乎是将此“哀乐中年”[4]的哀婉诗意(实属人性凄美)全蕴结于旧诗了。这用王圣思(辛笛女儿,华东师大教授)的话说,便是其父“在时代处于不太正常之际,用旧诗写作就恰好可以隐晦委婉地表达心绪”[5]。请注意“隐晦委婉”这四个字,无非说辛笛撰旧诗是用文言,且适度用典,故较之白话会幽婉得多——这就酷似蚕躲在茧中熬成蛹,因有银丝的自我缠绕而成外壳,故也就多了一份安全感,以期阻隔外界异样的窥视。
如此题旨导向,实已暗含如下三个子题亟待逐层疏证:
一、为何说辛笛是将其哀乐中年(37—67岁)的人性诗意全诉诸旧诗?此诉诸使其旧诗呈示何种诗学特征?
二、辛笛旧诗的诗学特征,当源自其主体人格纠结,此纠结与诗人1949年前后的角色选择以及现实境遇的错综关联,究竟如何?
三、1979年后辛笛诗艺已“左右开弓”[6],新旧诗体兼擅,然就其旧诗建树而言,真正经得起文学史咀嚼的名篇佳构似已在1979年前写完,相反,“率尔操觚”[7],应景诗却历历在目,这又是怎么回事?
看得出,本文之书写,与其说将触及辛笛的诗艺境界与人格限度,毋宁说也在潜心回味左翼知识者的心路跌宕的轨迹。这就是说,可用两只眼睛来读辛笛:当你用右眼将其读作现代文学史的珍贵符号,同时也不妨用左眼视其为有涉知识分子心灵史的珍稀个案。
“国史冷吟”的立论诗证
辛笛对其诗作的自我评估从来低调而实在。这可从他引用的一段奥登(W.H.Auden)语录见出。奥登为“九叶诗派”特别是穆旦最心仪的欧洲诗人。奥登曾将其诗歌按优劣分成四类:一是“不堪卒读”的;二是有“很好的意思”,但“由于才华短拙”而“没能写到好处”;三是“尚看得过”,“但缺乏重要性”;四是“他自己真诚激赏的诗歌,但若即以为限,结集成书,那么他的集子可就薄得太令人气短了”[8]。如上意思,出自奥登1945年版诗集的一个小序。1947年年底辛笛编就《手掌集》付梓沪上星群出版社时,其后记用了这些话。他说:“奥登这一段简洁完全的文字,虽然写来平易,创作的甘苦却给他轻轻道破。”[9]其实对辛笛旧体诗也拟作如是观。
辑集辛笛旧体诗最早的版本,是香港翰墨轩2002年版《听水吟集》,收作者自1924—2002年6月的旧诗六百零八首(含七律三十五首外,其余大多为七绝)。但不算全,2010年“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有《辛笛卷》(王圣思编),其旧诗又补录“未入集”者二十二首。2012年时值辛笛百年诞辰,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辛笛集》五卷,其卷三《听水吟》虽收如上“未入集”者二十一首,然总体体量缩水了,计一百八十九题,三百五十九首,比港版足足缩了41%,精干不少,耐读多了。若再“瘦身”呢,你又发觉,辛笛最好的旧体诗几乎全写在1979年前的“文革”时期,堪称“国史冷吟”。
“国史冷吟”并非是笔者杜撰,而实属对辛笛“文革”旧诗的诗学命名。此命名所涉“国史”“冷吟”这对关键词,更是典出辛笛。
辛笛曾自序其旧诗能“以诗代史”[10]。此“史”拟有二解:要么“国史”,要么“心史”。学界有人释辛笛之“史”为“郑所南的‘心史’”:“郑所南为南宋遗民,宋亡后隐居吴中,因其晚年‘虑身没而心不见于后世’,故命名其所作诗文集为《心史》。”[11]未免牵强。牵强处有两。一是郑氏《心史》又名“铁函心史”,系苏州承天寺明代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古井发掘一锡匣铁函,中藏《心史》,缄封书有十个字“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所南,郑思肖字),意在既不宜刊布当世,便藏之深井,反倒心安。这就与辛笛旧诗的总体概况有悖。因为辛笛当年不宜刊发的主要是“文革”旧诗,而“文革”前“歌功颂德”的那些篇什,诸如《朝鲜忆游诗草》《长江大桥口占》《瞻仰延安革命胜地,感赋两绝》《国庆献诗》等,不仅早早披世,而且与郑氏“心史”不啻南辕北辙。二是辛笛从不以为自己属“民国遗民”,1949年前夕他作为左倾诗人,是更自期以“潜伏者”身份来祈愿共和国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