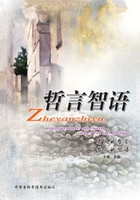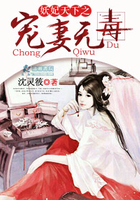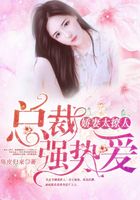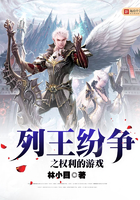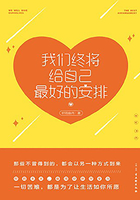——影响我的三位语文特级教师
复旦附中的确是个师生共同成长的好平台。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自身的努力,所有的有利条件交集便会助你不断走向成功!本人的成长也不例外,虽为地理教师,但身边三位语文特级教师的示范作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激励着我不断探索前行。
一、张大文:100斤退稿与6926级台阶
前不久,斗胆呈拙作《旅途印迹》请教大文老师,不料张老师竟在短短一周内,认真阅读并作细致点评,还指出了书中20多个错别字,其严谨学问的劲头,实令我感佩,不禁想到要写写他。
今年78岁高龄的张大文老师已是鹤发苍苍,但他神采奕奕,声若洪钟,不时看到在各地偌大的教室里,数百位学员聚精会神地聆听他讲课,鸦雀无声。而在课堂上,他总是情绪激昂、面红耳赤地说、教、争……还真有点“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之味,但我深知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张老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那仄仄的、耿耿的头颈,不多但切中要害的言语,他那闪烁着坚毅和睿智的目光,他对语文教学的专注。
曾听说,他“文革”初即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懂事的红卫兵批斗他,甚至施以拳脚,令其下跪,戴高帽,高喊“打倒张大文”,他誓死不跪,誓死不呼,吃足了苦头……而第二天,趁着课间操,他竟然一跃跳上领操台,激昂地演说:“今天,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听到了人民日报社论《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他的神情、言辞一如当年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从此,再也无人敢惹他!
张老师是在上世纪90年代评上特级教师的,曾任全国中语会副会长,华东师大、华中师大兼职教授。本世纪初,他退而不休,还在复旦附中上课。他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钻研和探索,寻找语文教学的科学规律,并以文字归纳、总结、提升。那100斤退稿正是他的尝试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中学语文教学体系创新》、《语感教学新论》、《文体沟通》等六七百万见诸报章杂志的作品则是他的丰硕成果,他的语文教学理论是有突破和创新的。他提出,语文教学就应研究:这样的语言文字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思想感情为何要用这样的语言文字,而不用那样的语言文字来表达。即“语言——思想——语言”。这在国内是率先总结提出的语文教学理念,在东南亚还被誉为“张氏教学律”。在此语文教学规律指导下,最有成效的是语感训练,使学生获得快速有效的语言感悟。
“张氏教学律”来之不易,正如他攀登泰山一般。张老师登泰山,与其说是去游览,不如说是考察,“一跨一级,逢十扳一指,逢百画一笔”,一丝不苟得出结论:登泰山至岱宗坊,连同去经石峪的石级,一共6926级。从而对姚鼐在《登泰山记》里说泰山石级“七千有余”的含糊结论,作出了明确说明。这是学者的顶真,专家的坚韧!
张老师从教50多年,学习50多年,为搜集《鲁迅全集》,他利用寒暑假,淘旧书摊;他甚至冒着炎热,穿着“防蚊靴”,埋头抄写《鲁迅全集》中尚未收集到的作品;他为自己立下规矩:一个月读好一本书,并且写好笔记。50多年书教下来,对教材该是烂熟于心、得心应手了吧!但他却并不以为然,只要上课,就认认真真写新教案,他说,人一天天老去,教案却始终是一个个新生婴儿。正是在这不停顿的“否定之否定”中,他的教学水平在不间断地螺旋式地上升。
张老师是有坏脾气的,若见到学生不负责任、弄虚作假……会不顾脸面,甚至不讲方式地予以训斥,有时还会让人感到委屈。然而他还是把学生称同学,与同学交朋友。寒暑假他带领学生过语文生活,师生互相通信,寒假一封、暑假两封皆手写。这样的朋友至今仍保持联系,数以百计。
在1993、1996、1999三届高考中,张老师执教的班的成绩连续取得全市第一。那时,其中一个委托班(高中录取分数低于正常录取分数线)的语文平均分,竟然超过一个正式班的平均分。学生走出考场发自内心地高呼:“张大文万岁!”而这些学生中就有当年被他“骂”过的学生。大文知道后,十分淡然:这无非是我们对语文的理解符合了语文学习的规律,平时思考在点子上,而且化成了操作的能力。
写到此处,我突然明白了这两个数字的含义:这100斤退稿为大文老师创建宏伟的教学学说奠定了扎实基础;而泰山6926级台阶就是大文老师教学若旅的坚实步履。
二、黄玉峰:教学生活得像个“人”
与玉峰兄相识是缘份,与玉峰兄相知是福份。相识相知,几度春秋。自1967年从教以来,黄玉峰始终耕耘在教学第一线。他一贯强调个性化教学,强调“爱的教育”;十分注重培养和保护学生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把学会读书、学会作文、做“真的人”作为培养目标。
所以,作为同事,我一直想写写黄玉峰,却不知从何写起。那天,读到《文汇报》上他的这篇《一棵树》,倒觉得是找到了题材,一吐为快。黄老师在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自豪地称自己是一棵树,这位在特别的年代里曾经“低下过高贵的头,屈下过尊严的膝,弯下过男子汉的腰”的探索者认为他忠实地履行了“不跪着教书”的诺言。
20年前,刚入附中不久的我便能时常见到一位休息日还总在学校忙碌的老师,他就是黄玉峰。从同事的言谈中,我逐渐了解到一些他的情况,无数次的见面寒暄交流,又深知那是一位勤奋又富有思想和事业心的长者,他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实践,充满了人文情怀和道德理念,他的“大语文教学观”同样刺激了人们对基础语文教学状况的深刻反思。他一直认为语文不仅仅是工具,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素质素养,这种思想也在无数次的激情演讲中越来越为人所熟知和理解。
黄老师上课幽默,谈吐自如又不乏激情,在他看来,语文教师要有通古知今的本事,要能写擅画健谈,而他便是这样一位全才,无怪乎学生被他的课所感动所折服所倾倒,而他却不止让学生折服、感动和倾倒,他更愿意通过其煽情和执着,激发学生的语文意识,碰撞青年的思想火花,鼓励学生读书做人,做独立思考的大写之人。黄老师认为: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便产生什么样的教育。以分为本,忽视对人的教育,培养的是一些人格不健全的高分低能儿,为社会发展要求所不容。在他的影响下,质疑成为学生发展的自我追求,做人成为学生迈向新高的内在需要。玉峰爱书,他的学生就是在这个“书为媒”的和谐环境中汲取着养分,成长成材。
有人认为:黄老师的语文课,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是灵动的,而非呆滞的。学生享受着从未有过的心灵的快乐和思想的自由。在他的课上,大量的时间是阅读、诵读、练笔、活动、背诵名篇佳文,明显带有“前传统”语文教学的痕迹,他称之为返璞归真,并就背诵阐述了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独到见解。他在《还我琅琅书声》一文中说,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负责任地批评“死记硬背”,其实,人们所批评的“死记硬背”,就是“吟诵法”,就是“熟读成诵”。在这样的“课堂”上,师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师亦友。
玉峰先生奉行了语文教改服务于学生成长发展的全程和终身,给学生以灵魂的滋养,突出体现了语文教育“人文关怀”的特质。
浏览他给学生开出的书目,细读班级刊物《读书做人》,学生展示的厚实的“精神的底气”和“文化的底气”,使我们欣喜地体味到语文教育是培养一个民族文化意识和文化精神的必要途径。
确实,玉峰所带班级学生的“人的精神的成长”显而易见。对此,北师大钱理群教授在给玉峰的信中说:“读了《读书做人》上的文章,仿佛看见了那些开始学会用自己的眼睛来读书、看世界的年轻人,他们实在是太可爱了,他们身上的潜能实在是无穷无尽的。我从来以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将人的潜在的想象力、创造力、美好的人性因子发掘出来,加以培育、升华。而你们正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读过黄老师文章的人,都有此种感觉:文如其人,无论学术论文还是生活漫笔,不仅言之有物,更有一种手到擒来的自如和潇洒,文字激昂却又引经据典。可以说,我最初的写作冲动,多少受着他的影响,以至于文章的字里行间总流露着一些对教育的思考与忧虑。
黄老师不仅影响着我努力实践自己的人生目标,更在影响着语文教师们,他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校门口经常看到他接待慕名而来的各地语文教师,观摩课和研讨活动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他总是凭借真诚与智慧,赢得同行的支持和信赖。不难想象,他的课一定不是那种预设好的,而是就地取材功到自然成的那种,这符合他的个性和学术主张,否则就不是黄玉峰。当我有机会与外地学者交流时,很多老师会打听他,或说同感于其教育观,只是他们也承认自己的身份不易于引起争鸣。而黄玉峰敢说敢为,这出于他对语文教育的热爱和深沉的思考,是责任使然,如今,新课程改革中的语文教学似乎已有他倡导的那种味了,这一点应归功于他韧性的坚持。
林清玄说,所谓“成功”的人,就是今天比昨天更有智慧、更悲悯、更宽容,更懂得生活、关怀和真爱的人。脸上挂满笑容的黄玉峰便是这样一位成功者,一位大家。
三、黄荣华:语文课堂“生命体验”的实践者
某日,我在二楼教师阅览室看书,无意中翻阅《语文教学通讯》,在“开卷”栏目上有一篇文章《生命本来没有名字》,署名黄荣华,读来感觉真诚、质朴、诗意、有哲理,一如其为人。这使我对黄老师这位长期坚持从“生命体验”与“人的发现”的角度,引导学生阅读与写作,以期解放、激发、唤醒学生的生命力,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逐步形成了“生命体验”和“文化贯通”相融相生的教学特色的实践者,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对他达到的语文教育境界更为佩服。
工作初,黄老师偏爱语法教学,之后转入“知识点教学”;但随着“语文性质观”讨论的深入,特别是在阅读了于漪老师关于语文性质阐释的系列文章和黄玉峰的教育教学改革事例后,根据学生语文成长的内在需求,他确定了语文课堂的落脚点——以语言文字为切入口,读懂文字背后的“生命意识”与“文化意义”,促进学生文化生命的发展。黄老师一次次勇敢而坚决地自我否定,不断调整和发展自己对语文教育的理解和实践,这背后是他对语文教学一贯的专情。他致力于探索语文的内核、语文的本质,为学生生命成长提供最需要的养料。为此,黄老师坚持在课堂开展“生命体验”和“文化贯通”教学的探索,引导学生在生命意识的体验和文化意义的融汇中走进语文的腹地。他认为:语文,理应拥有浓浓的人情与人性。
据我所知,新生入学,黄老师总要给他们布置“9月×日这天”的作文题。“这天”非9月1日,非9月10日,也非中秋节,无标识性。学生拿着此题会感受到很强的冲击力:习惯的思路与想法在这个题目面前失效了。这需要学生从一个平常的日子中发现自己生命的印记,思考生命的意义。这其实也是提醒学生,进入高中后,许多东西需他们重新审视。黄老师要用这样的题目,开启他学生的高中生活新篇章。
循着此思路,黄老师关注着学生发展,常把学生生命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关键点拎出来,设计成作文题,如此三年就构成了促进学生生命发展的独特的写作系列化过程。黄老师非常重视作文教学的这种“过程”,密切关注学生三年写作过程参与的热度、深度和完整度,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情感与思想高度。
黄老师发现,学生阅读时体味不到文章之美,写作时写不出性灵之作,主因之一就是其感受不到汉语背后深厚的文化。2001年,发表《全球化时代汉语诗性特征的价值想象》一文,指出“反省一百年的汉语教学,重新确立既符合本民族发展需要又有利于世界共享的汉语教学的文化体系,应当是目前语文教学改革的重要的议题之一”。
要有文化贯通,先要有文化积累。为强化学生的文化积累,从2000年始,他将《论语》与《古文观止》融合到课堂教学中。他认为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形式主要是《论语》的文化生命形式,而《古文观止》的文化生命形式也基本上是《论语》的文化生命形式。光有中国文化积累还不够,黄老师认为,高中生对外国尤其是西方文化也要有所积累。东西交融,东西参照,东西互释,这是黄老师期待学生具有的“文化贯通”能力。他以《苏菲的世界》为切入口,以“人的发现”为线索,推荐学生阅读西方文学、文化读本。为此,他还积极推进“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外国文化读本部分的编辑出版。
体验生命之“情”,融汇文化之“思”。他认为,“教育就是对生命进行文化约束的同时,唤醒、解放其生命力,故对生命具有约束与解放的双重意义,语文教育本质正在于此”。黄老师不愿迎合讨好学生的“需要”,他践行鲁迅先生“不能用秕谷饲养青年”的原则,不把对学生生命发展无意义的东西带入课堂。他说:“老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在你所任学科的学识上是不平等的。”他以文化约束为基础,唤醒、解放学生的文化生命力和表现力。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黄老师对语文教育的深情与深思,是“朴素实在地播撒在教学的全过程”中的。并非全部的学生都能在当时就明白黄老师的良苦用心,也有同行对其做法持怀疑态度。但他认准了,一如既往地坚持着。鉴于此,他领衔并主创实践多年的《阅读“中国人” 书写“中国人”——彰显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实践研究》教学成果获2014年上海市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至此,我又想,黄老师把杜甫的诗讲得那样具有生命力和文化性,对杜甫的诗歌创作可谓有着全面的了解与独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黄老师在生命体验与文化贯通中,真正触摸到了这个孤独而伟大的灵魂。
在一次聚会上,一位中学同学曾说道:成功离不开5个“人”——高人指点,贵人相助,内人支柱,小人监督,个人努力。当时皆一笑而过,而今,我以为此言虽近于戏谑,却独特高妙、见地颇深。谁都期盼被成功的光环笼罩,谁都期望在迷茫时得到高人指点迷津,谁都期待在困境时得到贵人一臂之力。诚然,解决人的智慧和觉悟及方向等人生关键问题,是需要有高人指点的。而我以为,以上三位皆高人,在成长途中,三位语文老师的示范力量也是对我这个地理教师的实际开悟。他们是我不断学习的榜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今天写出来,也是希望对大家有所启迪。其实,路就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