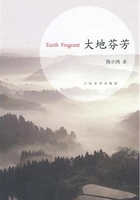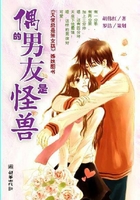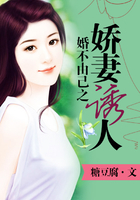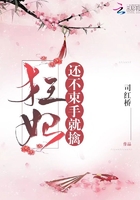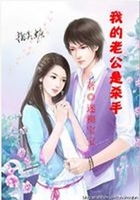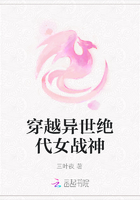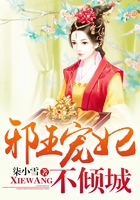我的抽屉里,放着一只牛皮纸的信封,里面有一本书,书里夹着几张发黄的纸。我知道具体的内容,也知道它们代表的含意,轻易不去打开它,细细地推算一下,大概有四五年没有动它了,尽管我常常看见它们,而且,在内心,我知道他们静静的存在,对我未来生活的意味。
今天一早,我刚到科室,就听说,医院要重新规划,紧靠南墙的太平间、配电房和木工房,都要拆了。这个消息让我的心一痛,久违的心酸和悲哀,像决堤的河水,顷刻间蔓延和淹没了我的全身,几乎不能自持。中午回到家,我急急忙忙打开抽屉,拿出已经磨破的牛皮纸信封,怔怔地不知道是否该打开它,老夏,那一张似乎精心设计过的、只显示百分之七十五的笑脸,活灵活现地,凸到了我的眼前。
九十年代初,我从医学院毕业,回到了家乡,分在县医院,做了一名临床医生。第一年在外科轮转,第二年定科。我那时年轻气盛,一心想做个手到病除的外科医生。每天下班后,不管是不是值班,我都呆在急诊室,抢着做一些下手的活,还乐此不疲,是名副其实的住院医师。那年的夏天很热,人都躁狂,天天有打架的来急诊室,头破血流,我正好有机会练练基本功,清创、切开、止血、缝合。有天晚上,大约九点多钟了,一直不忙,护士们笑我没有练兵的机会了。我刚到医院,脸嫩,不敢回嘴,只好低头喝茶。正说着,外面一串哭闹,我知道来了病人,忙趁机会跑了出来,免去了尴尬。一帮人抬着门板进来了,门板上的人,全身是血,那血,从大门一直滴到急诊室里,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和哀伤。哀伤是因为巨大的哭声,足以掩盖黑暗中所有的声响。我和值班的主治医师一起走过去,一听心跳呼吸,都没有了,就知道人已经死了。问缘由,是盖新房从梁上摔下来的,大概是摔破了脾脏,又在乡村,等救护车送到城里,没救了。一说死讯,哭声更响了。主治医师走了,我在一旁暗自叹息,值班护士走过来,对我说:“别发呆,去叫老夏啊。”
我不解:“老夏?”
护士:“老夏!”
我问:“谁啊?做什么的?”
一起大笑起来,又一起掩住嘴,怕被病人家属听到,值班医生过来,对我小声说:“就是住在太平间隔壁,专门给死人穿衣服的,你去一趟,就说急诊室有事情,他就知道了。”
“啊!去太平间?”我不自觉中发出了声。
“害怕?不会吧。就在住院大楼后面,路不远,快去吧。急诊室还要来别的病人啊。”值班医生用命令的口吻说话了。
我只得满心不情愿地向后面走去。我不是怕死人,是担心来了新病人,没有参与抢救的机会。
太平间并不难找,就在住院大楼的后面,紧靠着医院的南墙,一间可以看到天的平房,再过去,有个小间,斜接着太平间,我推测,该是老夏的住处了。我离得远远的,先喊了一声:“老夏!老夏!急诊室有事情了。”
“急诊室吗?就来!”居然是普通话,虽然带有吴语的口音,但在我们这一带,算是很标准的了。
我立刻如释重负,知道完成了任务了。刚要转身,老夏说话了:“你是新来的医生吧,没听过你的声音么,我还有几件衣服,漂一漂就好了,你可以先走,也可以等我。你姓什么?”
好奇心立刻拉回转了我的脚步,我慢慢地靠近那间小屋,明亮的灯火下,一位七十开外的老头,上身圆领的老头衫,下身长裤,还穿着袜子,套着拖鞋,满弓满架,正在漂洗他的衣服。这么热的天,这么大的年纪,居然穿得如此的齐整,令人不可思议。漂洗的衣服不多,就一件圆领的老头衫,一条长裤,一条短裤,都是他自己的。从身架和手势看得出很熟练,完全可以和我的母亲媲美。他背对着光,但我可以看得出他在对我笑。那笑,就是我后来形容他的,似乎精心设计过的,只展现了百分之七十五的笑。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对此的解释是,他从事的工作,使他形成了职业性的笑,不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笑容,那样容易让周围的人不舒服。我却不这么看,第一次,我就发现,那笑里,饱含沧桑和无奈,这是后话了。
他很熟练地漂洗、拧干、晾好,再洗净手,整好衣服,套起胶布围裙,换好胶鞋,点好烟,来到隔壁的太平间,推起帆布车,跟在我后面,向急诊室走去。一路上,我听他哼着什么,细一听,好像是京戏,带点凄婉的味道,歌词听不确切,但我能听明白,他哼来哼去,就那一句。
来到急诊室,死者的家属们,又不愿意让死者留在医院的太平间了。此地的风俗,死人要留口气回家,只有这样,死者魂灵才识得家,方可以获得亲人的供奉。既然如此,大家也不勉强,老夏就只好推着空车,依旧哼着他的戏词,衣着整齐地回了太平间。
这就是我和老夏的第一次相识。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大热天也穿得整整齐齐,烟瘾极大,走路爱哼着戏词,似乎挺乐观的一个老头,仅此而已。
那时医院的生活条件并不完善,夏天洗澡也没地方,没有公共浴室,只在锅炉房有间小小的水池,是烧锅炉的工人们下班后自己洗澡的地方,不对外开放。我们一帮小青年,身体也壮,平时就是冷水澡。想洗热水澡了,就去找烧锅炉的小王,他喜欢钓鱼,都叫他王阿呜(猫吃鱼的声音)。他爱抽烟,我们常常把科室里病人递的散烟,收集起来,晚上就送给他,顺便就可以洗把澡。那些没有“后门”的人,就只能把水打回宿舍,擦擦身,意思意思。住在医院附近的一些医生,也来医院打水回家洗澡,水就不够了。医院的后勤,为了限制用水,要求不住宿舍的人,打水一律要买水筹,一毛一根,一根一壶热水。那天,我和科室的几个小青年,正准备到锅炉房洗个澡,在锅炉房大门外,和小王说着笑话,老夏来了。大热的天,还是一身整整齐齐的穿戴,尤其脚上,穿着丝袜,还套着双皮鞋。看上去,确实比一般的老人精神。他左手两个水瓶,右手一只大水壶,看到小王了,先点点头,把三根水筹放到了板凳上的铁盒子里,然后,再去打水。水灌好了,他再跟小王点点头,依旧哼着那句听不清楚的戏词,身板挺挺地向太平间走去。在人来人往的打水队伍里,我无意间发现,放水筹的铁盒里,就只有三根水筹。我带着疑问的目光,转向小王,因为收水筹是他的工作范畴。小王看到了,嘴一撇:“公家的水,那么认真做什么?你也不想想,什么人才有资格住在医院附近?都是各科室的主任啊!这帮老家伙不主动给,你去追着要?就他,说天天打水洗澡的,明明住在医院里么,能省不省,真是个呆虫。”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注意起了老夏。因为职业的原因,在医院,基本上没人跟他打交道,谁也不屑去注意到他。
真正和老夏的亲密接触,是我的朋友父亲的死亡。
应该是那年十月底的事情了。我朋友的父亲,一直有高血压病,突然并发脑梗塞,住进了内科。经过半个多月的抢救,没能救活,晚上八点多钟,去世了。全家人哭成一片,都没了主意。我毕竟在医院呆了一段时间,有了些经验,问他们如何处理。朋友说,就放太平间吧,家里是楼房,又小,根本放不下的。我就当仁不让地去请老夏了。我来到老夏的屋外,轻声地问:“老夏在吗?”
门里老夏说:“哪个科有事情啊?”
我说:“是内科。”
老夏说了:“是于医生吧,进来吧,我还有几针收一收,马上就好。”
我第一次推开了老夏的门,走进了老夏的房间。
老夏那年,按照准确的年龄来算,该有七十一二了,但他的房间,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孤寡老头的房间,有异味和零乱。房间大概十四个平方左右,地上和墙上,一尘不染。家具不多,就两只大衣柜,一只杂物柜,几张木凳,一张床。床下有夜壶,老式的那种。换洗的内衣,一件件叠好,放在床头。杂物柜分好几档,最上面一档,散放着一叠旧报纸和几本厚薄不一的书。我这人,对书有天然的亲和力,立刻就走了过去,一本是没有封面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本厚点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下两册,再有一本,是繁体的《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的。还有几本大开本的书,居然是毛衣的编织技巧之类的书籍。老夏呢,就坐在房间的中间,那张唯一的藤椅上,在织毛衣!
我当时就惊住了。
老夏在织毛衣!
老夏头也没抬,娴熟地收好针,抹平毛衣的前摆,放平在床上,也不看我,随口便说:“给我女儿织的,马上天冷了。”
他起身,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套起胶布围裙,换胶鞋,点好烟,拿好钥匙,打开隔壁的太平间,推起帆布推车,对我说:“于医生,走吧。”
他的井然有序,让我充满了疑问。为什么在任何情况面前,他总是从容不迫呢?
来到内科,老夏先问家人,穿戴的衣服准备了没有。家人说都准备了,老夏说,那你们把衣服拿来,都出去吧。对我说:“于医生,你留下,帮我一把,不害怕吧?”
我当然不怕。我朋友的父亲,我一向称他为伯父,叫了有十多年了。直至他死,我都在他身边,没有丝毫的害怕。我是奇怪,为什么老夏会让我留下?
老夏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打来一盆热水,先绞一把热毛巾,捂在张开的嘴上。他说,如果不及时用热水捂嘴,到火化前,嘴都是张开的,很不雅观。果然,只五分钟左右,老夏拿走毛巾,用手轻轻一托,嘴就合上了。然后就是脱去全部的衣服,抹身。疾病死亡的还好,全身只是有点脏,如果是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那最难收拾了。全是血,还有油污,还有垃圾,还有没有缝合的伤口,那样抹身才困难呢。抹好身,开始穿衣服了,讲究了,要上四下三。为什么要这样?我问老夏,他也说不出来,他说,从他开始做这一行,就有了这样的规矩。我看他穿起来非常的利索,根本就不用我帮忙,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有了问题就问。据他说,穿衣服要赶在死亡的两小时以内,不然骨头就硬了。我想起了读书时学过的法医学,尸僵的时间,好像就是两个小时,他不知道理论,但他会用。衣服穿好了,套袜穿鞋,鞋有讲究,前面要放点纸钱,算是买路钱,阎王好见,小鬼难挡。怕小鬼挡路,延误了赶路的时间。鞋一定要合脚,合脚才跑得快,能尽早投胎,投个好人家,免得下辈子做牛做马。洗漱穿戴完毕,老夏要我和我的朋友一起,把伯父的身体,抬上帆布车。要脚向外,头朝里,意思是一路走好。然后,在一片哭声中,向太平间走去。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自始至终,他的嘴上,都拖着一根烟。说拖,是因为那支烟只有很小的一点叼在他的嘴里,其余向下斜着,烟灰再长也不抖掉。也不见那烟在燃着,但是,当工作进入了关键时刻,他就狠命一吸,红光闪闪,烟灰直掉,满鼻满眼都是烟味了。等烟散了,他的衣服也穿好了。我的理解,那烟,从某种意义上,是他的防毒面具。
一路上,他不紧不慢,嘴里还是哼着那句戏词,我想了几次,都没敢开口,他唱的到底是什么呢?
快要进太平间了,我和朋友走在前,因为屋矮人高,老夏赶忙叫:“低头!低头!再高的人,到了屋檐下,谁敢不低头啊。”
摆好尸体,脸上化妆,妆毕,黄纸罩脸,点上蜡烛,烧上香,放起哀乐,伴着阵阵哭声,哀伤痛苦的味道就出来了。本地的风俗是三朝,即要放三天,任亲戚朋友凭吊和瞻仰。我和朋友到一边,跟老夏谈价钱。常规的是六百八十元,包括穿衣、化妆、蜡烛、香、纸钱等一概用品。老夏问我:“是你什么人?”
我说:“世交,一直叫伯伯的。”
老夏说:“那就算五百。一分不多收。”
我说:“那不行,你做几个钱不容易的。”
老夏笑得有点得意,难得看到的表情,声音很小:“于医生,也就跟你说,这个医院,除了院长,就是我的钱多。说定了。”
老夏说完,就走回他自己的房间了。一会儿,拿着水瓶和水壶,要去打热水。我奇怪,天近十月底,已经很冷了,他还要打热水,在自己的屋里洗澡吗?
我陪着朋友和他的家人,准备一起守夜。天很冷,我们的心更冷,哀叹和讲述一样的哭诉,使人肝肠寸断。几个亲戚在忙碌着,做白衣、联黑套、缝小红帽子,那是第三辈的小人必须戴的。已经有亲戚来吊唁了,要忙着接待,子女和爱人要陪着一起磕头,我没什么事情了,就慢慢地踱到了老夏的门前。听得水声一片,还夹杂着他的哼哼,还是那句凄婉的戏词,带了点苍凉的味道。我不敢出声,静静地蹙在门边。他唱得有板有眼,我在心中静静地默数,这句词,完整地唱完。足足要两分钟的时间。在他反复的吟唱中,我慢慢地听出来了,那戏词好像是这样的一句话:未开言思往事心中……,最后两个字还是没听清楚。
为什么他要反复地哼唱这样一句戏词呢?
我觉得老夏本身,就是个谜。在不知不觉中,我对他有了更大更浓的兴趣。
门忽然开了,灯光像聚拢的强光一样,罩住了我全身。我一下子脸就红了,好像一个正在掏包的贼,被人当场捉住了双手。老夏是出来倒水的,他看见是我,并不吃惊,倒完水,对我说:“今晚没有觉睡了,先到我屋里坐坐吧。”
我只好跟着走进了房间。这是我第二次来,感觉就不一样了。在如此寒冷的夜里,踏进如此温暖的家,简直是天壤之别啊。房间里所有的陈设,看上去都觉得亲切,恍惚中好像走进了自己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