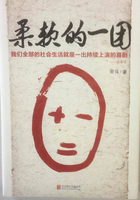我拖着一箱破碎的爱来到马德里的那天晚上,下着雨。一个西班牙女人去机场接我并且把我带回了家。
她告诉我,她明天要回马拉加。早上会有人来接我,并把我送去学校。
那个人是她男友的弟弟。
西班牙女人从柜子里拿出一本画册对我说:知道吗?这是我男朋友!他是画家!
她怕我听不懂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西班牙女人亲吻画册时鼻孔上两个金环儿不停晃动,发出了一种清脆的响声,像一首童谣。
她又说,明天他弟弟来接你!女人见了他,都会发疯!
说完,她把这本已经印上了三个红唇的画册放进了镶着金边的黑色柜子并上了锁。
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天真。尽管这个西班牙女人看上去比我大很多岁,但那种喜悦只属于恋爱中的年轻人。
我不知道那个西班牙女人是什么时候走的。门铃响时,我正在厨房洗杯子。当时我只想喝水却发现所有的杯子都泡在水池里:咖啡杯,红酒杯,水杯,啤酒杯,还有两只儿童可乐杯明显标着MAC赠送字样。
有人在电话里问,你是无依吗?我是桑。我在楼下等你。
五分钟以后桑上了楼,因为我一直没有下去。我等他上来是为了帮我拿两个行李箱。它们对我来说太沉重,装满了十年逝去的青春,永远不可能回来的年轻和美貌。
我,那个曾经光彩夺目的夫人和母亲。而今觉得自己就像一具干尸被装进这个行李箱又亲手把她拖到马德里,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
我打开门,只见两股泉水涌来,便大喊一声:人在哪儿?
你好!桑说了一句中文。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桑就站在身旁,刚才自己看到的只是他的两只眼睛。
Hola!我说了一句西语。
桑解释他只会说“你好”这一句中文。
我解释西语只会一点,于是下意识地打起了哑语手势。
我上了他的车,车子行驶在马路上,不停地发出怪叫。
桑提醒我系上安全带。那时的我,心是乱的。就在我上飞机前的那天下午,随着天空中一只怪鸟飞过头顶,嘶叫一声,鸟屎挂在我头发上,我还没有来得及问自己为什么突然就跟着我的白发先生来了这个地方,而我们已跨出民政局大门,从此结束了我们戏剧般的婚姻。
那头白发突然对着天空长叹一声:当年,一堆乌鸦屎掉在我头上,我就成为了诗人。命!这是命!都是命!
我再一次朝天空望去,天上什么鸟都没有,只有两片乌云。他那头白发却已消失在北京这条堵塞的三环路,似乎从来没有通畅的时候。
我爱他!我坚信直到现在依然那么爱他,那头白发,那个老人,那个永远长不大的诗人。
直到多年以后,我望着马德里的天空渐渐暗下来的那一刻,我依然觉得还爱着他,爱得那么深刻,像是血和泪交汇的河流翻滚着,每一分钟都不能停息。不能去想!因为那会使人死亡。如果死亡足以证明爱情,如果死亡可以挽回从前的恩爱,那么我想用命去换取。因为死亡也无法使过去重新开始,于是我选择了活下来!
那夜,我坐上飞往罗马的飞机,意大利小伙递给我红酒时,我说了句Grazie!那么自然。好像我们在罗马的日子就在眼前,那头白发似乎还躺在身边,在罗马一家陈旧的酒店,电梯老得让人感觉随时要出故障。如果没有爱,我们怎么会每分每秒在一起,从不分开。就是上厕所的时间都要相互道别一声。
诗人欧阳江河说,人家是一辈子夫妻,你们二十四小时在一起,这辈子也就是两辈子!
似乎午夜巴黎还在眼前,为了让我见到巴黎圣母院,为了让我见到埃菲尔铁塔,诗人多多盯着巴黎出租车上的计价器不停地唠叨:他为了你,不要命了!
而今,我坐在同一架飞往罗马的航班,我却离开了他!离开了两个天使般的孩子,独自前往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西班牙!
车子还在马德里温柔的坡度上行驶。
桑问我,是否喜欢听西语歌?
我望着他黑色的卷发点了点头。车还在行驶,驶过一个荒凉的山坡,像是我的人生,前面好像没有路了,但车子依然在行驶……
车速很慢,或许是桑为了让我了解马德里放慢了车速,或许是那时的我自己放慢了速度以至于身边的一切都慢了……
桑把我带进了他的公寓。
两只眼睛在幽暗的光线中发绿。
桑介绍说,这里是厨房,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做吃的。这里是卫生间,因为这个卫生间的淋浴坏了你可以去我卧室洗澡。这里是客厅,这是电视,如果想听音乐,那里有很多碟。这是儿童房。我有两个孩子,所以你今天可以放心住在这里。这两个床都可以,如果你喜欢爬上爬下,你可以睡这里。他指了指儿童床的上铺说,很安全。放心吧。不会掉下来。
那时我想说我也有两个孩子,突然又哽住了。好像什么东西卡住了,像失语一般,想说又说不出来。
他的眼睛,随着光线绿得通透。它让我想起好友店里的祖母绿,卖得很昂贵,每颗都有被专家鉴定过的证书。
透过他的眼睛似乎能看到另一种光,傲!
桑递给我一把钥匙说:这是公寓的钥匙。你走后把它放在桌子上就可以!我去庄园住,大概是周三回来。所以你不用担心没有地方住,因为你有几天的时间找房子。这是那个学生公寓的电话,你可以问。大概是在这条街。他把一张纸条给了我,又说,这里离你学校很近,你只要直走,一直往前走不用拐弯就到了你的大学。如果你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走丢了,你给我打电话。这是我的电话。他把电话写在了那张纸上,说,这是那家出租公寓的电话,这是我的。你不要弄错了。都记好以后,他教会我怎么开门锁门和使用一架极其古老的欧式木制电梯。
我说,很喜欢这电梯,在罗马我坐过这样的电梯。
但我没有说下去,那时我的心突然又碎了一地。
然后,他带我下楼。告诉我旁边是两家酒吧,都不贵。晚上喜欢喝酒就去那儿喝。他说,我哥哥是画家,他住在中国,中国人喜欢喝很多酒。晚上你可以去这里喝酒。因为就在楼下,所以我不担心你会丢!
我喜欢喝酒,酒是我的命。
他笑了笑,都清楚了吗?钥匙是否还需要再开一遍?
我说,不用了,都会了。
他又问,你再看一下路,认识吗?
我说,放心吧,我没有问题。
他说,我相信你没有问题。OK!今天你好好休息,什么都不想!喝酒睡觉!
途中我们去了马德里大学。在一片寂静的山坡上金黄色的树林里,落叶满地,桑推开办公室的门,向教授们解释了我由于签证晚了而迟到了一个月。希望他们给我两天的时间,因为我要找房子住。所以安排在周一对我的西班牙语言进行测试。
我说,谢谢你。
他说,不用客气。
桑走时推着一个咖啡色的皮质行李箱泛着岁月衰退的痕迹。我有那么一种感动和酸楚。看着他行李箱的滑轮渐渐远去,它似乎滑去了我很多的忧伤,一点一点,很久远,那在中国的所有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