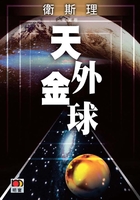早上醒来,我躺在儿童房,到处是玩具,汽车,海盗船,还有很多银币撒在地板上,童话书,纸片。我抱着一个洋娃娃,很想给她打针,喂她吃药,觉得她好像是病了。我从一个小药箱里找到了听诊器、体温计、针筒,给她取了个名字叫秘密。好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洋娃娃。这么蓝的眼睛会转,一碰她的肚脐,她就哭了。
娃娃的哭声让我回到了遥远的中国。在江南的水乡,奶奶就这么每天把我抱在灶口带大了我。因为我生下来只有三斤,像一只耗子。怕我冻死,她每天把我抱在灶口取暖。那时没有钱买洋娃娃,她用布缝成一个像娃娃的东西给我做玩具。
村里的那条河流是那么清晰,它流淌着她,一个农村妇女对我的全部的爱。奶奶不认得太多的字,只是小时候在私塾里念过几年书,她告诉我,那时先生很严厉,每天身上带一把尺子,不会背就用尺子打手心。奶奶拿着尺子打过我很多次,拿针扎过我不计其数,还用麻袋把我装起来沉到河里去。
就是这条河流。
它流淌着我所有的叛逆。
因为我太淘气太任性,因为我从小的基因里就布满了反叛。但是我的奶奶,她爱我。她以她的方式惩罚我之后,从她破了的棉裤兜里掏出一个鸡蛋。家里的母鸡只生一个鸡蛋。每天天还没有亮时她就要去鸡窝里把那个蛋掏出来放在那口大灶里煮熟了偷偷地给我。因为家里有三个孙女儿,但母鸡只生一个蛋。她只能趁着天没有亮就偷偷把蛋放在我的枕头边。因为那两个孙女都喝过人奶,我早产,我的母亲没有奶水,我从来不知道人奶是什么味。当我成为母亲的那天下午,医生给我挤出的第一口奶,我喂给了自己。
确实是甘甜的!
当时的我只有三斤,医生说恐怕养不活了。奶奶就把我包在一张草纸里坐着机动船从城里的医院把我带回了这个小乡村。按理,她是我外婆,但她希望我叫她奶奶。于是我随了她的姓。奶奶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就是邻村她都没有去过。她的亲生母亲是这里远近闻名的大家闺秀,雪白的皮肤、瓜子脸,却从来不对人笑。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她走过的地方都会有一种虫子莫名死亡。只要她摆动她的红裙,田里的农夫们都会放下锄头,所有的青蛙都跳出来了,所有的虫子都死了。她在生下我奶奶以后难产死了。而她的后妈在我奶奶五岁那年,因为在上海做珠宝生意亏得血本无归而跳河自杀了。
就死在这条河。
奶奶每天都要在这条河淘米洗菜,而这里埋葬着她的后妈。之后,奶奶得了一种头晕病,经常会犯,一犯就在床上躺几天有时甚至几周:头晕啊头晕啊。
我给洋娃娃喂完药后把她放在床上盖好被子。那时的太阳已把整个屋子照得通亮,白色的窗帘白色的墙壁白色的柜子,简洁干净。
很亲切。我的家也是这样的白色窗帘这样的白墙这样的儿童房。我突然感觉床上躺着的不是那个会哭的洋娃娃而是我女儿,她四岁了。她叫秘密。因为她生下来时太小,从我的身体里掉落时,红色的一团。我大哭起来,哭得比她怀里的婴儿还响!我的儿子也来看望她,看着床上多了一个小东西,问我:妈妈姐,你的大肚子怎么没有了?真奇怪!他到处找我的大肚子,那时他三岁多,叫我:妈妈姐。或许在他的印象中,他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爸爸。一个白发老头。他比我整整大了三十岁。他喊我,我宝,喊他儿子,宝宝。
当我再一次抱起她,喊她秘密,我发现她流眼泪了。我确定她不是洋娃娃,她是我的女儿,她要找妈妈。
我抱着她很久很久,想给她一点爱,多一点,甚至是所有的爱。这是一种天生具备的母性。我紧紧地抱着她,抱着她,很强烈地爱。
窗外的歌声、叫喊声把我从遥远的东方又喊回到了西方。
我推开窗户,男人,女人,酒瓶,香烟,雪茄,大麻味弥漫在大街上。
这里是欧洲,所有女人梦想的浪漫地方。这片地中海的大陆,它似乎为爱情所造。
这是那个西班牙男人的家,墙壁上是他两个孩子的照片,金发碧眼,和手里的洋娃娃一模一样。
我放下了手里的洋娃娃,把她装进了盒子。
她只是一个四岁孩子的玩具!
它或许是我生命中缺少的那部分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