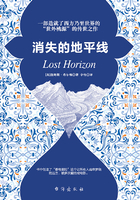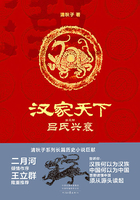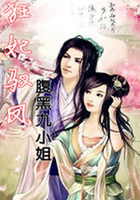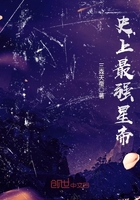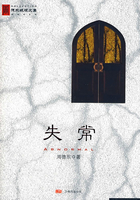26年前,那时我还是一名刚入伍的战士,在河南巩县杜甫家乡的一个小山村旁。我们的连队,就与那山沟里的风和黄土一起,走着军营直线加方块的韵律。我们训练,一个晚上野营拉练走100多里;我们施工,一次扛两包水泥。身体挺直时,便把红色的信念和绿色的心愿一起举过头顶,看那太阳,爆响青春的火花和声音。1979年的春天,就去了广西边境。半年后,再回到部队原来的驻地,才明白有了一场经历,才想起了猫耳洞前的风声,想起了战友倒下去时,眼睛里会喷出热血咝咝的声响,想起了边疆的泉水会唱出绿色的歌。于是,这些声音便走近;于是,我开始走近文学。看那一个个面孔,高大如山峰,深沉如海洋,而自己则如山坡上的一株小草,在风中低鸣。那小草上就亮着露珠,就成了战士的诗,成了绿军装的一个意境。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我就写了一些绿色的诗行。后来,就到军区的创作班听课,在一个刊物编辑部改了一个月的稿子。但终因悟性太低,那篇小说也就永沉心底。后来,就到军校,学了政治和历史,当了教员,上了研究生班。也还是在流血的倾诉和发黄的头颅中,把一个个事件和人物,抹上青铜和华表的悲壮与伟岸。这期间,曾试着写小说和剧本,可终是离文学越来越远,离生活越来越远。
1995年就转业到了地方。在京城的国家机关,就有了机关与人民、政治与人民的一些思考。而每次回到农村的老家,一些生活,农民的生活,就像春节的气息一样扑向你,揪你的心,扯你的灵魂。一些故事,我的姐妹和亲朋们讲述的故事,就如那燃着的柴火,拽出浓烈的烟,就把你不惑之年的冷淡,像江水一样地涌动起来。看那儿时熟悉的田野,想着土地的命运,农民的命运。人民是源泉,请不要把他们当作宝藏。人民是水,请不要污染这水源。20多年的大变革,生活变了,社会的阶层结构变了,利益的需求变了,国家机关的人员和作风也在发生变化。但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宗旨没有变,也不能变。我想,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各级官员,应该走近人民;应该像三代领导人始终强调的那样,走进人民群众之中,去真心实意地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谋利益。人民是水,人民是根。因此,我便把积累的故事,放在了《满罐》之中,放在了付一方和李满罐这些人物之中。这篇小说写完的几个月后,我在媒体上看到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的文章,他的呼吁是:回到人民中去。而秋冬之季的十六大,更是唱响了“三个代表”的主题。我想,这不仅是指各级官员,自然也包括改革的价值走向和文学的追求等等。
20多年过去了,又开始走近文学,感谢《北京文学》的扶步。显得老沉的我,皱纹里虽有风雪,可还是像孩童学步一样,蹒跚而行。再看过去的战友和同事,如阎连科,如朱秀海,如何继青,感到相距甚远。但毕竟走近了,走进去,感到自己如一头牛拉着的车,愿那牛不停地前行,拉着农民的日子,拉着人民的情感,向那高处,向那远方。